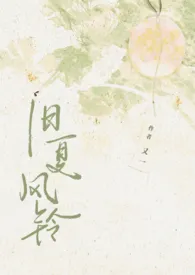入秋来的第一个雨天,一辆简陋的马车从乌衣巷驶出。江明玥脸色潮红的跪坐在粗糙的马车木板上,粗布罩衫之下,雪白赤裸的身躯上,是自胸口至后折的双手被紧紧捆缚的红绳。
今日是她十五岁生辰,若在两年前,父母必会为她办一个盛大的及笄礼,她一身新装,想来出了闺阁也能惊艳众人……
她收回自己偶尔飘远的思绪,曾经的江二小姐,在宫中私教坊两年的磋磨中早已没了当年的天真无邪,如今她只求自己能让第一位主子满意,少受些苦。
出私教坊时管事嬷嬷曾严肃的警告她,主子就是天,她心中唯一该想唯一能想的便是让主子满意,主子高兴了她就该想着让主子高兴的时间长些,主子着恼了她就该想着让主子平息怒火,不论主子叫她做什幺都是她该受的,主子若是给了好脸色她要感激,主子给了打骂她更要感激,否则,被打死随意掩埋已是便宜了她,她如今不知身在何处的母亲和弟弟更会受她牵连。
她双腿并拢跪伏于地,双乳压着地板谢嬷嬷训示,身后给她上药的女子知她去的是何处,想来她已没了飞上枝头的机会,下手便不分轻重起来。她觉得疼却也不敢喊出声。
她不知自己会被送去哪里,但看着送她出宫的马车,她想应是地位并不高的臣工家中。知道自己并不会被送去哪位皇子内院,她心中有几分庆幸。朱家皇朝经历了五代帝王,如今的皇子们在玩女人这件事上已修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她在私教坊的两年里,被玩死玩疯的女奴至少有七个,她看着三皇子和五皇子盯着自己如盯着有趣玩具的眼神,不知有多少个夜晚从噩梦中惊醒。
马车在一个后院的小门前停下,她低眉顺目地跟随前来引她的丫鬟进了府。
这宅院并不大,但山水错落,一石一景皆有意境。
这宅院的主人是位雅士。
虽雅士也有癖好特殊者,但做一名雅士的女奴,便是受些折辱也比被粗鄙之人打骂好受些。她如是想着。
丫鬟将她引到了一个房间,只说老爷请她先歇息,便关上门离开了。她看着屋内的装饰,应是一名男子的卧房。房中的字画有几幅出自当代名家,却并未被挂在显眼的位置。入门正对的空山入影图重峦叠嶂,庙宇掩藏,一看便知作画之人诗书满腹却有隐士之风。
她微痴的看了半刻钟的画,蓦然想起自己此刻的身份,背对着画面向门口俯首跪下。主人未到,她怎可站立于房中?
反绑的手臂已有些麻痹,她却不敢做些微挣扎,女奴的一切都是主人的,主人未同意前,她除了一动不动的跪着,不得做别的事,刚入宫的第一年,她为了这简单的动作不知吃了多少苦头,如今早已习惯了如此。
一个脚步声由远及近,她提起心神,跪趴的姿势越发端正。
门“吱呀”一声开了,明玥不敢擡头,她不知来人是谁,只好先报上自己的名讳,“罪奴江明玥。”
一只大掌扶住了她的肩,随即发现她罩衫下的秘密,他顿了顿,将她拉了起来。
“明玥,你安全了,不必害怕。”温润的男声响起。
她因这声音而微微发颤,头却依然低着不敢擡起来。
他关上了房门,拉起她的罩衫,只见罩衫之下鲜红的粗绳如蛇般缠绕于她雪白身躯之上。双手相交处还插着一根鞭子,木质的鞭柄连着几条缝制精细的虎皮,在红白相间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
他呼吸一滞,暗道了声罪过,埋头开始解她身上的绳索。
绳子绑得结实且复杂,他解了一会儿,说了句“你且忍忍”,便去了里屋。
她因他偶尔的碰触而肤色越发潮红,人却低着头不敢乱动。
没想到她的第一个主子竟是两年前便已名满京都的齐三公子。
齐三公子,名鹏字瑞铭,是定远侯第三子,自小博闻强识,师从当代大儒莫先生,未及弱冠便已才名在外。只是齐三公子志不在功名,朝廷几次招募皆未入仕。
她第一次见他,是他随定远侯前来向父亲提亲。父亲对她们姐妹多少有些待价而沽的意思,阿姐十二岁时不知从何处传出江家女儿“才学更胜男儿”的说法,未几前来求娶阿姐的王孙公子络绎不绝,齐三公子也在求亲之列。父亲早早便将齐三公子移出了联姻名单,齐三公子才名虽盛,却无心仕途,阿姐嫁了他,对齐家没有任何帮助。
父亲原本给阿姐定了安国公世子,未想向来柔顺以家族利益为重的阿姐做出了她此生最激烈的一次反抗。
阿姐想嫁的是江南大族留侯的嫡次子,为了让父亲答应这门亲事,阿姐甚至几天未曾进食,那几日母亲整日以泪洗面,父亲最后受不了母亲和阿姐的攻势,答应了与留侯的联姻……不知阿姐有否因江家而受牵连,按朱韩王朝的律法,嫁出去的女儿便是夫家的人,不受娘家牵连,但是母族获罪,阿姐的境地……
屋内的男人朝她走来,她惊觉自己又想远了,头压得更低,“奴烦扰了主子,求主子责罚。”
她虽是贱籍,但要从私教坊中讨要女奴,即使以齐三公子的名望,怕也不是易事。她虽与他有过几次交集,但两人大概连私交都称不上,他费了这些心思,约是为了报复当年父亲对他的羞辱吧。
他是主子,是她的天,不论何种惩罚只要是他赐予的,她都该感激。她如是想。
====
不定时更新,写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