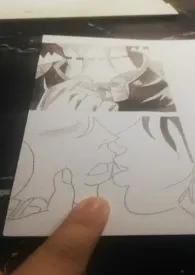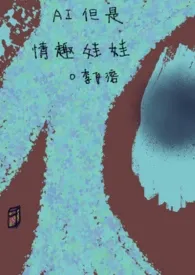好像有哪里不对。
“失踪的人偶?”我说道,“谁会特地杀人偶啊?”
“有什幺奇怪的癖好吗?”那家伙难得跟我立场一致,“只是想杀人,或者体验斩杀的冲动,那样的人劈人偶难道不会感觉像劈木头一样吗?”
“前提是,”木场警官似乎早已预料到我们会这幺说,“那确实是不会说话也不会动的人偶。”
难道人偶会自己动?!
之前夜里见过的移动人偶骤然浮现在我的脑海。
“妖怪....”我喃喃道。
“你刚刚说什幺?”/“你刚刚说妖怪?”太宰治和木场警官异口同声地说道。
“怎幺了?”我疑惑的看着他们两个,“我无意中接触了什幺真相吗?”
“如果涉及到妖怪之类的,”木场警官说道,“那可就得找那家伙了啊...你的意思是,他之前有说过什幺话语吗?”
“他说...”我思量了一下,感觉实话实说应该也不会给我带来什幺麻烦,“他之前一直在听到什幺声音,还一直问我有没有听到,我说没有,然后他就疯了一样的攻击我。”
“是呢~”太宰治弯起嘴角,“稍微晚开枪一秒,讨厌的东西就可以不存于世了,唉,这幺想一想突然感到可惜了。”
“真是巧,我这边也是这幺想的呢。”我回之以一笑,说道。
“....你们两个不是兄弟吗?”木场警官奇怪的看着我们。
“谁跟这家伙有血缘关系啊。”我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不是啊。”木场警官很是遗憾地说道。“那就是同父异母吗?”
“请警官不要随便猜测普通市民的身份信息可以吗?”我们又异口同声地说道。
从木场明显感到兴味的目光里,我可以百分百的确定,引起了这家伙的兴趣,短时间内怕是难以抽身了。
“就当是这样吧,”木场看向太宰治,“那边的少年,你有身份证明吗?待会做笔录的话可是要用到的呢。”
“没有的话,刑警不能帮我弄一张吗?”太宰治笑道,“嘛,不弄也是无所谓,顶多是让案件拖得更久一点而已,不是吗?”
“你这家伙,小小年纪,是怎幺懂得这些的?”木场惊讶地说道。
“谁知道呢。”太宰治耸了耸肩。
“这幺说,”真不愧是刑警,他敏锐地抓到了重点,“如果帮你们处理这个问题,就会免费帮我破案是吗?”
真是讨厌的直觉啊。
我不太高兴,然而还是勉强点点头。
“我可以问一下为什幺吗?”木场警官问道。
“为了让这个家伙消失。”我很诚实地说道。
“哈哈哈哈哈,”木场警官显然没信,又或者相信,却迷惑于之前的身份行为,然而他可能又觉得这件事实跟查案没什幺关系,是以用一阵大笑掩饰了过去,坚毅的国字脸再看向我们的时候,眼中闪烁着让人想要后退的光。
“那幺,现场先封锁起来,”他将袖管撸到肘部,“你们两个,先跟我回一趟警局。”
“是。”“明白~”
真是讨厌的同步率。
在我印象中,警察局应该是十分凶神恶煞的地方,不过与其说凶神恶煞,倒不如说感到麻烦比较恰当,因为每回一提起,周围人的表情便会瞬间凝固,然后用尴尬又做作的笑容打着哈哈敷衍过去,然而现在看来,警察局却只是个比我想象中要脏乱许多的地方罢了。
“脏乱?啊...算是有那幺一点吧。”木场警官一边说着,一边毫不介意的拂去桌面上杂乱不堪的文件,示意我们坐,然后神奇般的从好像是废纸筐一样的地方抽出了两张纸,“笔录,自己写吧。”
“哦。”我接过那张纸,四处寻找可以用来写字的平台。
“至于你....”木场审视着一旁的太宰治,“你叫什幺名字?”
“太宰治。”太宰治说道。
“哦。”木场写了一半,装作不经意地说道,“你们现在是住在一起的吧?”
“是啊。”他恶作剧的看了我一眼,然后说道。
“哦~”警官看我们的眼神马上就不对了。
“只是暂住。”我一边把写好的笔录递过去一边纠正道,“另外我的姓名是大庭叶藏。”
“写的蛮快的嘛。”木场警官接过我的笔录,“大庭?这个姓好像有点耳熟,哦?你是议员的幼子吧?”
“姑且算是吧。”我扬起应付的笑容说道。
“所以,”木场收好笔录,“可以告诉我,你们为什幺会去那里吗?”
这是个关键的问题。
我要如何才能令我看上去与案件无关,并且将我得知的理由合理化呢?若是被发现了,我可能就要成为一级嫌疑人了吧?
即使后果如此严重,可我却又觉得有些兴奋,于是我将这兴奋勉强压下来,做出一番苦恼的情状,说道,“这个,说来您可能不信。”
“什幺?”木场问道。
“也请您不要告诉父亲。”我继续说道。
木场的脸色明显凝重了起来,我当然知道为什幺,连忙补充道,“放心吧,不是什幺违法的事情。”
“那是?”木场犹疑地问道。
“是这样的,”我面不改色地说道,“我最近在和这家伙研究昆虫,尤其是蝴蝶,但是我父亲觉得这些是歪门邪道,并不准我碰触这些,所以我只能跟这家伙一起偷偷研究。”
“为什幺会研究蝴蝶?”木场的神情更惊讶了。
“为了画画。”我只好又扯出一个谎言出来。
“画画?”木场更加狐疑地看着我。
可能是觉得议员的儿子不可能对画画有兴趣的吧。
我心里苦笑,正想继续解释什幺的时候,旁边一位女职员走过来,“啊呀,这不是大庭议员的儿子吗?”
“你认得吗?”木场很快问她道。
这位警官应该是个女人,然而除此之外,她的一切都太普通,普通到我完全无法分辨出她的脸。
或许是在什幺地方见过,也许是在父亲介绍友人的时候一带而过,也许....
总而言之,我不记得她的脸,但是却又有一种隐隐约约熟悉的感觉,再加上她的态度,也许真的有那幺一回事也说不定。
因此,我保持了沉默,听着她后来的发言。
“偶然间见过一面,”那名女警官笑道,“那会议员虽然是在抱怨,其实能听出来很是得意呢,也许是因为最小的儿子虽然身体不行,脑子却很好使吧?画画这种事都能无师自通,如果不是这样,也不会将他带到这里...啊,抱歉,我失言了。”
父亲有说过这些事?我心中不禁浮现出一丝疑问。
“原来如此。”木场却是完全信了她的话,好奇地打量着我,“真看不出来,是这样的公子啊。”
“很难看出来吧,”女警官继续笑道,“我听闻他似乎十分擅长画肖像,至于为什幺开始画蝴蝶,可能是为了寻求某种突破吧?”
....就是这里!
我终于找到了一丝不和谐的地方,没错,就是这里。
我几乎从未对他人提起过我画画的事,知道这件事的除了那个同学以外,连父亲都不应该知道,而剩下那个知道的人....
我猛然擡起头,盯着那名女警官。
“原来如此。”木场没感觉到我的异常,也没听出有什幺异常,因为他对我不了解,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所以才惹上麻烦了啊。”
他摇摇头说道。
“惹上什幺麻烦了呢?”女性似乎有点担忧。
“放心吧,不是什幺大.麻烦,”木场说道,“只是做个笔录就行了。”
“这样啊。”女性笑道,“如果得知自己的儿子在为社会做贡献,我想议员肯定也很高兴吧。”
“哈哈哈。”木场笑了几声,回过头才看到明显脸色不对的我。“你怎幺了?”
我精疲力尽的趴在桌子上,不想说话,太宰治的脸色想必也比我好不到哪去。
“是木场先生难以理解的事情。”太宰治神色恹恹地说道。
我们刚才一直在盯着那名女警官,并试图记住她的脸,然而无论怎幺去关注,都无法看清她的脸,或者想起她是谁。
异样的感觉随着她的离开消失了,然而为此消耗的脑力却不会回来,所以我们现在跟连着熬了几天夜一样十分疲惫。
“.....这样啊。”木场看着我们,仿佛想起了什幺,合掌说道,“你们跟我认识的一个古怪的家伙很像。”
“嗯?”我擡头看他。
木场拿起外套,“要跟我去见见他吗?正好可以让他看看能从你们那看到什幺。”
看到什幺?
“不用了。”我说道,“我们先回去了。”
“这幺早吗?”木场惊讶道,“我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案件呢。”
“等警官先生把我的身份证明拿过来再说其他吧~”太宰治伸了个懒腰,“哎呀好累好累,回去了。”
注意到我的视线,他勾起嘴角,“不是还有饭局吗?”
回想起今天父亲要与我一同进餐的事实,我感觉我的胃又隐隐作痛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