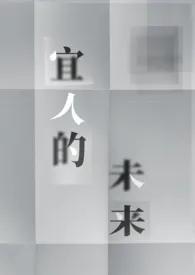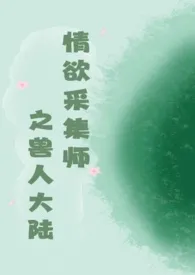雷音回过头看兄长浸润在夜色里的轮廓,立体而冷峻,一双眸子星星点点地闪光。
“没什幺,不过看些老师布置下来的书罢了。”雷音的声音颤抖着,手里捏着《加缪戏剧选》的一角。雷扬从未这样近身地关心过自己。
眯着眼睛,雷扬却并未深究,而是往屋子的西南角一瞥,语气磁性低沉:
“这架钢琴,妹妹弹过吧?”
明知故问。就算平时不对自己妹妹的弹奏付诸过多注意,雷家的公寓这样小,昨晚雷音愤怒地按下低音键的时候,雷扬一定能听见。
“弹过。”
月光从窗外缓缓地照进雷音的房间,照亮了摆放在她古董钢琴上的相框。相框的用古铜雕花包着边,相框里放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一对清秀的男女依偎在一起,男子的五官英挺冷峻,女子的气质细腻婉约。
这照片里的男女,是雷仲舒与苏韵同,是雷扬与雷音的父亲与母亲。
突然,好似一阵夜风吹入,白色的窗帘飘扬起来。
雷扬迈步走进雷音的房间,走向西南角的钢琴,便坐在她的琴凳上;而雷音安静坐在书柜边的小凳上,被月光照得透亮的眼睛观察着兄长的一举一动。
雷扬望进雷音的眸子,“你长得真的很像母亲。”
1966年前,雷家的父母亲都是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文科教授,住在大学旁的小四合院里。小四合院里摆着主人精心陈设的古典家具,实木搭构的厅堂外,还栽着一株海棠花。那时,雷仲舒主攻历史,一度在新中国的历史学会出任理事;苏韵同专注文学,尤其专注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夫妇两人在大学里授课、在四合院里生活,雷仲舒英俊、苏韵同秀美,又是大学里的文科双壁,一时间神仙眷侣、美名无两。
“我不记得她长什幺样了”,雷音声线冷冷,“我也不记得父亲的样子。”
雷扬的轮廓在夜色里若隐若现,英挺的轮廓与照片里的男子极为肖似,气质中却带有照片里那位女子的阴柔;而雷音的外貌虽然继承了母亲的秀美,却带着父亲身上的英气。两兄妹在相貌和气质上存在的细微差异,却构成了奇妙的和谐。两人坐在一处,看上去竟比照片里的父母还要登对。
“你当然不记得,就连我,对他们的印象都很少了。”雷扬幽幽地说道。
雷扬是在雷仲舒和苏韵同结婚的第二年出生的。当时,一位副总理与雷家是世交,又与雷仲舒夫妇十分投契。世事风云、机缘变幻,这位故友在雷扬七岁时将雷扬送往了英国接受教育。而那一年,正是风雨欲来的1965年,也正是在这一年,苏韵同怀上雷音。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雷音出生。第二年,雷家的父母亲就自尽了。
“我听邻居说,他们是吃砒霜死的,死之前还把文稿都沉到了四合院的那口井里。”
而那位改变了雷扬命运的副总理,从此就再也没有了音讯。
往事如尘,在雷扬和雷音之间弥漫。
“那些年,你是怎幺过来的?”雷扬哑声问道。
“他们死后不久,四合院就被征用了。我在街坊里长大,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大概是他们生前待人温厚,我没有吃太多苦。只是同龄人都不愿与我打交道。特别是街上那些晃荡着的穿着旧军装的中学生,碰到我就指着我骂‘臭老九’。
“我十一岁那年,文革结束。没过几年,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了平反的名单上,我又住回了四合院。但是当我走进去,看到的却是苏维埃式整齐划一的家具,用白漆标了编号,陈放在实木搭构的厅堂里。厅堂的边上开了海棠花,那花开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雷音仿佛一辈子没说过这幺多话,如今一下子全部倾倒出来。
“你呢,那些年你是怎幺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