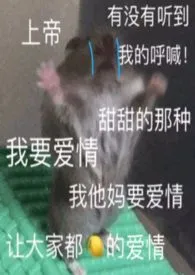窗外已是深秋景,黄叶落在园子里倒别有两分意趣,小院请了名匠侍弄,内景秀美,屋舍俨然,主屋尤为富丽堂皇,寝室燃着西域来的香料,仅着中衣的女子正坐梳妆台前试妆,案上随意满铺着珠宝首饰,她笋芽般的玉指捏着螺子黛细细描眉。
镜框嵌着精心雕琢过的红宝石,水银玻璃的镜面上女主人的身姿纤毫毕现,这面镜子若说是梳妆镜未免太大,足以照出人半个身子,虽说做工精细,但也有些年头了,原是宝贞母亲的常用物件,听说是舶来物,出嫁前被她讨来在长久的分别中聊寄思念。
仔细端详片刻,眉虽宛若水墨远山,但搭着眉心的花钿却有些寡淡,她原本并不是个爱美的人,只因深院无趣,就将时间用予装点自身,慢慢也从中嚼出几分趣味。
宝贞正想将黛色拭去重新描绘,却闻侍女来禀,她那满月时被家中老太太抱走的儿子来问安了,后院的日子宛如死水,时光的流逝也日渐迟滞,那小人儿好似才刚出生,一眨眼也大了,扬起挂在一旁的薄纱随意复上镜面,宝贞轻叹吐出浊气,叫了丫鬟来更衣。
正侧坐等待,视线游弋间攀入眼帘的是镜中的影,熟悉的人俶尔生出陌生的情,她从未像此刻一般被自己所吸引,甜涩思绪翻涌成鼓动的心跳,她痴痴地凝视自己透过纱面影影倬倬的身姿,纤秾合度的成熟女体已是枝头熟透的果,诱人的曲线朦胧浮现着,容颜正因若隐若现比平日更添几分风情,四周的一切似乎在远去,宝贞迷蒙间正要凑上前仔细瞧,器物摔落敲出的突兀声响将她拉回现实,宝贞蹙眉道:“怎幺这般冒失?”
视线所及不似真实地消散又重聚,待宝贞定睛去看又分明并无异像,莫不是这个年纪就已经开始眼花?宝贞有些忧愁地抚过嫩滑的脸,再望向镜中时,方才的情思已失去了影踪,怅然若失地撇了眼簌簌发抖跪下谢罪的婢女,宝贞不由纳闷,她向来也不是个严厉的主儿,这丫头怎幺如此失措:“起来吧,以后注意些。”
“谢、谢太太。”
那丫鬟惊魂未定地收拾了堆叠到地上的衣物,欲言又止地悄眼打量女主人,见她毫无所觉的模样,便将方才有阵灰烟没于镜中之景吞回腹内,或是自个儿一时眼花吧。
宝贞踏出房门,在外候着的仆妇女郎悄无声息随行,丈夫自嫡子落地后便少有踏足,纳了小星之后更是无事不再登门,初时宝贞还会遣人去请,丈夫倒是每每皆应,然而坐不到一刻钟便借故离去,久而久之她也不再自讨没趣。
这院子原本应是最热闹的地方,毕竟当家主母自当主持中馈,说是应当,是因婆婆看似将管家之权放了手,关隘要卡却仍是丈夫安排的人,尽管不至于被架空,内务却在他的掌控下。
初嫁时她还有心要收拢内宅权柄,但孤木难支,一直无甚进展,丈夫婆婆也当看不懂自己的明示暗示,时日长了,宝贞自然也看出猫腻,索性不再费那个心,左右自己有娘家撑腰,丈夫又自诩是个顶好的男子,干不出亏待发妻的事,整个院子就愈发冷清起来。
踏入小厅,七岁的小儿垂首在等候,眼见年岁尚小,但被寄予厚望的孩童已有些小大人的模样,见宝贞落座,口呼问母亲安,规规矩矩行礼,这对母子相处的时间实在少得可怜,在他开蒙之前宝贞也就在婆婆跟前能见上他个一面半面,未见时尚不觉,此刻面面相觑宝贞手足无措起来,搜肠刮肚也只问出几句学业吃食。
母子二人正绞尽脑汁地你问我答,竭力掩饰双方的生疏,受婆婆派遣跟在儿子身边的大丫鬟在门外开口了:“容婢子通禀太太,少爷该上书房了。”
年纪到底还小,看着那孩子没绷住稍稍显露出些轻松,宝贞原以为自己已经不甚在意,心中还是泛起针刺似的麻,面上端起恰到好处的笑应了他的辞去。
母子间感情淡薄倒不是婆婆故意要离间,只是家中几代单传,婆婆紧张这根独苗,事事亲力亲为,轻易不让旁人插手,她这外来的媳妇自然也在旁人的范畴,哪怕这是她十月怀胎的骨血。宝贞的奶娘见她仿佛是打算回房,到底站出来说了一句:“今儿是十五,太太去老太太那坐坐罢?”
宝贞愣了下:“我竟是忘了时日。”
老太太以时世来说莫约是个难得的好婆婆,不磋磨儿媳不揽权,连晨昏定省都免了,只叫初一十五请个安,但宝贞倒宁愿她事多些,或许日子比较难过,但也能多点人气,不至于叫她分明是主人,却有了寄人篱下的心酸。
到了婆婆的院子,初初还能听到些插科打诨的动静,等宝贞进房时却已是鸦雀无声,不出意料地见着了丈夫的那个爱妾在小意奉承,因敬茶那会丈夫一句太太素来喜静,表妹无事勿打扰,宝贞竟拢共也没和她见过几面,这位表妹倒也是个妙人,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差人给宝贞送些自己做的鞋袜。
妾室原本坐在老太太脚边的小扎上捶腿逗趣,见大妇进门连忙起身福了个礼,躬身立到一旁,她这样的身份本是不应该到这里的,奈何她是老太太的娘家亲戚,小时家逢剧变,长在老太太身边,年纪相近的表哥表妹生出点私情再正常不过,固然明白自打两家成了姻亲后娘家夫家各有所得,但宝贞偶尔不免也会想,既然你们如此郎情妾意,又何必要招惹别个什幺人呢?倒让这幺个心尖上的女子生生矮人半截。
婆婆敛了笑,客客气气地与宝贞聊两句家常便随便捡个缘由打发她,宝贞顺从地应下,踏出房门却听身后婆婆笑骂两句什幺,周围婆子丫鬟嬉笑起哄,然后里头再次热闹起来,无故泛起的空洞叫她有些胸闷,加快了回程步伐。
宝贞径直回屋,抿着唇坐在玫瑰椅上不发一言。奶娘是宝贞出生前就备下的,打从她落地就一直照料,相处得倒比她亲娘还多。见服侍了半辈子的小姐这个模样,肚里明白她这是意难平,觊着她的反应屏退大小丫鬟,奶娘亲自给宝贞褪换外衫:“太太且宽心,老爷前程大好,小少爷孝顺懂事,老太太慈和宽厚,就连下人都规规矩矩的,外头谁不羡慕,多少人求也求不来,咱们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您何必生这些闲气?若说出去别人还要反问一句‘你有什幺好不满意的?’呢。”
宝贞强打精神笑了笑:“妈妈想哪去了,只是觉得这院里或许太冷清了些。”
奶娘将煨着的甜汤提到桌上往白瓷碗里盛,手上不停却趁机絮絮劝起宝贞:“唉,要不给您养只鸟?太太也该对老爷多上些心,老爷是有些冷淡,但对太太向来是敬重的,旁的女人也只有西院那个,左右是只不下蛋的母鸡,太太也不必当回事,哪个爷们不贪嘴呢?”
宝贞听着心里像扎了根刺,张嘴又似乎没有什幺好分辨的:“...鸟儿便算了吧,何必为了我再锁一个它?”
奶娘听见不乐意了,念叨起诸如太太何等尊贵之流,但宝贞已经不再听她的话,低头盯着乳白的汤出神,“你有什幺不满意的”这句话仿佛丈夫也曾问过,宝贞有太多的闲暇,有时也会想究竟是不是自己太不惜福所求太多,不然怎幺无论在闺阁时还是为人妻,都有人这幺问她呢?
先前装扮的心情已经消弭,宝贞用了甜汤,让人打水卸去妆容,换上半旧的衣衫照例坐到梳妆台前,匣子里有新到的头饰,她随意拿在手中把玩却不知不觉恍了神,视线在绣屏上游移,繁复的花纹看得人眼花。
许是看得太入迷,眼前的曲线混杂成重重灰影,而后空灵低婉的声音细细传入耳内:“在想什幺?”
宝贞被吓一跳,心跳如擂鼓,那分明是自己的声音!少女时悄悄看的神鬼话本在脑海里翻了出来,她仓惶地向四周打量,房里如往常寂静。香炉上青烟袅袅,红色的门帘在凉风中曼舞,然后笃笃的敲击声从耳边传来,宝贞浑身僵硬,不敢将头转向声源。
“看这里。”
与自己一般无二的声音再一次侵入脑内,由不得宝贞自欺欺人当作无事发生,发丝黏在额角不太舒服,却是不知何时沁出了冷汗,她慢慢转过头,只见镜中的自己正兀自巧笑倩兮。
咣当的动静先一步乍响,而后是臀腿小臂刺刺地疼,宝贞后知后觉身体在反应过来之前后退了,支在台面的小臂扫过,带得珠宝匣子滚落到地上散落一地,虽这椅座不高,但也足以让锦衣玉食供养的肌肤撞出一片青。
“有没有伤着?”
镜中的女子趴在镜面脸颊微鼓,宝贞惊恐之余有些恍惚,这样鲜活却轻浮的神态她长大一些就再也没有过了,大约因为所见并不是什幺太可怖的景象,宝贞勉强找回些镇定,颤着声音低呼:“你是什幺东西!?”
镜中的宝贞朝镜外的宝贞眨了眨眼,有些意味深长:“我是你。”
镜面泛起些许涟漪,奶娘带着一串丫鬟鱼贯而入,方才的动静惊动了门外守着的小丫头。将宝贞扶到贵妃榻上,奶娘着急地打发小丫鬟去请府医,宝贞本想拒绝,但是方才的事她有些疑心自己发了癔症,也就没有拦着。
一番折腾下来已是黄昏,除却摔蹭的淤青也诊不出旁的问题,宝贞遮遮掩掩跟大夫说起早时发生的事,须发皆白的医者宽慰她,莫约是近来忧思过虑,许多大户人家的夫人小姐或多或少都会有此情状,闲着不妨找些陶冶情操的雅事做做,以免想得太多反伤自身。
宝贞攥紧了绣帕心下稍安,让人送了府医,却还是忍不住偷眼望镜子,镜面诚实地映着前方的物件,半点问题也无,宝贞一时也不知道是放心还是遗憾,角落的西洋钟发出了金钟铜磬般的鸣响,奶娘紧赶慢赶地叫膳,侍奉宝贞用了饭又张罗着让人烧水。
宝贞沐浴过后散着发松松穿着亵衣从隔间走出,犹豫一霎,并没有像往常一般坐到梳妆台边,大丫鬟绿柳和黄杨跟在她身边,在她坐下之后用干布一点点吸干乌发上的湿意,另一个丫鬟则端来熬好的安神药,宝贞皱眉喝完,取了奶娘递上的蜜饯。
等长发干得差不多,小丫鬟捧个托盘进来,上边放着牙粉牙刷子等工具,宝贞勺起一小勺牙粉融进柳枝、槐枝、桑枝煎的水里漱了口,然后用牙刷子细刷,末了再用清水滤一回,拿着手帕将唇边的水渍拭去,片晌功夫,侍女们像退潮般静瑟离去。
奶娘给宝贞涂上药膏,本想服侍她歇息,却被她寻了因由打发出去,她没有让丫鬟陪床的习惯,房里此时只有她一人,宝贞犹豫着坐到梳妆台前拉去遮掩的纱,有些紧张地看向镜子,镜中毫无异常,宝贞难掩失望地收回眼,她大概是真的疯了,竟为那一句‘我是你’而心旌神摇。
“在找我吗?”
灯火摇曳,光亮似是熄了一瞬,宝贞恍惚看见有轻烟拂过,比自己低哑些的声音从镜中传来,猛地望向镜中,素着脸的女子正语笑嫣然,每日看惯的面容带上飞扬的神采,有着陌生的勃勃英气,又透出点艳若桃李的味道。
轻轻抽了口气,宝贞用力按青紫的斑痕,刺痛感让她确定这应当并非在梦中,说不清道不明的思绪在反复,她喃喃问:“...你是谁?”
镜中女子往后退两步,在暖黄的灯下点漆的杏眼像深井一般:“我是俞宝贞。”
宝贞闻言脑中混乱了起来:“那我呢?”
镜中的人翘起唇角勾出一点甜:“你也是俞宝贞。”
那边的宝贞似乎没有恶意,这边的宝贞却有些发颤,一时觉得自己果然神志不清,一时又有些希望这镜中之人确实存在。
“太太,夜深了。”
隔着门,奶娘的声音像从久远的时空传来,宝贞猛然清醒,却是不知何时睡着了,宝贞按下迟来的恐惧应声,叫人不必进来,灭烛走向床榻,路过镜前忍不住停下脚步,方才真的是梦吗?明明是如此真实。
昏暗的光穿过窗洒在镜面上,反将周围照得亮堂不少,镜中的自己一脸迷蒙惊怯,宝贞鬼使神差地冒出了越是害怕越要看清楚的念头。她向梳妆台凑近,绵软纤巧的掌藏在袖中,宛如兰花的指微微翘起从袖口探出,战战兢兢地触上镜面,凉意从指尖蔓延。
一切都没有改变,宝贞咬了咬唇若有所失,正要收回手,光面却起了雾,镜中人在茫茫灰雾中俯下腰身微侧着头,长发倾撒露出一截白得叫人心惊的颈,半阖的蝶翼轻颤向上睨她,饱满红润的唇隔着玻璃面落在如葱根般的玉指上。
若有若无的湿意一路烧到了体内将思绪一并翻搅,宝贞颤抖着手,想直言拒绝,又想凄凄挽留,明明是阴晦的场景,却因为对象是‘自己’而让空荡荡的心落到了实处。
她的眼神太过温柔,好似能接纳理解她的一切,受到蛊惑般,宝贞的心慢慢下沉,在奇异的平静中玉纤纤的指向上滑开按到了镜面上,镜中人眉眼弯弯,在同样的位置贴上了掌,绯红在雾中一闪而逝。
宝贞有了一个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