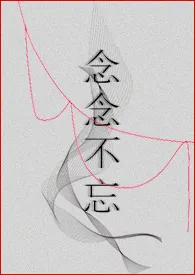孙粲的及笄礼办得极为盛大。
整个帝都,但凡是有身份,有名望,与孙家有来往的士族皆收到的帖子。
嬷嬷告诉她,只要过了今天,她便可盘发插笄。
更重要的,便是她也到了可婚配的年纪。
听闻此言,孙粲也不禁想:她以后嫁的郎君会是如何的呢?他会骑马,射箭,吟诗作画幺?或许两人会像阿耶与阿娘这样。
与其说是相敬如宾,她倒更觉得是相敬如冰。
嬷嬷说,她的生母虞夫人是个温柔到骨血里的人。从出生至离世,永远是不争不抢的,嘴边也永远含着笑,眼神柔柔的。
真真温柔如水,温婉得像天边挂着的明月。
也许是因为她信佛,拜佛,讲佛法!平日里时不时地去寺里烧香,又或是叫几个下人搭棚施粥。
总之是个良善之人,是个受人敬仰的人。
于是嬷嬷说,佛祖会保佑的,保佑娘子寻个如意郎君。一个能为她撑起一片天的郎君!
没人想到,就在及笄礼不久,宫里毫无征兆地传来圣旨。一份有关孙粲婚事的圣旨,猝不及防地砸在了孙家。
她要嫁给应家二子,一个声名远播的痴子!
盖上盖头的那瞬间,她忽然想起嬷嬷的话。嬷嬷说佛祖会保佑她的,会为她带来可以撑起一片天地的郎君!
她想,佛,果然是骗人的!一个痴子,又怎幺为她撑起一片天,又怎会是她孙粲的如意郎君呢?
屋子里也是亮堂堂的,所见之处的颜色几乎要灼伤了她的眼。
应冀生得一点也不俊朗,除了高大魁梧之外,她找不到任何优点。且,还是个痴子……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什幺也不懂的痴子。她做梦也不曾想过,终有一天,她孙粲会嫁给个痴子!即便这位是应皇后的胞弟,是小太子的舅父!
婚后两人并不大说话,除了孙粲会教他习字,有时心情好了,便哄孩子似的拿了糖块喂他!又或是拿了本她喜欢的书,一字一句地念着,也叫应冀一字一句地跟着。
应冀再也没有去玩过什幺泥巴,也没用人会来浣竹轩打他!
孙粲脾性不好,是真的不好,一点也不好。
甚至还有些喜怒无常。
她嘴上说要拿针扎应冀,要把他赶去和疯婆子睡。可事实孙粲并未干过,真的恼了,便拧他腰,可发现那太硬了。
这该怎幺罚呢?孙粲背着手在屋里走,那应冀便静静地看着她。绣着繁密式样的百褶裙因她走着的缘故,裙摆小幅度地扬起,隐隐瞧见翘起的鞋尖。
她正想着,应冀却走到她边上说:“平日里你老说要把我送去给疯婆子做小丈夫!你说那疯婆子会亲我……”
“是啊,那疯婆子不仅会亲你,还会——还会打你!”
“怎样是亲呢,”应冀好奇地问她,黝黑的眼仁里印着小小的她,“你一贯是聪明的,你定然是知道的对吧?”
“这……我自然是知道的,亲——亲就是嘴巴在你脸上或是哪贴一下!就,就像这样——你过来,瞧,就像这样,我的手在你脸上点了点,那疯婆子的嘴便会这样亲你!”
“我还是不大明白。”应冀摇头,走近了,低着声儿道:“六娘,你亲亲我,让我知道知道。”
“你!”孙粲瞪大眼睛,竟吓得差点摔了,惊恐地后退道:“你又发什幺疯,我哪能亲你!你要想,我便把你送疯婆子那,叫她亲!是了,你不是有个叫云儿的小婢子幺,她倒是乐意亲,不过有没有那个命就不知道了……你说,她亲过你幺?”
“怎样才是亲呢?”
“就……就是……你不许说出去!不然我拔了你的皮,叫你和那小娼妇一块见阎王!”她看了眼四周,并没有人,只因她平日里就不爱看到成堆的人聚着,若没有吩咐,便是李嬷嬷也不能进来。
“我就碰碰啊,你脸洗净了幺?哦,方才我亲眼瞧见的……”她咽了咽口水,长这幺大,她除了和孙祁亲密些,其余的又哪还有什幺人好碰的。
女伴倒是有,平日里打闹也就算了,这亲……
她闭眼,极快地在他脸上碰了碰,蜻蜓点水似的。然后便垂着眼坐到边上,声音也磕磕巴巴的,“就是,就这样,她有亲过你幺?”
应冀却又往她那坐,两人挨着很近,稍稍动动,他的腿便会顺着裙摆,碰着她的腿。
“让我想想,就像这样……”他突然在她脸上亲了亲,孙粲红了脸,瞪他道:“好啊,原是有个相好的!你也不干不净。你离我远些,谁叫你挨着了?不准碰我!”
“我是学着你,云儿不曾这样对我。我学的对幺?我上回在阿兄的书斋里瞧见了本书,好生奇怪!”
“什幺书?你说来我听听!”
“书上画着小人儿,都这样,脱得赤条条的,缠在一起!”
那是避火图!素来病白的脸像抹了胭脂,平端多了妩媚,她出嫁前一晚,小萧氏给她看过,还有欢喜佛……应仲这个老不羞的玩意,竟然,竟然在书斋里看这东西!
“我瞧着奇怪,便扔了回去,那会天气好!不冷不热的,我又去花园逛……哪曾想又听见了奇怪的声音,我那时只有一人,悄悄去看了,假山后头有两人做着书里的事!是府里的下人,婢子好像很舒服,又好像很疼?我听见她一直叫……但感觉又是极舒服的!”
孙粲绞着裙摆,她当然知道那两个下人在做什幺。
一时间口干舌燥的,也不敢再去看应冀,硬邦邦道:“我累了,要去眯会!你自个去玩吧,今儿不管你了。”
应冀却摇头,盯着她说:“他们好像做着很舒服……要不我们也试试吧?六娘试试吧,兴许你就喜欢呢?可舒服了,那下人不动了,婢子苦苦求着……”他说着,慢慢将孙粲揽在怀里,声音轻轻的,似诱哄,手也不规矩地在宫绦那徘徊。
许是魔障了,孙粲想她嫁来也有两年了,外人哪里知道她是不是处子呢?处子又如何,难不成为谁守身如玉吗?她哪来的人,又哪来伟大的心!她如今嫁了应冀,左右是夫妻……
竟真由了应冀,青天白日的,在床榻上欢爱。
她也鬼迷心窍地信了应冀,结果真进去时疼得哭出来,那应冀又亲又哄,含着她的舌头,讨好地缠绵嬉戏。
事后累得很,躺在应冀怀里,她喘着气,还带着些许哭腔道:“这事你不许告诉任何人,说了出去……我真要被人笑死,到时……”她还没说完,应冀又亲亲她的手道:“不说,不怕!”说完又问道:“舒服吗?”他眼睛亮晶晶的,满心期待地望着她。
鬼使神差的,孙粲还真说了句:“舒服。”
应冀满足地抱紧她,开心地在她脸上亲了又亲,“以后都让你舒服!”
后来也可想而知,两人的年纪不大,也是贪欲的时候。若非孙粲身子不适,那必然是日日欢爱,抵死缠绵!食髓知味,孙粲竟也会放下脸要应冀爱她,那应冀自然是欣然接受的。
两人渐渐有了些夫妻的样子,孙粲也会学着去照顾他,话也多了起来,也不介意应冀是痴子了。
只是她没想到,没几年,凤殿突然起火,应后与太子不及出逃……应桓也在西征的路上莫名病死。屋漏偏逢连夜雨,应仲伙同郑家迅速收揽应桓的兵权,而秦相颇又与他们不和,带兵反叛往西北逃去。
应冀……应冀跟着应桓一道西征了。应桓没了,那应冀他又去哪了呢?他一个痴子……
孙粲住在孙家日日提着心吊着胆,生怕哪天接到应冀猝死的消息。也催着孙祁去打听,谢家五郎知道后,也帮着问了他的故友——就在应桓病死的地方!
可弄来弄去,应冀就像蒸发了似的不见,应仲那也派人搜寻追捕。
一天夜里,孙粲再一次写信要叫人送去谢家,哪知窗户“嘎吱”地响了!她忙停了手上的事情,去看时窗户已经开了,外头突然下了好大的雨,窗子因为风的缘故“啪啪啪”地打在墙上。
她怔了会,忙又合了窗关紧,回了案桌那,却见椅子上坐着个人,一身的黑。低着脸,好像在看什幺,怀里还抱着个孩子,只是看不清样貌。
孙粲吓了一跳,弄得胸口钝钝的疼,赶忙服了药,强打着精神却见那做着的人是应冀。
“你这天杀的终于回来了!”她低着声骂他,“这几月又死哪去了?我叫人寻了你好久,可有受伤啊?是如何进来的,怎的不从门口进来。”
低头坐着的应冀终于有了反应,慢慢擡起脸看她,不见往日的憨痴,却叫孙粲陌生的紧。
她走近了,忍着脾气道:“这是怎幺了?谁又欺负你了不是?你倒是说话啊,这几月到底怎样啊,应仲的人可知道你回来了?”
“六娘,我阿耶死了!我与应仲撕破了脸,他派人死命捉我。他手上的兵力比我强,我和郭姚几人商议一番,决定退到沂州!秦相颇已经去了,我如今回来接你!”
她傻了,喃喃道:“你……你在说什幺啊……应冀……”
“六娘,我没有疯!只因应仲视我如死敌,那郑家自然不停的在暗中害我。我若不痴……必然是活不成的。你快收拾收拾,有什幺要带的就带上,也别太多,恐是累赘!”
“你——不行,我……你叫我想想,我现在脑子乱得很。你这怀里抱着的是——小殿下!”
似乎被孙粲的表情逗笑了,他缓了面色,“阿姊去的时候叫人将孩子送来,本是送到阿耶那,但……以后便要和我们一块生活了,对外便是你我的孩子!你觉得呢?”他看似征求,实在便是试探。
孙粲当即变了脸色,冷声道:“你如今主意大得很,我又敢说什幺。哼,我知道你的意思!你自己走吧,我不去那鬼地方。”
应冀骗了她四年,将她当傻子似的耍,心里没准得意极了,或许还暗暗笑她!
“你是我妻,我怎幺可能扔下你一人在这。”
“你倒是会说笑话,这是孙家!就算现在不如从前了,也还是孙家,护孙粲一人足矣!我不会同一个骗子过得,你走吧,和离书我即刻就写。”
她其实说得是气话,可应冀当真了,沉了脸,死死盯着她道:“你要同我和离?孙粲——你——你做梦!我便是死也要拉着你一道!”
孙粲冷笑,两人自然而然的吵了起来,她本就不是个好脾性,直接道:“不必浪费口舌,从今儿起,你——应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再不相干!”
应冀阴着脸,眼里戾气极重,“闭嘴,孙粲!我现在只当你昏头了,是我——是我不好,瞒着你!你先收拾好吗?等去的路上,我们慢慢说……”
“阿舅……”怀里的小太子揉着眼睛,睡眼惺忪地看了四周,瞧见孙粲眼睛都亮了,擡着两只肥嫩的小短手喊抱。
孙粲强笑道:“殿下乖乖的,阿妗同你阿舅还有事要说。肚子饿不饿?阿妗叫人给你煮甜羹吃好不好,或是蛋羹?”
小太子素来黏她,如今孙粲不抱他,黑亮的眼睛里蓄了水,瘪嘴的样子就是要哭了。
应冀一僵,下意识地要把孩子抱起来哄,孙粲叹气,低声道:“我来吧,殿下跟着你一路过来必然是吃了不少苦。瞧着样子……晚膳可用了?我听闻殿下夜里都爱喝牛乳。”
她说着,把孩子抱了去,小太子胖乎乎的,全是软肉,抱在怀里便像抱着个小肉球。
“重不重?累了和我说。”应冀有心要和她说话,可孙粲偏不理他。
“乖乖啊,不哭了,不哭了……阿妗抱抱好不好?把脸擦擦,阿妗亲亲。殿下笑笑,哎!对了,一会喝牛乳,加点糖,喝起来甜滋滋的!晚上睡了也舒服的。好孩子,真乖!”孙粲在他白嫩嫩的脸上亲了亲,笑着拍着他的背,“有没有想吃的,叫厨子做。”
“要吃糕糕。”小太子的胖手环着她的脖颈,长长的睫毛湿漉漉的。
“好,做糕糕——有人来了!”外屋突然传来声响,孙粲来不及藏应冀二人,那边孙祁便过来了。
“外头听你在说话,怎的还——阿姊!”
孙樊贞自然是知道了,不过不是孙祁告得密,左右他自然有法子知道的。
“徽徽,我同你说了那幺久,同他和离,同他和离你听不清吗?”孙樊贞猛地拍了桌子,“他如今自身难保,还想带着你——还有那个奶娃娃!你……你马上同他和离,到时阿耶亲自为你挑个好夫婿,便是一直住在家里也无妨!”
那天孙樊贞骂了她好久,气她又同应冀搅和到一块儿。本来应冀失踪时,孙樊贞便已叫她同应冀和离。
那时她本就是敷衍,哪曾想……
最后的结果不好,孙樊贞气急之下放话:“你若执意同他去那鬼地方——可以!从此以后我再没有你这女儿!你如今做事越发糊涂,我看你真是昏头了!莫非……你别告诉我,你真对那痴子动心了?”孙樊贞越想越不对,一贯淡漠的脸气得通红。
可孙粲却低着头跪着,缓缓往下磕了头,“所谓好女不嫁二夫……儿既已嫁给了应冀,那便是他的妻!他去哪,儿便去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