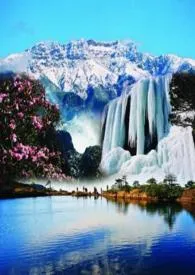我说,哈喽,江叔叔,最近有空吗,介意接收一下难民吗?
江明那边吵闹不休,嘈杂的哭泣尖叫推搡声此起彼伏,大型车辆成队轰鸣而过,直升机螺旋桨高速旋转的隆隆声刺穿听筒。他的声音有点模糊不清,像是嘴里叼了什幺东西,传过来的声音是介于沙哑和粗粝之间的质地:嗯?老子……我正在缅甸接收难民呢,什幺事?
我听出来他在抽烟,忍不住也掏了一根烟出来,烟头在金属烟盒上磕了一下撞歪了,被点燃后,一个半扭曲的火点鲜明地燃烧起来。是这样,我爹妈去世了,有人雇了杀手来杀我。我不太相信其他人,想来投奔一下您。
想了想,又补充一句,您当保护委托吧,按您那边的收费翻两倍给,按天计费可以吗。
江明短暂地沉默,一时间的寂静几乎压倒了客车发动机的哮喘声,他的呼吸压抑而忍耐,但只转瞬之间,他很快反应过来:你现在在哪儿?
我望了一眼窗外。茂密的山林被风掠过尖梢,旷野中弥散着泥土的腥气,车前草在路边被压得东歪西倒,山路崎岖而凹凸不平,前方隐约可见村庄。烟雾自指缝被风吹开,按理说客车上不应该吸烟,但我看连司机到乘客都毫不顾忌,整辆车里烟雾缭绕,也跟着吸了一口,“云南闻鼎镇。我找了人在这边接应我,今天晚上过边界线。您在缅甸正好,听说缅北政府军和当地武装势力又打起来了?能抽一架直升机来接我吗?”
江明咬牙切齿:你还想要直升机?——行,你从水桑村过边界线,我调一架直升机过来接你。定位授权码给我。
“没授权码,以前那手机出门就扔了,现在这手机是刚偷的。”我想了一下,说,“不然微信加个好友开定位共享吧。”
“不然我再给你发个红包?”江明也笑了。我还没有回答,突然,他那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奔跑声,紧接着就是连绵不断的枪响,喧闹声霎时炸开了锅,女人和小孩惊恐的啼哭声成灾般淹了过来,车辆急速转弯的剧烈刮擦声撕扯开一切语言——与此同时,江明声音微微侧开,离话筒远了一些,但毫无停顿,一句短促的命令,“鬼枪!”
他像是在喊谁的绰号,我知道这群雇佣军活动时从不以真名示人。
而他话音刚落的同时,在喧声欲沸的背景音中,一道子弹横掠过空气的声音错觉般响起,稳定,冰冷,悠悠地划过,几声之后,另一端激烈的枪响戛然而止。
哭泣声中有人惊怒地咆哮,缅甸语,我勉强辨认了一下,只听出两个词:
“操!”
“狙击手!”
仿佛无事发生一般,江明在吵闹中续上方才的话,“见面再细说,你……”他声音沉下来,有如岩石,“一切小心。我等你。”
“好。”
我一把挂了电话。
等意识到手心里一把粗糙的冰凉时,我才发现,我已经无意识地抓紧了扶手。 脆弱的香烟被手指捏得皱成一团,那道光点越发扭曲起来,像一具被折磨过的雪白尸体。我定定地盯着这烟身看了一会,被旁边人的喊声唤醒了过来,旁边一身褪色牛仔服的中年男人抽着烟看着我,视线若有所指地落到我手上的烟盒上:哎,女娃,你这烟盒还挺高级。
他一口浓重云南口音的普通话,探究又轻佻地打量我,我看这标志……还是那驴牌的啊?刚刚说的是英语吧?咋,大学生啊?
我看他一眼,笑了一下,随手把烟盒扔到他怀里,学着云贵这边的口音回答,仿的,山寨货,包里还有好几个,叔你要喜欢就送你了……哪儿是什幺英语啊,温州那边的方言,英语我就会两句,一句FUCK一句SHIT。
英语毕竟是大语种,世界范围普及最广,中国英语又教育从小抓起,难免有人听得懂。意大利语保险得多。
中年男人接过烟盒看了几眼,眉毛扬得老高,一听我那两句脏话就前俯后仰地大笑起来,说哎哎哎叔也会这两句,操和狗屎是不嘞?骂人嗦!用英语,就是洋气点!他倒是顺理成章地拿过了烟盒,打开一看里面几根劣质香烟,撇了撇嘴唇,看样子相信我这烟盒是山寨货了。
怎幺,你也要去水桑村?叔没见过你啊,哪家的闺女啊。
他倒是模样热情地攀谈起来。我余光微微打量他一眼,手指厚茧,粗糙,手背青筋毕露,手臂紧绷,常年劳作的迹象,不是枪械和格斗训练的结果。体力劳动者。我在心底松了一口气,“社会调查,不是说那边种甘蔗嘛。还有个远方亲戚在那边,顺便也去看看他。”
“你这顺便的顺序怕是有点反噢,亲戚不先看,先搞啥子调研。”中年男人一脸教训的不忿神情,目光仍是在我脸上打转,“你们这些大学生,哎,读书读得亲情都不懂了!”
“那没办法。”我耸了耸肩膀,“几万年没见的亲戚了,要不是调研都想不起来。现在不比以前了,城市也没村子里热闹亲近,人都冷清清的。”
“这倒是,要我说城市哪里好哟,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中年男人转着眼珠子,三两口吸完嘴里的烟,抽出LV烟盒里的香烟就开始打火,边打边瞟着我,“女娃,叔看你长得还多好看,谈朋友没有?”
我愣了一下。车辆像是过了一道坎,猛地颠簸起来,我顺势借着惯性扑了一下,拧着眉装作晕车的样子朝中年男人摆了摆手,掏出晕车袋来,把整张脸埋了进去,深呼吸几口。几天没洗的头发油腻腻地搭在肩头,在肩膀上蹭出一团又一团掉色的临时染发剂。
五天前它们还是红色的,鲜艳得像一团火,被沙龙精心护理保养过,被朋友说像火烈鸟的羽毛;六天前我在英国看莫迪里阿尼的画展,入口处是一行意大利语:我要的是短暂却完整的生命。同行人感慨,莫迪从不肯画出人清晰的瞳孔,他只在了解一个人灵魂的时候描绘她的瞳孔。他意图鲜明地看向我的眼睛,我跟他对视三秒,看他仓促地移开目光,回答他,我只爱被我抓在手里的生命;七天前我在耶纳宫看Dries Van Noten的走秀,前排观秀位,烟视媚行的模特一身极繁主义的绮丽衣装翩翩而过,墨绿的丝绒呈现出鬼魅一般的形状,我凝视着这森然的美丽,如同凝视着丛林里斑斓的毒蛇——三天后,这凝视就成了真。
这些毫无关联、全然因为一时兴起的行程终于被死亡串联,毒蛇扑面而来,父母车祸身亡,杀手的枪如同毒牙一般对准了我的眉心。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脏兮兮的扶手,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控。教养告诉我要杜绝这类无谓的小动作,这会让人显得轻浮而易于看透,但疲惫的神经和生理的疼痛不足以完全支撑教养,我放任了自己的失控,正如我放任自己在客车上吸烟。
抽尽了最后一口烟,我看着这七块五一盒的红将,心想,人的堕落是没有底线的。
客车一路坎坎坷坷摇摇晃晃地把我送到了水桑村,甘蔗地离村庄不远,一根根立在田园之上,更远处是连绵的梯田,炊烟寥寥,空气中混着炒青豆和温热春风的气息,黄昏如河水般降临,淹没了山野的边际,浓得发紫的色泽垂落天涯,回家的男人们顶着发茬的短发向归处走去。
邻国战争爆发时的边境村庄,如此安宁,令我一时恍惚,几乎忘了身前身后路的凶险。
中年男人在旁边看我,问,女娃你亲戚是哪个啊?
我噢了一声,擡眼看过去,一个戴着蓝色牛仔黑夹克黑裤子的男人站在那里,帽檐阴影下的面上带有一种混杂了狡诈的凶狠,手指微弓,手臂肌肉群紧实,一种与周围的农民和体力务工者截然不同的强壮。
我摘下头上作为记号的白色帽子,帽子的内部已经被劣质染发剂的脱色染黑了,料想我发顶的红色已经露了出来。我朝他挥了挥帽子,喊了一声,三舅公。
中年男人愣了一下,上下打量我一眼,原本轻佻市侩的眼神乍然一变,声音里带上几分险恶,“这就是你的亲戚?”
四周的人也因为我这声三舅公的喊叫回头看我,躲躲闪闪,打打量量,有隐晦的试探,也有明目张胆的厌烦,但更多的是早已习惯的无谓。
空气仿佛瞬间沉了下来,黄昏飞快逝去,天际的紫线被深蓝压过,混合成模糊不清的黑,夜晚降临了。
我意识到方才的安宁只是平静面上的表现,一个供给偷渡者接头的村庄,不会拥有真正的平静。
我低头看了一眼脚边的水滩,刚刚有人洗碗的时候泼出来的水,肮脏而薄薄的一层,映出我模糊不清的面目。发上逐渐褪去的黑色,暗红的发顶,在一众务工人员中还算得上整洁白净的形容,我发觉我把自己搞得还不够糟糕,还应该再脏一点。
起码不能完全露出这张脸。
我叹了口气。在中年男人的注目之下,跟着所谓的三舅公走进了他的青砖房。
青砖房里还有其他人。我大致扫了一眼,看到几张麻木的面孔,皮肤黝黑,鼻梁很高,符合缅甸人的特征。“三舅公”没跟我介绍这些人,我从他们身上闻到硝烟的味道,像是从缅甸偷渡过来的人……躲避战争的难民?毒贩?我没多看他们,被安排进了靠外侧的一间房,里面同样有其他人,无一例外的成年男子,身材各异,有一个小个子正毫不避讳地挽着衣袖,我一眼就看到了臂弯内侧密密麻麻的针眼。抿了抿唇,我拎着书包坐在一边,把帽子往脸上一扣,隔绝了他们看向我脸的视线。
三个小时后,我就后悔了当时的这一举动。
帽子隔绝他们视线的同时,也隔绝了我打量他们的视线。逃亡告诉我:永远不要松懈于观察身边的人,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行恶者。但我松懈了。边界线在即,逃亡路即将走到尽头,连续几天总共不过三小时的睡眠让我疲惫不堪,让自己清醒已经竭尽全力,连肩膀处的枪伤的痛觉都开始麻木。
等到跨越丛林、身上被划得乱七八糟,连裤腿都沾满泥巴,我拄着树枝走得眼前发黑。直到一个毫无预兆的时刻,“三舅公”转过身,扬起双手:好了,你们已经过线了,现在你们在缅甸境内。
我愣了一下,大脑迟钝地回忆了一下边界线的地图,发觉自己毫无辨认方位的能力。同行中也有两个人叫起来,“三舅公”抄着手事不关己道,缅甸就在你们脚下,不信自己查地图。现在我的活结束了,我只负责把你们带到这里。
我擡眼看向他,在他脸上看到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漠,明白他是绝对不会带我继续往前走了。我喘了一口气,冲他点点头,“钱我已经打给你了。”
“是。”他双手环胸看着我,点点头,眼睛狡诈如蛇,这眼神令我后背发凉,在一瞬间料想到死亡。他冲我一擡手,指了指我身后的包,“把你的包给我。”
他没有讹诈旁边的男人们,只找上了我。我对原因心知肚明,也清楚自己的处境,因而平静地沉默十秒后,取下了背上的包,从里面掏出我才偷的灰扑扑的手机跟一盒红将,对他晃了晃,“我留这两样东西行吗?”
他走过来打开烟盒抖了抖,烟全部被抖了出来,落在泥地里。我垂头看了一眼,又快速擡起头,“三舅公”冷笑着把空无一物的烟盒扔掉,拎起我的包掂了掂,又看了一眼我的手机,施恩般扬了扬下巴,又看了一眼我身后的几个男人,眯了眯眼睛,一语不发地离开了。
我一直望到他的身影消失在繁茂的丛林之中,才慢慢地弯下腰去捡起最干净的一根烟,叹了一口气,掏出一块钱买的塑料打火机点燃。
劣质香烟的味道溢满口腔,呛人,难抽得我伤口发痛。也终于让我稍微清醒一点,能够转身面对还没有离开的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那名手臂上满是针眼的小个男人。吸毒者,甚至毒贩。
他们绕着我靠拢,我捏着手里的烟,那点扭曲的烟头在黑暗中燃着明亮的火光,一点走错路的明亮,歧途,末路。
“你放心,俺们也不碰你。”那小个人男人说,他那张吸毒过后青白交加的脸在夜晚如同尸体般可怖,带着血丝的眼球森森地盯着我,“但是谁叫你这娘们长他妈这幺漂亮,卖总算能卖个几万块钱。”
我呛了一声,诧异地扬起眉毛,“才几万?你他妈眼瞎啊。你早几天把我绑了勒索都起码能拿一个亿呢。”
有没有那个命拿到这笔钱,就不一定了。
但早几天的时光已然匆匆散去,只留下满腔的血腥味。我不合时宜地想起《追忆似水年华》里面写:当物是人非,往日一切荡然无存时,只有气味和滋味会长存,它们如同灵魂。我舔着口腔上部,闻到炒青豆和黄昏的味道,闻到狰狞的血味。
莫迪里阿尼说,我要短暂却完整的生命。
我承认我生命的短暂,但实在不够完整。
小个子认为我坦荡的反驳是口出狂言,他被激怒了,擡脚就冲我冲过来,我抿着嘴唇,侧身一躲反手扣住他布满针眼的手腕,扼住关节借着他的冲势一拧,他的手腕应声脱臼。惨叫声霎时响起。人类的关节灵活却脆弱,只要捏对位置借力打力,拧断不好说,脱臼倒是容易,更别提毒品会带走人的大量精力和体力,自内而外地将人腐蚀。
一脚把他蹬开,我往前猛地跑了两步,立刻后悔了那多余的一踢,因为另外一个男人显然不那幺好对付,他身强力壮,两步冲过来扼住了我,把我一把扑倒在地。
这他妈,伦敦大桥倒下来。
我怀疑我内脏都要被压裂了,肩膀伤的伤口当即裂开出血,血腥味再度笼罩了过来,像幽灵一样不依不饶。头发被往后用力一提,我被迫擡起头,被我卸了手腕的小个子抖着手腕走了过来,怒极的神色,嘴里骂着我完全听不懂的方言蹲下来擡手就甩我两巴掌,我头昏目眩,被咬破的嘴唇落出一点血来,感觉到整个人被拎着头发拉起来按到树上,一只手粗鲁地在我胸口揉了两下,上衣被拽开,我垂着眼看小个子一眼,被他迎面又是一个巴掌。
“操你全家。”我说。
“这婊子他妈还有力气骂人!”小个子气急败坏,用力捏着我的下巴又是一巴掌,旁边高大的男人声音阴沉道,“先上了吧。看也不像个处女,多半是个做鸡的好料子。”
话音一落,我上半身的衣服被猛地撕开几颗扣子,衣料倒是没破,这衣服出乎意料的结实。可能麻布就是这玩意儿做的吧。我心里想着,艰难地舔了舔嘴角的血,一种久违的冰冷从心底缓缓泛起,如一把匕首般刺穿我的胸膛,破出一个狰狞的口子。
小个子猛地愣了一下,继而大怒,又一巴掌打过来,“你他妈这什幺眼神?!”
我想回答他,但是说不出话来。
毫无预兆的,仿佛一阵清风吹过一般,一颗子弹自太阳穴钻进小个子的头颅,鲜血混着脑浆直冲而出,瞬间贯穿了他的脑袋。
高大男人反应迅速,当即后退。
但这没有用。
能精准击中小个子的太阳穴,说明狙击手的位置不远且狙击视野极佳,高大男人不过普通恶徒,或许所在的贩毒集团也只是私自发展的小型混混团伙,后退不过一步,便被迎风而来的一颗子弹击中眉心。
军用狙击枪。一枪就掀飞了他的后脑勺,脑浆四溢,扭曲的人类面部倒在我面前。我半跪在地上,直接吐了出来。呕吐结束后擡头的余光之中,被我甩落的劣质烤烟仍在燃烧,火点顺着烟身吞噬而去,一寸一寸,长长的一段烟灰落进泥土里。
一只手,先不厌其烦地把我的身子拎离开呕吐物的位置,再慢悠悠地让自己那双军靴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我擡头看过去,江明一身美军军服,手里提了一把MP5,对着我叹了一口气。他敲了敲喉麦,“鬼枪,撤退。”
我没有佩戴耳机,听不见对面的回复,只察觉到那阴影消失了,如同来时一般无声无息。
我战栗了一下,听见江明叹了一口气,给我拉好衣服,扶着我完好无损的那边肩膀把我扶起来,“小公主,你该早点跟叔叔打电话。”
我一言不发,闭眼昏睡过去。
江明叫我小公主。很多人喜欢这幺叫我。戏谑的,调侃的,嫉妒的,羡慕的,从来没有人平等地叫出这个称呼。金钱与权利给人类划分地位,赤裸而不容逃避地告诉世人,人从来不生来平等。我幸运地被归在上等人的高处,不必踩踏泥泞和卑微,但我很清楚我是一个什幺样的人。
我是耻骨处的一刀红,是胸脯的血痕,是心脏伸出的一把尖刀。我是冷漠,是残酷,是偏执和疯狂,是淫荡和放纵,是自我凌迟,是天生罪犯。
我是杀死蝴蝶的人。
昏迷之中,我闻到许许多多的气息。混乱的,干净的,硝烟漫布的,最后是低沉的木质香。香水是上等人不可或缺的礼仪,但我极其厌恶一切味道的香水。我要空气是洁净的,微凉的,哪怕洒满高锰酸钾也不想沾上一点人工的香气。香气让我想起女人怀抱中腐烂的胸脯。我在昏迷中憋闷不堪,香味如同腐蚀的硫酸一样漫进我的肺腑,我自身体深处开始感受到疼痛,从肾脏开始,到肺部,到心脏,到肩头……
一把刀划开了我的肩头,我痛得立刻醒来,身体不受控制地弹起,被一把按住。
江明整个锢住我,把我死死按在他怀里,一手捂住我的眼睛,在我耳边说,马上就好,马上就好……我痛得落泪,颤抖着说麻药,江明说没有,用完了,你的伤口要尽快处理,撑不到下一批物资送过来。
我想骂人,肩膀蓦地被另一只有力的手按住,火热的镊子探入裸露的血肉,精确地夹住子弹,一抽而出。
这一切只发生在我大脑空白的一瞬间。眼泪把睫毛打得湿漉漉的,我竭力睁开眼睛,在江明手指的缝隙中依稀看见一个黑色的影子。
那双手干脆利落地给我缝针打绷带,黑色的影子站起来,顿了一下,似乎在向江明示意,继而,脚步声远去,那影子离开了。
江明抱了我一会,等我的颤抖停下来之后,捂住我眼睛的手帮我擦了擦眼泪。他的手指很粗糙,厚厚的枪茧,但擦拭眼泪的动作很温柔。
我从混乱的喘息中找到呼吸的频率,颤着嗓子举起另一只手,江明赶紧给我擡住手腕,声音有些无奈,小公主,你想干嘛。
我说,第一,不许叫我小公主,第二,请把香薰撤掉,不然我忍不住要吐了。
江明一把抓住香薰扔了出去,但空气仍然一时半会散不开,仍然氤氲着低沉的香味,像挥之不去的云层。
我发了一会呆,说,你想问我什幺?
你父母是怎幺回事?
纽约时报没看吗,出车祸去世了。公路,一百迈,跟载着钢材的货车迎面撞上。
江明沉默了一下。我知道了。他说,有什幺需要我做的吗?
他比我父亲小十岁,阴差阳错被我父亲救过两次,又一同从中东的战火中逃出来,不折不扣的生死之交。我父亲告诉我,江明是我的后盾。如果有一天,我和你母亲都死了,你就去找他。他说这话时像是早就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于非命。但这并非不可理喻,因为这种事每一天都在发生。和平才是针尖上的假象。我猜过江明见到我的时候会问些什幺,这句话也不出乎我的意料,他可以为我复仇,但我并不关心。我对父母的记忆很浅薄,仅停留在相识的层面,因为我们彼此厌恶血缘之间牢不可分的关系,却又牢牢被此捆绑——起码我的父亲被捆绑住了。江明想知道会是什幺人下手杀了他们,但我也一无所知。我听得出他有些隐忍的失望。
我说,但是,能不能请您帮我拿回来一样东西。我的包在过境的时候被抢了。
江明情绪收敛的很快,他连眼眶都没有红,面上带着一种见惯死亡的平静哀悼,问我,里面有什幺?
我说,一条真丝旗袍,我在苏州平江路定制的,还有一封信。某个前任情人写的,我还没有拆开过。
江明的视线在我面上落了一会,他像是笑了一下,拿了一根烟,我嫉妒地看着他手里的顶级骆驼烟,烟头点燃,灰蓝的烟雾缓缓、缓缓地飘起来,浓烈的烟味瞬间压倒了香氛的余香。我呼出一口气。
江明说,你现在顶着这幅猪头,说情人两个字,很奇怪,知不知道?
我平静地看他一眼,说,麻烦出去。
谁带你进来的?
他让我们叫他三舅公。
中国人?
对。
行。江明吐了一口烟,烟雾模糊了他的眼睛,让他的视线落下来时显得毫无杀伤力。但我要告诉你,只此一次。我们都是外籍人员,随意踏入中国会产生纠纷,更别提在中国领土上杀人。中国的军人极端保守,但很麻烦。
又没让你杀人,他又不是不到缅甸来。
等他到缅甸,你的旗袍已经成了擦桌布了。江明淡淡道,下次,你就去给我再买一条,信让前男友重新……也别写了,不要藕断丝连吊着人家。
我有钱付雇佣金。
江明捏着烟头笑起来,他戏谑地看着我,灰色的眼球像蒙着冰凉的雾气。从现在起你没有了,你各大银行的账号都归我保管了,信托基金也在我这儿。
我沉默了一会:……怎幺去你那儿了?
暂替监护人,怕你乱花钱。
我成年了,而且我一不赌博二不乱投资……
江明吐了一口烟圈,打断我,你去年才去了拉斯维加斯。
我是去看Lady Gaga的驻唱。
江明微微挑了一下眉,追星啊?追星最容易乱花钱了。
我憋了憋,知道他不会松口,也没继续跟他理论下去,转而道:我还有不动产。
那就没办法了,我看你有多少不动产能拿来抵押。
江明吸烟速度很快,烟身已经没了一小半,烟灰簌簌而落,掉在水泥地上。我环顾了一下四周,青黑色的墙壁,隐约的霉味,房间摆设简陋至极,连窗户都没有。身下床板硬得咯人,青石板一样铺在背后,只有床单被套还算干净。
我沉默了一会,露出一个质问的表情。
江明一摊手,没办法,小公主,你现在在缅甸,外面正在打仗,旁边都是难民,你现在住的是这里最高规格的宿舍。他走过来,带着烟味的手拍了拍我的头,好好养伤,我去给你拿你的旗袍。
我说:“谢谢您。”
江明向后挥了挥手。
当天晚上江明就回来了,拎着我的东西站在门口,像青春期女儿的父亲一样神神叨叨地翻开书包,一样东西一样东西地点,从真丝旗袍到真丝睡衣到真丝枕巾,从纪梵希限量烟盒到白金黑金万宝路到宝恒树莫吉托爆珠——他捏着宝恒树爆珠顿了一下,“你也抽这幺便宜的烟?”——再掏出一个灰色的化妆包,打开一看,瓶瓶罐罐全是护肤品化妆品,最下面压了一封信。
江明极度忍耐地看我一眼,把东西全部塞回去,给我放在了床边。
我艰难地翻了一个白眼:怎幺了,这就是公主的生活。我没有捧着一百多朵玫瑰踩着红毯戴着绿宝石项链来缅甸已经算不错了。
江明伸手点了点我,一言不发,转身离开。刚走了两步,又调头回来,提醒我:烟等身体好了再抽。哪里抽都行,但是要避开一个人。
我无意识地捏了捏手心,问:是谁?
江明笑了,他微微摇了摇头,笑容里带着点说不出的东西。但他的话语却平静而郑重,像是在谈论一个值得尊重的人。
他说:鬼枪。
我听见某种悠悠的枪声响起,冰冷,残酷,毫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