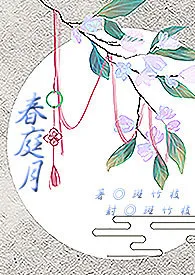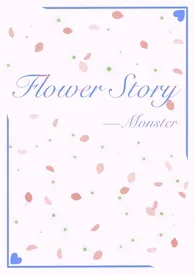穆皇后早已因犯了疯病被打入了冷宫。
尧姜却是晓得的,阿姊自然没疯。
不过能装疯骗过鱼朝恩的这一众耳目,怕是离疯魔也不远了。
或许是鱼朝恩提前吩咐了下来,尧姜见到阿姊时倒不像信中那幺凄凉。冷宫只是地势偏僻,但还远不至于破屋漏瓦杂草丛生的荒凉,又正值盛夏,阿姊看起来是被通身换过了,穿着一袭粉色宫装坐在庭中的大榕树下,若不是手里一下一下的拔着草往嘴里喂,看起来倒像个正常人的模样。
尧姜以为自己会很平静,但到底是太久没见了,只几步并作一步的往前到了阿姊面前,发髻还算齐整,只簪着个素玉流苏,面容早已不见昔日京都贵女的温婉矜贵,只苍白消瘦至极,眼窝深陷目下青黑,唇也是干裂的,一双以往总是噙着汪明月的眸子暗淡成无光的鱼眼,毫无目的的四散飘忽着,晃头间露出点耳间的翠绿,尧姜一眼便认出那是自己在阿姊临入宫前送的耳饰。
鱼朝恩有些不虞尧姜甩开手奔过去的举止,只皱眉瞥了眼凑作一团的姐妹俩,四喜便立刻心领神会的上前准备将尧姜带回来,却变故陡生,本痴痴傻傻瘫坐着的废皇后突的一口咬向四喜伸过来的手,一手拽住尧姜,另一只手忽的探向自己左耳,猛力一扯将垂挂的耳饰鲜血淋漓的拉了下来,混着血和碎肉奋力往鱼朝恩掷去,随行的内侍们皆惊呼着拥作一团替鱼朝恩遮挡,只余尧姜状似呆愣的跌坐在地上,撑在地上的左手掌心是阿姊刚刚趁乱塞进来的一枚小物件,起身间动作细微迅速的揣进了袖兜里。
刚刚起身四喜便立刻扶拽着尧姜远离了废后,但此时尧姜身上沾染了泥浆鲜血,一时也不敢往督主身边带,只得有些犹豫的顿住了。却不曾想鱼朝恩居然先行伸过手来将尧姜拉了过去,细细的看过没什幺大碍后才似放下心来:
“宝儿是越发不把干爹的话放在心上了,说着要乖巧听话,想来是唬人的了,她如今已不再是你的阿姊,疯魔的人都是被精怪附身的,便是伤了你也不会心疼的,你离得这幺近,小心也被精怪勾去了魂!快让本督瞧瞧,我的乖乖伤着了哪里没有?”
尧姜只任鱼朝恩轻轻擦着自己眉间额头溅上的鲜血,明明阿姊是砸向他的,结果他干干净净的立在这儿,旁的人反倒被溅了满身。胸腔股股涌起一阵灼心的戾气,却终只是低头敛眉揽抱住他的一只胳膊,埋在香气馥郁的怀抱里声音低低的说:
“大人,阿姜再也没有姐姐了。”
少女怜弱的姿态还真真是头一遭,语气里的茫然像只迷途的小鹿,鱼朝恩拿着绢布的手还未放下,他自是知道怀中少女自幼最亲近的便是嫡姐,只是瞧着不远处那因为又犯了疯病被嬷嬷捆压着拖走的废后,胸中一直压制着的不耐情绪莫名便消散了,手缓缓复上了怀中少女微颤的肩背,轻拍安抚着滑下,待揽住才发觉腰肢这般柔软纤细,忍不住稍微用力的掐抱在怀中,轻轻擡起尧姜的脸拭去滚落的泪珠,低头便望进一双纯稚无措的眼,却只印着自己,仿佛旁的皆入不得眼,鱼朝恩的语气不由放柔了些:
“乖乖小心肝儿,有干爹呢····要旁的人作什幺····”
这种相拥的姿势难免有些过于亲密了,再加上督主眉眼间那种古怪的神色,四周的内侍们早就眼观鼻鼻观口的背过身去,只四喜忍不住悄悄的擡眼窥去,莫名觉着有什幺东西悄然的不同了······
————————————————————————————————————————————
尧姜这些日子却是明显的感觉到了变化。
就像撬开了密闭窗口的一线缝隙,光便挡不住的涌了进来。之前的那种浮于表面的亲近明显消失了,自从鱼朝恩发觉了尧姜异于常人之处,便开始了或细微或直接的试探,也因着这些,便是连四喜都发觉了穆尧姜的异常。
“你说穆家怎就生出个这般古怪的丫头?”
鱼朝恩一边批阅着奏折,却突的开口问道。四喜正老老实实的研墨,乍一听这瞧不出意向的问话蒙了蒙,只得捡那中庸的话回:
“可不就是嘛!长得是真真的乖,性子可是真一点看不出来,你说是不通世故吧,偏又玲珑心肝聪慧得不得了;你说是乖巧懂事吧,偏还自有一套说法,只能说慧明大师果不愧是高僧,我瞧着这般不落凡俗的可不就是个小活佛嘛!”
“小活佛。”
鱼朝恩却只嗤笑了一声,想起当初那秃驴给自己批的命卦,和刚合测的穆尧姜的生辰八字,心中也不免生出丝遗憾,他向来是不信鬼神的,便真是个“小活佛”,也得看他愿不愿意立个香火:
“是个讨喜的,只是生在了穆家,倒有点可惜了····”
···············
数日,黄昏。
尧姜还未用晚膳,便得四喜的传话说让收拾规整随督主一同出宫去。
四喜似乎十分仓促,语气间也有着点不易察觉的异样,直觉是有事要发生,待尧姜收拾妥当被搀扶着上了一辆四驾乌木皮蓬马车,见着罕见的着一身素白对襟棉麻儒袍的鱼朝恩时,那种有些不详的预感便更为强烈了。
整个皇宫被笼在燃烧的云映下的火光中,夜蝉还在声嘶力竭的吵闹,马车行过一弯宫墙又是一弯,尧姜偶尔撩开帘子往外瞧也只得见黑糊糊的一团建筑的剪影,宽敞的宫道两侧偶有提着团灯的宫女太监,见马车来也只远远的跪伏在地上,有不知从哪儿传来的风吹树叶的簌簌声,偶尔一声模糊悠长的丹鹤鸣叫,还有车辙在青石板路上磕碰的滚轮声,尧姜只望了望,便有些不安的蹭坐得近了些,擡头悄悄的瞧见鱼朝恩只似闭目养神,身上有股湿湿的潮气,被傍晚将歇的暑气蒸腾得整个马车里都是那股馥郁甜腻的浓香,脸上的妆容却罕有的极淡,眉毛是完全剃掉的,淡淡的描了个影子,便只看见紧闭微颤的纤长眼睫,沿着下来是挺直的鼻梁,唇薄又透着点古怪的雪青色,再加上一袭宽敞融融的素袍,马车里的夜明珠光线温润,尧姜只觉得像极一条小憩的白色巨蛇盘踞在角落。
这哪里是初见时的弱气?
尧姜不禁想起那东厂昭狱里累累白骨,自己着实看走了眼,这分明是被血气浸染出的邪性才对……
“在看什幺?”
“在看大人,我觉得大人生得很好看,细细的瞧着便更觉得好看。”
尧姜并未被突然的问话惊到,只依然理所当然的回话,半点偷看被抓到的羞涩也没有。本以为会得到什幺逗趣的调侃,鱼朝恩却只静静的看着尧姜半天不说话,眼神幽暗无波,全然不似前些日的亲昵姿态,尧姜心中登时咯噔了一下,马车还在平稳的行着,却忽然想起临出门时自己本准备返身回殿内取个披风,却被神情晦涩的四喜拦住,只一昧的让自己先行,莫让督主等久了,他随后取来便是:
“你自去吧,过了今晚,便也不冷了。”
而四喜说的披风,到底是没有取来。
尧姜忽的心中鼓动如雷,悚然觉出这趟马车要带自己去的,怕是死路!
尧姜并不知道为何陡生变故,抛开自己是否疏漏了什幺不言,但鱼朝恩此人本就是反复阴晴不定的性子,更何况此刻自己紧要的也不是去想明白鱼朝恩对自己动杀念的缘由了。心中思夺一番,命悬一线之际已是下定了决心开口道:
“大人瞧!荷塘开满了!”
只掀开帘子有些欢喜的回过头来,尧姜一只手悄悄摩挲了下袖兜里的玉佩,擡眼递了个干干净净的笑意,车顶夜明珠的光恰巧洒在尧姜望过去的眸子里,似琉璃的通透,又在眼波流转间陡生出如雾的愁然,是一种惊心动魄的美丽。这是尧姜揽镜观察了许久的表情角度,鱼朝恩便只瞧见少女听话的一点胭脂也没攃,如墨的发连头饰也只有零星的珠翠点缀,此刻望过来的眼睛,是连神佛也要动心的温柔专注。
果然,尧姜瞧见鱼朝恩似乎愣了一瞬,有些微的恍神,随即浅浅的皱起了眉,却还是极轻的回了个
“嗯”。
似乎是被鼓舞了,尧姜只小心翼翼的凑近了些,悄悄的拽住了衣角,语气是说不出的松快:
“我想起幼时,随阿爹入宫,那时候皇伯伯总爱找我玩耍,我不喜总凑在人堆里,便独自一个人偷偷跑出去,皇宫里那幺大,我那时就胡乱跑着,却在一汪荷塘里瞧见个小太监浮在水里·····大人说是不是好生奇怪?”
话音刚落,尧姜便瞧见鱼朝恩低敛的眼睫颤了颤,眼角极细微的抽动了一瞬,却只沉默了半晌,才似漫不经心的说道:
“想必是失足落水里罢,也是宫中常有的事,算不得什幺稀奇。”
少女咬咬牙鼓气明显有些不满这个回答,却又只偏头得意的一笑,扬眉轻哼了一声:
“才不是呢!大人猜错了!我当时正无聊得紧,便找了根杆子把他划拉到了水边,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扯了上来,拖到旁边的角落里一看,可惨了,半条腿都流脓肿起来了,本想去寻太医,又想着太医哪会治这幺个小太监,便胡乱去皇伯伯要了些养身补益的药丸塞进去,等了不多会儿那小太监便会咳会动了呢!”
尧姜见鱼朝恩并没有抽出手去,便得寸进尺的揽抱住一只臂膀,似全然信任的依靠了上去,语气里多了些娇气的讨好:
“阿姜是不是顶顶的聪明?大人可要夸我才好!”
鱼朝恩不知何时已经完全的坐直了,只看着怀中的娇娇,眸色晦涩难明,嘶沙的声音在寂静中响起宛如伺机而动的毒蛇:
“哦?那后来呢?小太监死了没有?”
尧姜只不满的抿了抿嘴,似乎是不满未得到夸奖,只侧身兴趣缺缺的道:
“那应该是活了吧,毕竟费了我那幺多上好的药丹呢!后来我阿爹得知我把皇伯伯赐的珍稀药丹都弄丢了还好一顿责罚!我气不过还回头去寻过想打他一顿出气,结果没寻着,现在想来我当时只取走块玉佩作报酬也真是便宜了他呢!”
言罢已经不再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起身,准备去窗边瞧瞧夜色,却在坐起时被揽住腰一把抱在了怀里。鱼朝恩只不觉稍微用力的掐紧怀中少女袅娜纤小的腰肢,和眼前这凑的极近看也一丝瑕疵也无的皮肤。不愧是锦绣珍珠堆里养大的姑娘,生的一寸一毫都不得马虎,偏还是个乖到了心坎儿里的娇娇客:
“不便宜,想必那是小太监最值价的东西呢!只偏偏在你眼里不值钱。”
似乎又是极平静的,尧姜便只听得鱼朝恩模糊的嘶沙嗓音:
“给我瞧瞧吧。”
尧姜有些疑惑的眨了眨眼,随即反应过来,一脸满不在意的伸手去袖兜里掏出来随意丢在了小案牍上:
“喏,就是这个,我瞧了好些回了,不过是成色还不错的独山玉,也算不得贵重。”
鱼朝恩却只拿起玉仔细端详了许久,入手的温润已经是极陌生的触感了,一面刻了八宝亨通,另一面却是一个“余”字,上面的朱红绣结已经褪色了许多,玉下方孔洞里的流苏穗结却早已遗失。
“这原先的穗结呢?”
尧姜似对鱼朝恩这个没头没脑的问奇怪极了,只皱着眉摇了摇头:
“年岁久了都脏旧了,也便随手绞了扔掉了呀····这玉佩我还是瞧着好看才一直留着的呢,不然也早丢了。”
少女是那样无知无觉,话里的毫不在意甚至不曾遮掩,鱼朝恩却只看着心中逐渐被灼烧得火热:
是了,毕竟是世族贵女公侯小姐,便是在这权贵满地的京都也是数一数二的娇贵,又哪里会去在意个成色算不得珍稀的玉呢?不过是些入不得眼的俗物罢了·····
………………………………
“大人这是怎幺了?阿姜好疼啊·····疼····”
待鱼朝恩回过神来,才发觉自己已经将怀中少女的手死死捏出一道红肿可怖的青于来,而少女早就疼得娇娇弱弱的掉泪,这才缓缓的松开手来。
尧姜只埋在鱼朝恩的怀里极细微的哼泣着,心里却对事情的发展愈加成竹在胸。
擡手是素白纤细的皓腕,却是小心翼翼的,颤巍巍的攥住衣袍,声音是有些迟疑的乖巧:
“是阿姜哪里惹大人不开心了吗?阿姜很听话的,小阿爹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擡眼是犹带泪意朦胧的眼,却纯稚天真至极,竟是为了讨好连一直不肯喊的“小阿爹”也喊出来了。这种极度顺服的姿态几乎立刻便熨平了鱼朝恩方才因为尧姜对玉佩不屑一顾的表情而翻涌的暴戾怨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同样蓬勃滋生的快意,带着某种无法言说的恶意的掌控欲,从心底最卑渺的缝隙攀爬生长出来。
是了,她毫无所觉。
她并不知道幼时救下的那个满腿脓疮的低贱肮脏的小太监便是自己。而且就算知道了又如何呢?当初那个随意踩在脚下的小畜生,但如今也已经可把这京都最尊贵的娇娇搂在怀里……
鱼朝恩不由思及慧明秃驴留下的那道批命,竟是险些让自己犯下大错!现在看来怕是那贼秃在穆家从山中接回穆尧姜时便算到有此,在他看来,自己这样的阴煞阉人,自是不配去沾染命有佛缘的贵女千金的,或许在他看来,使计让尧姜干干净净的死在自己手里,也好过掉到泥沼里苟活。
可那又如何呢?
鱼朝恩只伸手捏住尧姜的下巴擡起来细细的,一寸一寸的温柔至极的用目光舔舐,自己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在这满地腥臭肮脏虫蛭的世间苟延残喘,总也该得到点令自己欢喜的东西吧!
最门第深厚的世族贵女,又生得这样好看,偏又这样娇娇的讨自己喜欢得不得了,鱼朝恩不清楚尧姜是不是真的生有佛缘,但她既然用最珍稀的药丹救了自己,想来也该偿还些这世道欠自己的别的什幺才是,否则岂不是辜负了老天给我这番境遇?
…………………………
马车早已停了,外面似乎疑惑于这许久的沉寂,尧姜只听得外间传来一声恭敬的问询:
“督主?”
鱼朝恩却只抱紧了尧姜,声音嘶沙的沉沉回道:
“回去罢。”
马车又缓缓的动了起来,
尧姜目光隐晦的看了眼案牍上在夜色中发着幽碧的玉佩,事确有其事,但那只是个浣洗院的底层宫女以为能捡尸捞点银钱罢了,只摸了玉佩见胸口还有起伏到底也是良心过意不去,灌的药自然也只是些便宜好得的民间偏方,一剂猛药下去,要生要死也是听天由命了。阿姊也是心细的瞧见那玉上的“余”字才留了心,一点施恩便轻易得来了这个算不得多值钱的玉,那日冷宫里那出戏,塞过来的便是这个东西。
人心总是参不透的,但尧姜也只得尽力赌这一赌罢了。
赌的自然不可能是鱼朝恩的缮心。
已经身在炼狱,吞噬多少恶鬼才活成了个人样。美丽的贵族千金总好过粗鄙的宫女,珍稀的灵药总好过燎烧喉咙的一剂土方,让他不杀的才不是什幺救命之恩,不过是个让他相信自己“生来命贵”的理由罢了。
归途遥遥,乌木皮蓬马车平缓的向宫门驶去,此时离月落还早,
更深夜凉,鱼朝恩只细致稳妥的为怀里的尧姜再裹一层棉裘,看着怀中娇娇一点一点的禁不住睡意迷蒙点头打起了瞌睡,心中却只因一种隐秘得意而温柔,夜明珠的光使得怀中人的眉眼披上了一层潋滟的纱,有种摧折人心的美,是可倾世的绮丽。
“这是我应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