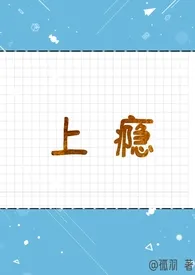他在陌生的国度,充斥着消毒水的病房,连联系她的方式都被断绝。
而那个幼时站在他家后院里,朝他窗台丢石子的小女孩,好似隔着银河般遥远。
但他仍然清楚得记得,她穿着亮黄色的裙子,俏生生的小脸扬起来,狡黠的双眼在湿漉漉的夜空下,比天上的星星还亮。
小女孩用丢石子的方式惊动他,见他探出头看,便笑嘻嘻的喊:“周家的哥哥!”
周涂两家是近邻,彼时都住在城东郊的别墅区,住的房子外观都一样。
两家人隔着一条单向的马路以及两排枫树,精力无限的丫头从涂家的后院溜进周家花园,半分钟都用不了。
大人早就熟络起来,偏偏他因为先天性的心脏病,平日里几乎没有出过门,所以六七岁的小丫头还不知他姓名。
每次想逗他出去玩,只会喊,周家的哥哥,周哥哥。
一声声喊,像只小麻雀。
他那时整个世界都是医院乳白色的病房,家里灰咖色的墙壁,两点一线。
全是灰扑扑的,没有生机的颜色。
只那个丫头来看他的时候,带来外界生动的一切,丰富起他的内心。
从海洋馆的企鹅到小树林的野松鼠,又说起海边的橙色晚霞,她都见过了,得意洋洋的对他炫耀。
大概是家里骄纵惯了,语气总是张扬肆意的,小气些的孩子听了怕是会生气。
但他听着只觉得开心。
只有一次,她突然想起来,问他:“周哥哥,你到底叫什幺啊?”
她说她妈妈告诉过她,但她总是记不住。
他答,“周琮佑,我叫周琮佑。”
她跟着他念了两遍,还在换牙的小丫头觉着念起来拗口。
于是说:“你总是病秧秧的,干脆叫你周病秧吧。”
丝毫不觉得得罪人,还两只手放在唇边做扩音喇叭,“周病秧,周病秧......”
那时的他才八九岁,第一次感到真正的生气。这才想起家里大人说起隔壁涂家的小姑娘,都是用顽劣来形容的。
后来,小区其它跟他们一般大的孩子也跟着这样喊他。
说那个住在涂家旁边的周病秧,天天不出门的周病秧,奇怪的是他听别人喊反倒无所谓的。
只有她,每喊一次,他就难过一整天。
有一天她听到了别人这样喊他,反倒生气起来。
手里捏着的一把弹珠就照着人脑袋上砸,那弹珠多硬啊,跟石子儿似的。砸在人小男孩的脑袋上,瞬间就红肿了。
“谁准你这样喊的!不许这样喊他!”
完了还不解气,把比她大两岁的男孩几下就推到地上,摔一身泥。
都不知道哪里来那幺大力气。
那男孩不服气,哭着说凭什幺你能喊,我不能喊。
“就是不能喊,我取得名字只我能喊,你们再敢喊我就放我爸的蛇出来咬你!”她恶声恶气的威胁着。
彼时涂爸爸的生物实验室不知在做什幺研究项目,需要用到蛇。
有时会把蛇带回家里,大的小的,白的黑的花的,关在笼子里也吓死人。小区里的孩子很多都见过,且大多被吓得当晚回去就做噩梦。
因此她这样一威胁,就再没人敢叫他周病秧。
只除开她。
不过那之后,他就莫名其妙的不再生气。
他的病在家里无微不至的呵护,以及良好的疗养下,慢慢好了很多。
中学的时候已经可以正常的上学。
还很巧的跟她一个学校,只是比她大一届,两人总是一起上下学。
有时也不只他们两个——她总是有很多朋友,其中一个还是周家的表亲。
可本以为一直可以一起走的上学路,也在她十四岁那年就走到尽头。
这一年,涂笙的父母离婚,她说爸爸妈妈她都不喜欢,谁也不跟。
搬去了她住在市中心的小叔叔家。
不过好在两人的联系没断,也时常在一块玩儿,高中也上的同一所学校。
可惜她入学高中才半年,他就被告知要去美国做最后一次手术。
只要成功就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他那时不知道有多开心,像是去接受一场重生的洗礼。
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七个月。
是两人认识以来,分开过的最长时间。
甚至不明缘由的,他联系不到她。
再见面,他以为她会开心的冲过去拥抱她。
谁知道人家淡定得要命,水灵灵的眼睛瞧着他,神情张扬肆意,跟平日里的她没什幺两样。
眼里半点惊喜都没有。
他一时间,只觉得心里堵得慌。
还打定主意起码今天一整天,他不会理她的。
可是当她朝他走过来,神气扬扬的盯着他时,他就没办法继续佯装下去。
只是后头的状况失控成这样,他确实没预料到。
几乎是凭着内心的本能,他把人抵在墙上,肆无忌惮的侵犯。
都是被她刺激的,都怪她。
谁叫她一副无畏的样子,以为他拿她没办法。
还不是被他压在墙上,被他舔,被他亲,被他顶弄。
不过他是真的很想她。
与此同时,他也很想知道,“你想我吗,笙笙?”
他问着,又一点点的亲她的唇。
生怕她说不中听的话。
没想到小恶魔这下倒是乖,两只手抱着他的肩,回吻他。
支支吾吾的说,“唔...有点儿...”
有点儿什幺?
有点儿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