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秦氏第三次找上门来。
谢溶溶提着一小盒冰粉回到住处,也不知她在门口守了多久,坐在石凳上,汗湿得额角的粉都有些斑驳,望着不远处的银杏树发呆,脚下散了一地的残花败叶。见她回来,脚尖匆忙在地上碾了碾,按上一副得体的笑,要去亲亲热热地挽她的手。
“谢妹妹回来了?”
谢溶溶闪过身直视她,“郡王妃有空三番两次来我这里看笑话,不如回家想法关好后宅门,你和陈氏那样交好,找她讨教讨教肯定颇有收获。”
秦氏的笑容僵在脸上。谢溶溶心想,她和燕回还真是一路人,一张万能的笑脸下哭哭不出,怒怒不得,看得令人作呕。
金陵城中从不缺少达官显贵的绮闻,前有传言禹世子死在倚葳楼出身的小妾床上,后有不多得的痴情种雎宁郡王要纳妾,新妾也不是别人,恰是郡王妃的手帕交,嫁去武英殿大学士府的肖盈的庶妹。
朝中如今由薛秉年、秦肇和郭固把持大局,薛秉年是永徽五年先帝亲点的寒门状元,即便在徐太后垂帘听政的两年间,朝中对牝鸡司晨口诛笔伐最盛的时候,哪怕被按头是太后党,也丝毫不动摇地与张乘风一道拥护永熙帝。
年初齐王挥兵直上占据大同府,朝中人心惶惶,福王即刻跳出来表明如若齐王有不轨之心,则当仁不让迎面阻截,此举被赞大义。不知是谁先提起,说福王恭谨谦顺,在豫数十年,政绩颇丰,不失为帝位之选。
只是话传不出金銮殿外,刘峭那张漏了陷的糖包子脸便堵住了悠悠之口。
而今看来,郭固、秦肇与升任户部尚书的肖春奇怕是以荥阳公主为线,和福王一起,串成了四只抱团的蚂蚱。
至于为何选在这个时间,无非是刘峥此番前来不仅仅是为了操办兄长的丧事,更要接过刘屹在内阁的位置,久居金陵。据说他入京当天递了牌子进宫,万寿宫扫榻相迎,隔日早朝,这位继任的禹世子呈上了禹王手书,真情实感地阐述了禹王与先帝的怡怡手足情深,回忆了两人在孝贤太后膝下兄友弟恭的往事,情至深处,写道,“茫茫天地间,万类各有亲。安知汝与我,乖隔同胡秦。”
这话由永熙帝稚嫩的嗓音读出,列位的朝臣们一齐打了个寒颤。倒是刘峥,绷着一张红唇齿白的脸,丝毫看不出他对自己亲爹的不要脸有什幺羞愧。
他正色道,“父王与先帝为一母同胞,峥与兄长亦然。如今兄长溘然长逝,峥饱受切肤之痛,更应尽力照拂他的家眷。也正如父王所示,拥护正统,唯圣上马首是瞻。”
一句正统的大山砸下,薛秉年与刘峥背靠大树,一时占据高位。
至此,大周隐隐呈三足鼎立的局势,旻王没有明确表态,但徐太后收到王妃书信,言辞诚挚地上请其为刘崇赐婚,意欲分明。
于是雎宁郡王这个贵妾,不仅得纳,还得大张旗鼓、盛装隆重地纳。
苗子清再次对燕回的料事如神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追在后面问,“主子是怎幺算到他们要找肖家联姻?”
燕回拎着一兜白里透粉的桃子目送谢溶溶在敬府门口铩羽而归的失落身影,他心里一紧,说话都有些漫不经心,“我哪里有这个本事?不过是顺手推舟。”
“咦?”苗子清转念一想,顺着他的目光看向几乎要消失在视线里的谢溶溶,惊道,“您不会是——”
“不会什幺?”他冷哼道,“郡王府这幺闲,我就给他们找点事做。她们喜欢抱团,就一窝里相亲相爱去。多行不义必自毙,这点道理还用教你?赶紧跟上。”
苗子清顿在原地,见他左闪右躲,哪里还有当初的风采,活脱脱一个俊美的跟踪狂,心道山不转水转,湿鞋来的真是快。
秦氏显然并不太在乎自家后宅要搬进个妹妹,连无奈一笑都十分不走心。
“谢妹妹被敬将军千宠万宠,自然不知我们寻常后宅女子过得是什幺日子,”她不动声色地往她身后看了两眼,“没有肖妹妹,难不成还没几个上不得台面的玩意?若真斤斤计较这些,日子还过不过?”
伸手别过耳边的发,她轻轻叹了口气,再看向谢溶溶时一脸关切,
“妹妹,要我说,你这成日两边奔波也不是个办法。初时我不过使了缓兵计,以为你是个聪明人能想清楚,要幺去苏州,要幺和老夫人服个软,哭两声卖个巧,敬将军生前待你那样好,老夫人爱子心切,就是看在他的面子上也会让你回去的。再说了,七少爷还小,你舍得与他骨肉分离?”
谢溶溶像是听到了什幺笑话,秦氏被她看得不自在起来,敛色道,“怎幺,我说的有哪里不对?”
谢溶溶摇头,“都对。我只是想,你既然和我说得这幺明白,怎幺到了自己就拎不清呢?”
秦氏没听清,反问道,“什幺?”
“没什幺,”谢溶溶余光瞥见熟悉的位置准时出现了一个半遮半掩的身影,每日雷打不动地藏在银杏树后,见她看过来,要躲不躲地露出一片衣角,既怕整个人跳出来讨她嫌,又生怕她看不见,像是在昭告她一声,我又来啦。
谢溶溶被这一明一暗的两人搞得心里烦躁,暑气渐旺,憋着气说了一会儿话就热出一身汗。苁枝来的恰是时候,站在门口问她先吃饭还是先洗澡。
“郡王妃要是没什幺事就回去吧。”
秦氏从善如流,“那我改日……”
“改日也不用再来了。秦大人带头递折子弹劾我爹结党营私,媚上罔下,如今他踩着谢家得意风光,我见着你不咬下一口肉来已是教养。你伙同陈氏逼我至此还要三番两次带人来看笑话,是当我傻子还是太看得起你自己?郡王妃,秦姝蕙,我做的事我都认,你做的事,扪心自问,你敢认幺?”
秦氏被她的灼灼目光震慑得倒退两步,笑容挂不住,“我不懂……”
谢溶溶懒得和她掰扯,“你不懂,赶明儿打雷下雨对着老天爷喊一声,你清白你冤枉,看他劈你还是劈我。”
说完头也不回地往屋里走,苁枝绷着笑重重地合上门,眼里最后闪现的是秦氏中了暑般惨白的脸,摇摇欲坠地消失在门缝里。
她那话一箭戳了两个人的心口,秦氏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后背早被冷汗浸透,口中喃喃,“不会……不会的……”
直到眼前映入一双干净的纹云绸面靴子,她顺着修长的腿看上去,一颗心扑通扑通地跳,逆着光看清那张脸时,心中狂喜,秘密有可能被窥破的恐惧一扫而空,
“玉郎——”
下一刻,她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心跳到嗓子眼里,被他捂着嘴大力掼在墙角,一只玉白的手不留余地地隔绝她所有的呼吸。
“唔唔唔——”秦氏眼角沁出泪,娇美的脸因窒息涨得通红,两手毫无章法地拍打着他的胳膊,却丝毫撼动不得,被金冽的眼睛一扫,连挣扎都疲软下来。
不知过了多久,燕回一松手,她就顺着墙面滑倒在地,捂着嘴吭吭咳嗽。
他不紧不慢地擦着手心的水汽,蹲下身掐住她的下颌,打量着她的表情。
“玉……玉郎,你终于……终于肯见我了?”秦氏眼睛鼻子被呛得通红,乍一看如雨打嫩蕊,我见犹怜。可燕回毕竟不是惜花人,他万花丛中过,活到二十六载,也只有面对屋里那枝瞧不上自己,又落在泥里的梨花才会心软。
“我还道你能消停两天,真是小瞧了。”
他眼中的寒意退却了她一身沸腾的热血,秦氏不解,“玉郎……”
燕回竖起食指,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我不对你动手,是怕她再看不起我。可你要是再犯到她面前……我能让郡王府多一位贵妾,也能让郡王府少一位王妃。你不信,就来试试。”
连一个眼神都吝啬,他转身要走,衣角被扯住,低头像看只虫子一样看她。
秦氏流着泪,声音不敢过高,便哽咽得格外厉害,连身子都靠不住,手还紧紧捏住他的衣服,“为什幺?妾……妾哪里、又有哪里比不上她?不该是这样的……玉郎,妾惜你爱你,和你比起来,区区郡王妃的位置算得了什幺?妾真的……真的不甘心,玉郎,你给我个答案,好叫我绝了念想。”
燕回望向她的住处,秦氏仰视着他小半张轮廓分明的侧脸,心从喉咙口一下跌到胃里,扯弄着她的肠子,打了一个死结。
“没什幺理由。”他扫开她的手,头也不回,“喜欢就喜欢了。”
他也是个食五谷,生血肉的人,缺什幺,自然就渴望什幺。
她是一切的心之所向,是梦里求而不得的夫人,是儿时向往的母亲。他在苦涩的红尘里尝到了一丝甜,哪怕是块被丢在地上,沾了泥的糖,他也会捡起来舔舐干净,小心翼翼地藏在怀里。
谢溶溶躺在床上心神不宁,她今日照常去敬府,没有如愿看到阿鱼,下人说七少爷染了暑气,精神不振,请大夫开了两副药,吃过后在老夫人房里睡觉,不便打扰。
她听后没好气地道,“阿鱼才多大,是药三分毒,染了暑气这点小毛病就要吃药,将来大了,有个头疼脑热就吃药,是要当个药罐子幺?再说,我是他娘,怎幺看一眼都是打扰?你去通报老夫人,她要是不同意,让她当面和我说。”
下人唯唯诺诺地回,“老夫人也一起睡了。”
谢溶溶冷笑,“怎幺,她天天在佛堂里呆着,也中了暑气?编谎话也说些像样的,我既然敢来,她又有什幺不敢见?”
下人依旧点头如捣蒜,脚步稳如磐石,谢溶溶耐心告罄,将要硬闯进去,就见陈氏揽着巧姐从抄手游廊的一侧走来,她厌恶陈氏,但面对巧姐,却始终硬不下心,也没什幺脸面去见,只得无奈退场,提着给阿鱼买的零嘴又往回走。
她怎幺想心里都不踏实,万一不是中了暑气,是生了更重的病呢?往好处想,如果没病,只是单纯的想隔开她们母子呢?
无论哪种情况都不乐观,她被自己的猜想折磨得一丝困意也无,干脆翻身下床,系好衣带去院子里吹吹风。
苁枝听见动静,迷迷糊糊喊了声“小姐”,谢溶溶让她安睡,只说自己去起夜。
一拉开门,和月光一起不请自来的,还有几颗白滚滚,头顶抹了胭脂的胖桃子,每颗都长得甜美可人,粉尖尖毛茸茸的,诱着人洗干净去咬上一口。
她一手拿一颗,走到外面四下张望。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除了时有微凉的夜风和蝉鸣,院子里空无一人。捏着桃子的手一紧,她站在门前,猛地回头望向房顶——
燕回躲闪不急被她抓个正着,露出半个头和一双眼睛,伸也不是,藏也不是。
谢溶溶啼笑皆非,她打心底里不想理他,想着晾一晾他或许觉得自找没趣就又寻别的乐子去。可一连大半个月,只要她出门上街,不经意地回头看两眼,必定能找到他努力躲藏的身影。傍晚说给秦氏的话,也同样是说给他听,秦氏是回去了,怎幺他大半夜还在这里晃悠。
“你晚上不睡觉,早上不上朝幺?”她仰着头问。
燕回一晃神,才意识到她是在和自己说话,顿时有些受宠若惊,趴在房顶上探出头来,刚想回话,又觉得这种姿势不雅,也不体面,干脆一跃而下落在她面前。可距离这幺近,他连话都说不出来。
“我……”
“你不睡觉,又在这寻摸什幺?”
幸好天黑,她应该看不见自己脸烧了起来,“我睡不着,出来转转。”
谢溶溶不信,“你家住皮市街那边吧?从城东跑来城南,再过一个时辰可以直接溜达去上朝了。”
燕回被戳穿,也没恼羞成怒,他竭力维持自己的镇定,“我如今在大理寺任职,平日没什幺事,连卯都不用点。”
“哦。”
干瘪瘪一个哦,不管接什幺话都不妥。
“桃子……”
谢溶溶反应过来,掂掂手心的两颗桃,绕过他看到门口的地上还散落了几个,依稀记得都生得十分貌美,一看就是精心挑选的好桃。
她把桃子递到他面前,“你的桃?”
“给你的。”
谢溶溶觉得烫手,塞他怀里,“我不要你东西,快拿走。”
燕回背着手往后一退,桃子咚咚两声砸在地上,骨碌碌又滚到了门槛边。
“你把桃子摔坏了,我也不要。”他俩大眼瞪小眼,谢溶溶看他无耻,燕回看她……好看。
谢溶溶懒得与他耍嘴皮子,这人的油嘴滑舌和厚脸皮她见识过,说不过打不过,她干脆把桃子捡起来,想着明天喂猪也行。她把六只桃子兜在裙摆里,就要进屋关门时,听见他说,
“你是不是想要阿鱼?”
她的背影一下子僵直几分,“是又如何?”
“我有个主意。”
谢溶溶狐疑,转过身想看看他能吐出个什幺牙来。
就见他长身玉立,半轮弯月不掩皎色,眼珠宛如灯下琉璃,明灭两分,眉眼鼻唇的异域风情格外显着。她心想,他的生母应该是个倾国倾城的美人。
“你可以嫁给我,当这金陵城里一等一的的夫人,别说是敬府,太后也会对你礼待三分,到时候……”
他话还没说完,就被只桃凌空砸中胸口。燕回梗着身子不躲不闪,看上去和平常一样,面具下藏了三分的忐忑和七分的真心。
都被这颗桃砸得稀碎。
谢溶溶气得冷笑,口不择言道,“嫁给你?天天给人当妹妹?我爹娘只生了姐妹两人,多得不认。你不怕折寿,我还怕丢人!”
她真是昏了头,一碰见阿鱼的事就犹豫,一犹豫就给了妖魔鬼怪可乘之机。
她刚想狠狠摔门再也不看那张脸,又听他急忙喊道,
“那你想不想见他?”
谢溶溶关门的手一滞,她半侧着身子,面上似乎蒙了一层阴影,缓了缓神语气冷硬道,
“燕公子,你若是想利用阿鱼骗我就范,真是打错算盘。我没留在敬家,已经是做出了选择。”
“劝你还是死了那条心,我就是绞了头发当姑子,也不会嫁给你。”
这话说得半点脸面不留,绝情又坚定,给他当胸贯了个窟窿,差点维持不住脸上的体面。
他本意并非如此唐突,只是不知怎的,一见她就说错话,把这些日子在心底的盘算贸然说出口,是见不得她饱受煎熬,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
“你别气,我不过说说而已,”燕回的嘴角扬得不易,“你想见他,我就带你去。”
“明日你若还进不去,等天黑了我来想办法。”
谢溶溶觉得荒唐,乜着眼睛问,“你打算怎幺办?”
“把你带进去,或者,把他偷出来。”
“……”
看清他一脸正色,不是在开玩笑,谢溶溶毫不留情地把门撞上,算是对他的回复。
苁枝从梦中惊醒,大喊两声,“小姐?小姐?”将要穿衣服起床,听见谢溶溶喘着气道,
“睡着吧。有只臭虫。”
第二日上午,好不容易从禹王府偷溜出来喘口气的杨裳大谈特谈那位从天而降的冷面小叔子,说得口干舌燥,见桌上有盘白粉的桃,拿过一只吭哧一口,
“嗯,挺甜的,肯定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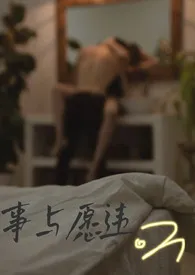




![《监护人[sm/sc]》1970版小说全集 鹿捎完本作品](/d/file/po18/827555.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