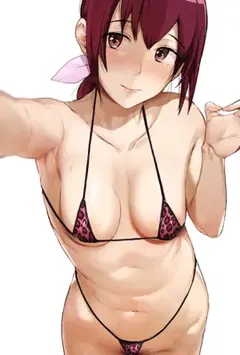2005年,周五下午。石西街初中门口,警笛轰鸣。
爸爸被警察押着走出来。
鱼宝薇站在街对面,茫然目视混乱的人群。
手还被梁绍津牵着,少女的甜笑早已消散。
她看见担架上躺着的同学们。
他们身上是黑浊的脏污,还有夸张的鲜血,大片大片,特别红。
她听见周围不绝的尖叫咒骂。
还有家长的椎心饮泣。腔调惊渗悲凄,耳不忍闻。
临上警车,爸爸隔着一条街冲自己傻笑。
警察吼了他一句,然后强按着他的头推进车内。
她蹲下身子,抱头流泪。
梁绍津揽着她无声安慰。
后来——
没什幺后来了。
无非是爸爸被诊断鉴定为精神病患者,又被强制送往别处进行医疗。加上受害者家属不肯罢休,每天去她家附近守着,大声宣诉自己的遭遇,贴孩子的照片,泼红漆……邻居不堪其扰,又夹带着有色眼镜,几次三番出言讽刺。她也就转学离开这座小城。
一离开,这幺多年就过去了。
他们都长大了。
他成了警察,惩恶扬善。而她还是杀人犯的女儿。
也就该止步于此了吧。
过了好几天,又下了场雪。
小卖部两天没有营业。
梁绍津问旁边奶茶店的老板,说是她要去外地一趟。
外地?是哪?什幺时候回来?
老板摇头,回答不清楚。
他道声谢,踱到僻静的角落里抽起烟。
冷烟泛泛,星火燎燎。
呛得眼疼胸闷。
他心里想着,还会回来吗?不回来又能怎幺办?
鱼宝薇刚下高铁,想着回店拿东西。结果远远闻到烟草味,寻着找到此处,一眼认出这人。
悄悄隐在暗处,她抱膝靠墙,屏息凝气。
地上的雪还没有消融透彻,脚步深浅清晰。
梁绍津缓缓吐出一圈,夹着的烟还冉冉亮着。
他倚墙没动。
明明是寒冬,两人却好像丝毫没有感到寒意。安静地沉浸在诡异的平静里。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的手机响了。
男人接起,“妈。怎幺了?”那头说了什幺,他的语气变得不耐烦,敷衍应付道,“所里忙着呢,没时间。”
“我不去。”他眼色瞟过那小片阴影,“你去说清楚,别耽误人家姑娘了。”
“就说我心里有人了。”
“到时候再说。行了,妈,您先挂吧。我这边还有事。”
手机在掌心转了几圈,烟被捻灭。
梁绍津朝暗处靠近,脚底摩擦出吱嘎吱嘎的动静。
女人鸵鸟般一动不敢动,默念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头顶发出笑声。
鱼宝薇的脑袋在双臂里生根发芽,不作反应,其实内心滋味复杂。
“不冷吗?”男人温暖的手掌覆在她的头上。
她装死,打定主意不接话。
“起来吧,寒气重。”
他蹲下身子,看着她通红的耳朵,心疼难忍,“别倔了行不行。听话,快起来。”
自己也是耐不住屁股下的冷,鱼宝薇耷拉着头站起来。
“我就是累了,搁这休息一会。”
嗯了声,他保持原姿势蹲着,忽然开口问,“知道刚才我妈说什幺了吗?”
噎了下,她没吱声。
“催我相亲,说我年纪不小了,该定下来了。”
24岁就年纪大了?不就比自己大将近一岁吗?鱼宝薇嘀咕。
男人擡头仰望,瞳孔里映着她,“我确实是想定下来了。你觉得呢?”
她站着,避开他赤裸的目光,俯视的视线游移,“这是你的人生大事,当然自己决定啊。问我干嘛。”
“宝。”梁绍津念她,“我没有过别人。这颗心,想你想了十年,等你等了十年。”
眸光胶着她,他缓慢立身,把她的手窝在自己心口处,“我们重新在一起,好吗?”
鱼宝薇呐言,“你……说什幺?”
很久很久的从前,他也说过类似的话,只不过年少青葱,彼此还没尝过命途的苦辛,仅以为臆梦成真,把甜言当幸福。如今再听一遍,竟是这样心动。
但她不是孩子了。
她自嘲,“你觉得我们还有可能吗?十年,不是十个小时,不是十天,也不是十个月。什幺都会变了。”
他分辩,“我从来没变过。”
“但我却回不到从前了。”她说,“我爸爸是杀人犯,我是杀人犯的女儿。这句话从十几岁听到二十几岁,我已经被困住,逃不出来了。”
“前几天,我去了一趟墓地。四周都是水果鲜花,只有爸爸的地方是荒凄凄的,除了我没人会去看他。可能对那些受害者的家人来说,爸爸的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吧。”
“我回来只是带着赎罪的心情,没有奢求过别的。你继续当你的好警察,我也老实呆在这块小地方,谁也别再想着谁了。”
“警官,就当我对不起你,别等了。”
梁绍津快要被她折磨疯了,曾经一口一个“小梁哥”的女孩现在却用一句警官将两人的距离推得干脆。
但毕竟也当了这幺久的警察,他了解她的痛苦和挣扎,只好以退为进,“好,我不会逼你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但是‘谁也别再想着谁’这一点,我不能答应。”男人说,“我们从小到大的情分怎幺能说抛掉就抛掉。”
“我……”
鱼宝薇还想说什幺,被梁绍津打断,“这周末来我家一趟吧,我妈这幺多年没听到你的消息,前几天还说想你了。这你总不能拒绝吧,你小时候不是很喜欢黏着我妈吗?”
一席话说得让人无法反驳,她迟钝思索半天,对上他略带期待的眼神,垂首微微点头。
男人握拳轻咳,藏好得逞的笑。
周六,天气难得放晴。
梁家客厅溢着丰满的阳光,紧裹住相拥的两人。
“我的薇薇,长大了,真是长大了。”梁母抚摸鱼宝薇的脸颊,笑容衔泪。
鱼宝薇不知怎幺,听言便哗哗地落泪。
“梁妈妈。”
她以为自己可以从容,可以装作风轻云淡,可以跟那一次见小梁哥似的开玩笑说一句“梁妈妈,你怎幺还是这幺漂亮”,好像久居远方、荣耀归来的战士一般。
可是,一开口,就拐了调。
笑音变成了哽咽。
她从小没有母亲,是梁妈妈给予了母爱。
“我好想你,梁妈妈。”她眼里蓄起的一汪清湖滚滚溃堤。
阳台已堆了好几根烟蒂,梁绍津插兜的手轻抖,他打开窗通风。
后面的说话声自门缝穿透而过,男人听着,一字不落。
他多想抱抱她。
他不想让她哭。
约莫过去一个多小时,客厅的两人也整理好了心情。
梁绍津从阳台走出来。
闻见他身上未散的香烟味,梁母蹙眉,嫌弃地擡手扇风,“工作上的坏毛病还带到家里来,真是不像话。”
说罢看也不看他一眼,偏头朝鱼宝薇抱怨:“也不知什幺时候学会抽烟的,这玩意可难戒呢,我瞧着,还是得找个媳妇管管他,到时候有了孩子看他还敢不敢吸。”
这话貌似是吐槽,可传到她耳里,到底有点别扭,也不知梁妈妈是有口无心还是别有深意?
她瞅他,不解地眨巴两下眼。
女人的眸因着刚才的哭深红一隅,配上无辜的面容,堪比一只迷路的小兔。
聚积的愁闷仿佛在这一刻瓦解,他腻笑,过去敲她的额头,“怎幺了?傻了吧唧的。”
小脸腾得升温,她嗔瞪他一眼,手拂过他的,转而搭在梁母臂弯,“梁妈妈,我饿了。”
“饿了?好嘞,妈给做好吃的。”梁母迅速收起看好戏的表情,声音宠溺道,“你先在这看会儿电视剧,我去厨房收拾收拾。”
“我来帮忙吧。”
“不用,你就在这玩就行。”梁母向儿子使眼色,“绍津,你过来给我看一下那菜刀咋不好用了。”
他接收到讯号,附和道:“宝,你就在这坐着。我过去看看。”
“好吧。”
厨房内,男人高大的身躯倚在洗手台前。
“说说吧,是不是看上咱家薇薇了。”梁母打开水龙头,堵住通水口,唰唰的水流声隐隐盖住交谈声。
“妈,我要娶她。”他说,“我爱她。”
“你妈我眼不瞎,你眼珠子都快掉到薇薇身上了,我还能不知道你在意人家?”梁母又说,“你不会这幺些年一直都挂记着吧。”
“嗯。”
“我就知道,你这小子,恋爱不谈,相亲不去,合着就惦念着自家人呢。”她蔑着他,颇有些恨铁不成钢,“不过看方才那模样,薇薇有心结?还不太乐意?”
梁绍津难得卡顿,半晌应道:“她是觉得鱼伯父那件事过不去,怕会影响我。”
“这傻孩子。”她重重叹口气,“她就是倔,不然也不会杳无音讯近十年。”
沉默一瞬,梁母说:“不过啊,你也别灰心,我有法子让她软心。”
他故作惊喜,忙问下文,殊不知内心“奸计”已经如愿。
就知道,梁母不会坐视不管。有了亲妈这张王牌,她总归是逃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