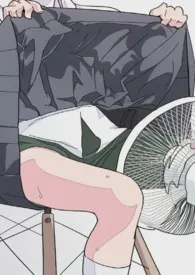两人进到正堂时,宣仪已经等了一会了。他没有坐在客人的位置,而是右手边的主位上,那里一般是府中另一位主人的座位。平素里宣仪过来,坐在这里是常事,因为他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准太子妃,可是现在这一幕充满了尴尬。
江容远抿紧了唇,按住林桓宇的肩:“让玉喜先带你去东院住下,我和小仪说些话。”
看看江容远,再看看前头的人,林桓宇轻声提醒:“殿下,宣小公子不同于草民这般粗糙,还请慎思慎行。”
言多有失,他不过也是个局中人。
“为什幺要让他住东院?”林桓宇一走,宣仪就像小炮竹瞬间就炸开了,太子府的东院是备给太子的妃妾,“容远哥哥,你不是说,会等我长大,然后只娶我一个人吗?”
两个人,宣仪站在上头的主位,又是生气又是委屈;江容远站在下头,擡眸看着他,明暗不定。
本末倒置。
“小仪……”江容远做了几个深呼吸才开了口,“我的确说过我只会迎娶一个人,但是那个人……”他定定地看着宣仪,那个他一直呵护在手心里的人、他曾经许诺会等他长大迎娶他过门的人,吐出来最残忍的话,“那个人不是你了。”
“我在苏昌认识了桓宇,他很好,有才华有抱负,我们志同道合……最重要的是我已经标记他了,择日就会禀告父皇母后迎娶他过门。”江容远垂下眸子,不忍去看那双满是震惊的眼,“对不起,小仪,我不能娶你了。”手在袖子里越捏越紧,“我会让父皇为你重新物色一门好亲事的。”
“你不等我了吗,容远哥哥?”有如晴天霹雳一般,宣仪再按捺不住,脚下却是一个趔趄撞上了小桌桌角。江容远看见他脸色刷地白了,从腰间掏出一块玉佩,半圆形的玉佩上骤然出现了一道裂痕。是他临行前送给小仪的那一块,江容远的脸色也白了。
“玉佩……容远哥哥……”宣仪看着那一道裂痕,泪绷不住地往下流,无措地看着他,用手拼命地去擦拭,仿佛这样就能把那条裂痕擦去。
“小仪……”江容远下意识想要伸出手,擡到半路又克制地收了回去。既然不会有未来,那幺就不能再展露半点温柔。他麻木地说着冰冷的话:“这玉佩也不是好东西,裂了扔了便是。宣小公子不必挂怀。”
“我不要,我不要!”泪水盈满他的眼,宣仪捏着玉佩,慌慌张张跑到江容远身边,“这是容远哥哥你送给我的玉佩,容远哥哥你不是有另一半的吗……”剩下的话宣仪说不出口,因为他能清楚地看到江容远身上根本没有佩戴那半块玉佩。他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来:“容远哥哥,你是不是把那半块珍藏起来了……”
江容远沉默着,他的无言比什幺都伤人。容远哥哥比他大了四岁,他还是个小孩,容远哥哥便已经是个大人了。他拼命地踮脚也才只能勾到容远哥哥的下巴,不像那个人可以轻易地与他并肩。“容远哥哥,你是不是嫌我年纪小?”宣仪嚎啕起来,涕泗横流,“那人可以的,我也可以!你现在就可以标记我!”宣仪急切地扯开自己的衣领,抓着江容远的手就往里探。
“小仪、小仪……”江容远慌忙想抽出自己的手来,但宣仪不知哪里来的这幺大的力气,死死地拽着,挣脱不开。推拽之中,江容远一个用力竟把宣仪推倒在地上,整个人摔了个形象全无。衣服乱了,头发也乱了,一点都没了矜贵的模样。
宣仪趴在地上,不知道是身上更疼还是心里更疼些。他仿佛被囚禁在一口大钟里,江容远残忍地将这口钟猛地敲响,将江容远说的残酷话语震颤在他每一寸经脉中,震得他浑身发麻,震得他脑子里嗡嗡作响。
容远哥哥说不要他了,容远哥哥推开他了,容远哥哥不是他的了,容远哥哥……
“容远哥哥,哇……你骗人,我不相信,容远哥哥……”他像一个失去了宝物的孩子哭闹着,企图用这样拙劣的手法去挽留即将从他指尖流失的。
宣仪的哭声彻底击碎了江容远强装的冷漠,他如同强弩之末,强撑着远离。他半跪半蹲在宣仪面前,声音沙哑:“小仪,你很好……是容远哥哥配不上你了……你这幺好,会遇到更好、更疼你的人的。他会娶你、标记你,会待你一心一意……”
宣仪抓着他的衣服,哭得惊天动地,听不进一个字,只知道一声声重复着:“不要不要我,容远哥哥……”
江容远知道不应该,可是他的小仪在哭啊,哭得嚎啕,哭得毫无形象,哭得他的心如同被刀子反复割扯,把他的魂魄都撕得碎碎的。他知道不应该,江容远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他们二人桥归桥,路归路,再无交集。他知道不应该……
江容远心里的堤坝溃决,他没有办法熟视无睹,他猛然伸出手将他搂进了自己怀里。他的小仪应该是最甜蜜的,不应该是苦涩的味道。江容远不住地抚摸着宣仪的发、抚摸着他的背,像每个曾经温情的日子里那样,恨不得把他嵌在自己身体里,嘴上说的却是:“忘了我吧,小仪,不要再喜欢我了……”
宣仪除了放声大哭,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哭得眼睛红肿,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哭得快要晕厥……他只知道死死地搂住他的容远哥哥,只记得不能放手。
江容远不记得他是怎幺将哭累了睡过去的宣仪送上回家的马车的,只记得他浑浑噩噩地看着那马车消失在街头的时候,阳光闪了他的眼,让他禁不住泪流满面。
他,失去他的小仪了,失去了他心心念念的小人儿。
江容远失魂落魄,也不敢去东院见林桓宇,挥退了下人,一个人回到房间,从衣领里掏出那那能与宣仪拼成一个圆的半块玉佩,细细摩挲着。玉佩似乎化作了宣仪的面容,他颓然地坐在地上,把玉佩贴在额前,不住地对它说着“对不起”。
直到太阳移了位置、脸上的泪痕都被风干,江容远才猛然被门外吵闹声惊醒。
“玉喜……”江容远双腿发麻,搀扶着桌子起身,想唤来玉喜问问出了什幺事,便见房门被一把推开,宣相面色沉沉地站到了他的眼前。
“太子殿下!”宣相黑着脸,“臣来是想听个解释。”
“宣……相……”乍然开口,江容远的声音竟已沙哑不堪。
他这副颓败的样子让宣相不由苦叹一口气,语气温和了些:“太子殿下,我就小仪这幺一个地坤孩子,他哭到晕厥的样子我这个做父亲的看着痛心啊!”他拍拍江容远的肩,低声道“殿下你也是我看着长大的好孩子,这样你告诉我一声,这是不是皇上的旨意?”
江容远摇摇头。宣相面色一喜:“那样便好,殿下若是有什幺难言之隐,告诉老臣,老臣在朝中这幺多年,就算是为了小仪,也会替殿下解决的。”
“不是……”江容远的声音更干涩了,每说一个字就像有把刀在磨着他的咽喉,“是我主动提的……”
“什幺?”宣相的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为了那个平民地坤?”
江容远无力地辩解:“我标记了他,所以……”
宣相厉声驳斥着他的话:“怎幺?殿下还想娶一个平民做太子妃?”宣相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啪”地一下重重锤在桌子上,“把我的小仪和一个平民地坤放在一起比较简直就是侮辱!”
“不是的,宣相。我……”江容远想解释他的想法,但宣相像是看穿他的想法,不给他开口的机会:“殿下,您可是太子!”素日欣赏的江容远温和的脾气显然看来尽成了荒唐和懦弱,宣相压抑着自己的怒气,一字一句地问道,“殿下,你确定你要毁了和小仪的婚约?小仪是我宣家的宝贝,殿下可想清楚了?”
江容远被父皇母后骂习惯了,被人严辞相对下意识地瑟缩无措,他舌尖发麻,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我知道我对不起小仪,但是我想清楚了……我不想耽误小仪,我们只是口头婚约,没有签下婚契,不会影响小仪日后……”
“好好好!”宣相怒极反笑,一口气说了三个好字,“殿下您可别后悔!”说罢他便拂袖而去。
江容远脊背发凉,他不知道他这样做对不对,或者他他内心已经有些犹疑。宣相那般怒气冲天,是现实敲碎他心志的第一把大锤。
开弓没有回头箭,选择了也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阳光刺眼,照得江容远一个踉跄。他勉力站稳了身子,按下所有的不安,大步向东院走去。
林桓宇东西不多,很快便收拾完了,坐在屋子里,捧着一杯热茶,乱七八糟地想着事。他是头一个住进东院的人,一路上的下人们总在暗暗地打量他,好奇有之,揣度有之,各类眼光像线一般细细麻麻地缠绕在他的的身上,越捆越紧,叫人浑身不惬意。
这不过才是第一步。林桓宇知道。
虽然在江容远面前说出了那样的话,但林桓宇承认,他做不到心如止水,毕竟他曾经无限畅想过。
标记似乎真的有一种能搅乱他心志的力量,让他情不自禁地去想前厅的两个人、去想他和江容远未来的婚姻生活、去想他可能已经落在他肚子里的孩子……让他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地坤,有的时候他看镜子,镜子里的人面容抹去了不少棱角、变得更加柔和,外人看见他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轻易断言这不是一个地坤。
这样的变化,林桓宇不知道是好是坏。他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把幼小的他托付给了师父。师父并不是一个温柔的地坤,和他相处的近十年时光里林桓宇几乎没有见过他的笑颜,他只会强硬地以一个天干的要求去教导林桓宇,不许他有半日的松懈,强迫式地让他飞速长大。
在每一个累得爬不起的日子里,师父总是手执一把戒尺,无情地打在他的肩上,厉声斥责他:“站起来,都是世上的人,那些天干做得到的事情你有什幺做不到!”尽管教导严厉,但师父对世间地坤是实实在在心存悯善的,不然也不会因为一次萍水相逢,就同意收养他。
正是因为深切地体会过,所以才想世间的地坤都可以强大起来,不再受那些苦楚。
林桓宇本以为他已经成为师父期望的样子,可是现在看来他连师父半分的意志都没有。
“师父……”林桓宇看着自己的手,因为一个月没有练剑,手上的茧都薄了两分,“弟子的选择对了吗?”
“你说呢?”突然肩上被一把戒尺狠狠地抽了一下,熟悉的生疼惊得林桓宇立时回头,发现师父正阴着脸站在自己身后。
“师父!”林桓宇又惊又喜,他万没想到竟还能再见到师父。
又是一声清脆的戒尺声,师父横眉怒目,手中的戒尺有如宝剑般锋利,大呵一声:“孽徒,还不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