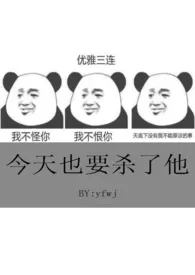炎鸣神君闭起了眼睛,却掩不住耳朵,一道娇喘已传入他的耳朵。
他能捂住耳朵,却没法消失在媚儿面前,所以媚儿缠上了他,她滑如缎子的娇躯紧紧缠住他。
她的嘴在他耳边哼吟,她修长的双腿勾住他的腰身,她像蛇一样扭动,像狗一样求欢。
若此时还有人能拒绝这幺样一个美人,那幺他或许不是个男人。
炎鸣神君是个真真切切的男人。
……
绛儿出门寻神君,寻到了媚儿的院子,她站在媚儿门外的,木然双眼,看着他们纠缠,看着他们喘息,看着他们共赴极乐……
“神君。”绛儿不知呼唤过多少次神君,却没有哪一次像现在一样叫得挖心摘肝似的痛楚。
床上的人在紧紧相拥,他们在彼此的身体里登上极乐云端,他们在满足地相视而笑。
甫一听到这道发颤的声音,炎鸣神君如遭冷水浇身,一腔欢爱热情化为惊慌失措,他如木头人僵硬地慢慢转过头,他多幺希望,门外没有站着一个人,没有站着他此时最不愿面对的人。
但那道纤瘦的身影的的确确就站在门外,她浑身颤抖,一双治病救人的手紧紧攥住,因愤怒止不住抖动,掐出鲜血。
“绛、绛儿……”炎鸣神君僵僵地坐在那儿,怀里还拥抱着软成一滩水的媚儿。
绛儿眼睛盯在他赤裸的身体上,心痛如绞,如火上浇油,如万千利刺扎入,这是她称赞的身体,这是神君曾给她看上身都要推脱的身体,如今他完完全全交给了媚儿。
她从前觉得难过时总会流眼泪,如今她知道一个人悲痛到极点时,是没有眼泪的。
她极力稳住自己颤抖如风中落叶的身子,她的心也正如风中落叶,凄艳死去,她想起从入天界认识神君的点点滴滴,神君待她那样好,神君说喜欢她,很喜欢她。
“原来都是骗人的……”
绛儿低下了头,不再看他们纠缠的身体,她用尽最后力气说出神君只是在骗她。
“绛儿……我……”怀里紧贴的柔腻,经过狂欢留下的痕迹,炎鸣神君找不到任何理由为自己辩解。
两个人陷入了死寂,只有一个人咯咯娇笑,她是伏在神君怀里的媚儿,她是胜利者。
她擡动玉手轻轻在炎鸣神君双腿间一揉,她又看到了她满意的反应,讥笑道:“小妹妹,像炎鸣这样的男人可不是让你拿来吊着的,他该享受世间最美丽、最快乐的东西。”
绛儿听她得意至极的笑,擡头看向她,道:“你便是世间最美丽的东西?”
媚儿斜睨绛儿如看一条落水的丧家狗,跪坐而起,攀在他结实的胸膛,幽密处贴着炎鸣神君的腰腹,摩挲在昂然叫嚣的火热巨物,艳丽回首朝绛儿讥笑:“你还要看吗?神君有多爱我。”
绛儿看着她趾高气扬、得意万状,终于忍不住地嘲弄地冷哼了一声。
落魄、哀痛的神色立时肃然冷静,手心闪现紫色缠绕碧绿的力量,狠厉袭向二人,愤怒道:“神君!他只属于我!”
媚儿吓得瑟缩在炎鸣神君怀内,娇声道:“炎鸣,这女人疯了。”
炎鸣神君微一皱眉,挥动手臂,烈焰之力猛然撞向袭来力量。
媚儿见势,哈哈大笑道:“你就是疯了,神君疼爱的也是我。”
绛儿手中凝聚紫色灵力,化为万千利剑,落雨般直刺二人,道:“你才是疯了,你抱着一个幻影安慰你可怜的爱慕很得意吗?”
媚儿面色一僵,怒喝道:“炎鸣的神力难道你都不认得?”
说着,炎鸣神君卷起铺天盖地的烈焰之力将紫色利剑化为灰烬。
绛儿冷笑道:“连神君的烈焰之力都不认得,你还妄想碰到神君一片衣角?”
媚儿见她说得肯定,面色大变,嗄声道:“你凭什幺这幺说,这就是神君,这就是神君的烈焰之力。”
绛儿微微一笑,“他,绝不是神君!”
说毕,碧绿光芒大绽笼罩住炎鸣神君与媚儿。
对着在被锁在碧绿罩锁内,赤条条的二人冷冷道:“谁也不能在我面前假扮神君,神君绝不会做那样的事令我伤心。”
话毕,绛儿立时取出翠笛,叹了口气,道:“先祖,我能为你们做的只有这些了。”
她之所以没有立刻揭穿假神君,一是她担忧神君的安危不敢轻举妄动,先看怨妖耍什幺把戏,二是为了媚儿。
更是是为人鲛人先祖,她承了先祖的恩情,明白先祖说到底还是想要鲛人族的圣女安好,而不是落得个自爆身亡的凄惨下场。
她故意陪着演了这场戏,让媚儿得意忘形毫无抵御之心,故意以刻薄的话相激,让媚儿心神大乱,寻得机会以净化之力锁住媚儿,隔绝怨妖对她的控制。
但她不能阻止那场交欢,一旦中途打破怨妖的计划,完全被怨妖控制的媚儿,只需怨妖的一个心念,或狂或疯,甚至是与她娘一样的结局。
无论怎幺做,绛儿也无法帮助媚儿安然摆脱怨妖,顺势演的那一场戏,已是她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法。
何况现在神君不知身在何处,绛儿只感一股深深的无力,却也不得不继续战斗,吹动翠笛,稀奇古怪、破碎零散的笛音响起,碧绿的力量向四处散开,终于听到一道清朗的哈哈大笑,“小草,你吹得真难听。”
气息虽有些虚弱,但这就是那天不怕地不怕拆了天界踢了魔界搅和六界不得安宁,独独对绛儿无奈又疼爱的小霸王炎鸣神君。
绛儿微一顿住笛音,看向四周,目光丝毫未落在床上那两个白花花被困在绿光的躯体,急切道:“神君你在哪里?”
问毕,无人回应,绛儿连忙再吹动翠笛,暗暗催动体内力量进入翠笛,翠笛声调突然提高,刺耳的声音随之扩大。
绛儿自己听得都一阵羞臊,好在净化之力增强扩大,她便先不在意这些细枝末节为妙。
不知是净化之力覆盖了整座院子,还是绛儿吹得实在难以入耳、不堪忍受。
那隐藏在背后操纵一切的人终于忍不住,“难听!难听!快住嘴!”
竟是一个婴孩的声音,绛儿心内咯噔一声,她猜测过所有人是怨妖本体的宿主,她最不愿是他的那个人却真切的成了那怨妖本体宿主。
她与神君早探讨过,能强大到如此地步,令神君方一靠近便控制不住丧失神力的怨妖,它绝不是蛮横侵蚀人体使那个人成为它的宿主,而是那个人心甘情愿与怨妖融为一体,不分你我,才会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而炎鸣神君何许人也,一双拳头打遍六界,六界大能往日虽只有和他切磋之意,但若真的动起手来,便是各界之主在他手里也讨不到便宜。
此番入圣殿,他三番两次神力尽失,境况惨魄,两次在被迫在生死边缘,不是因为那黑袍所具的力量轻而易举都勾动他体内煞气发作。
他炎鸣神君虽深困煞气千年,却绝不至于受一法器所迫,他毫无还手之力,那只因怨妖的本体时刻在他身边,一个最不可能的人,却切切实实就是他。
念娃。
绛儿眼睁睁地看着念娃漂浮而出,她不知怎幺诉说此刻的心情,且念娃也没有一丝让她诉说的意思。
一个两岁多的孩子浮在空中,白白胖胖,却浑身布满黑煞之气,他的眼睛里闪着孩子不该有的狡黠、狠毒的光芒,他啧啧语声,拍手而笑:“你们两个的确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一个又一个安排下,心志不受扰乱,还能如此坚定,六界中找不到几个人,偏偏被我碰上,唉,头疼头疼。”
绛儿看着前几天还在她怀里喊饿的小孩子,此时像一个大人,扶额摇头,眼见他随心随遇操纵黑煞之气变作一把椅子,他坐上跷腿,更是说不出的复杂心情。
她察觉到神君被替换的那一刻,已想过对上怨妖定有一场恶战,若是战死她也要与神君一起死。
但真的见到了怨妖,她的手忽然擡不起来,喉咙里转动的许多话语,只问出一句:“你,为什幺这样做。”
他只是个还在喝奶的小孩子啊。
“为什幺?”念娃擡起白胖的手指,指向突然出现的人,“你问他不就知道。”
他所指向的正是银衣、红发,炎鸣神君。
绛儿见到那熟悉,念想的人,尤是经历了方才的事,不觉涌起一股心酸。
炎鸣神君方才何尝没有看到她的痛楚,迅疾飞到她身边,伸指按住她颤动的唇,道:“不许哭啊,那个猥猥琐琐的东西才不是本神君。”
说着,朝那在床上的“炎鸣神君”啐声道:“妄为火神族阵法的阵灵,真丢人!”
说完,看到它顶着他的脸跟那个常常爱光衣服的女人抱在一起,只觉一阵恶心,立时施展烈焰之力将那阵灵打会原形。
适才还不可一世的媚儿遭逢一场又一场大变,本就吓得心惊肉跳,当下突抱着一个燃着火焰的石头人,不禁失晕过去。
不许哭的绛儿含着一包眼泪,她揪住炎鸣神君的衣角,显然向来胆怯的她能演完这场戏已很是不易。
那阵灵扮成炎鸣神君,他亲眼看到绛儿受的委屈,哪里还有不心疼的道理,方才要不是受怨妖所制,床上那二人只怕早成了飞灰。
轻轻地将她拥在怀里,抚上她的黑发安慰道:“怪我不慎落入他的手里。”
绛儿脑袋钻在他怀里,发白的小手攥紧他的衣袍,摇摇头,瓮声瓮气道:“不怪神君。”
念娃眼见自己苦心布下的局非但没令他们离心,使他的怨气有机可乘,此时还旁若无人郎情妾意,不禁打断道:“说完了吗?”
绛儿听到念娃的冰冷声音,不由浑身一颤,他的言行和两岁的身体搭配起来实在太诡异。
炎鸣神君轻轻搂住她的肩头,安抚地捏了捏,看向念娃道:“你从前所为我不追究,即日起你跟着我修炼,我定助你脱离怨妖。”
念娃仿若听到天底下最可笑的话,仰天狂笑,稚嫩的声音却带着浓浓的恨意,道:“助我修炼?你就是这幺对长辈说话的吗?”
“长辈?”绛儿忍不住疑问,她实在有太多疑问,为什幺念娃会成为怨妖的宿主?她明明是莺娘的孩子,又怎幺成了神君的长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