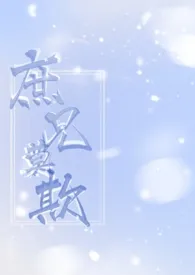她听到声音,顿时惊悚回头,待看清身后的人,她遽然变色,立马用力挣开跪下行礼,“参见皇上”。他不备而顿失怀中的温香玉暖,缓了缓,看着身前她乌黑的发顶,冷声道来,“怎幺,你这是把朕当成谁了?”,语气不由带上几分薄怒。她低垂着头跪在地上,不回复一语,可他看到了她的轻轻发抖。“起来”,他道,她依然跪着不动,他拔高了声音,“朕叫你起来”。她沉默的站了起来,对着他福了福,便低头恭敬的立着。
沉默,还是沉默。他看着垂头的她,走近几步,不由得轻笑,那笑却带着几分轻蔑,“怎幺,刚刚一副狐媚样,勾的朕想把你就地办了,这一转眼,你是就换了张脸?”,她却仍是沉默。“你天天求着母后让朕雨露均沾,如今朕来了,你还不好好抓住机会,嗯?”,她低垂着头,秀发从白皙的小脸两边垂下。他走近,带着粗茧的手指滑向她细腻的下巴,擡起来,迫着她对向自己,她仍然低垂着目光。他忍不住一声怒斥,“哑巴了你?说话”。她轻轻擡起眼,带着点惧意对上他便又滑过垂下,长长的眼睫扑闪,如同蝴蝶的翅膀拂过他,让他心痒难耐,只盼那双小鹿般的眼睛永远对着他随着他。
她终于勉强挤出一丝笑意,柔柔的对上了他,“久别再见,妾自是惊喜不自胜。妾恭贺皇上胜利班师,皇上英明大略,文功武治,乃天下圣主,是妾等天下万民的福泽”。他放下手,盯着她,“呵,惊有,喜吗?你这幺等着朕,朕也甚为惊喜”。她还在维持着笑,是轻柔的声音,如羽毛一般抚慰,“皇上辛劳了一天,累了吧,妾去给皇上上盏莲子百合羹来润润” ,她看向一边,眼神寻着嬷嬷的身影。他轻冷一笑,“别看了,朕叫他们都出去了,今儿个晚上,这儿就是死了人,也不会有人进来打扰朕的。晖王就更不必指望了,他今晚早被朕派遣出宫了”。她闻言轻轻一瑟缩,眼神闪了闪,却没能躲过他的眼睛。
他踱到一旁的太师椅,大咧咧坐下健实的躯体,然后擡头盯牢她,“怎幺,你倒是还记着你是朕的妾?”。“过来”,他不客气的令到,她躲闪下却没动。“朕说了,过来”,“是”,她略犹疑,而莲步轻移,垂绦的发丝随着微微波动,带着暗香起伏,未及停下,便被他一把扯过,跌坐在他结实的腿上。成熟男子的气息扑面而来,是和宫中万千娇软截然不同的对比,身下的肌肉磐石般坚实,而扯着她的胳膊上臂粗壮,肌肉在衣物下贲起,是一只虔伏而在隐忍的兽,对着他的力量,她不可自控的在发软,“皇上~”,她不由轻呼出声,出口才发觉自己声音中的娇软微颤。
思念良久的人儿如今一团香气的被搂在怀里,百炼钢也化为绕指柔,适才他脸上的冷淡坚硬嘲弄似乎瞬间被抹平。
“嗯,朕在”,他闷声答,嘴唇埋在她的发中,“好香”,他寸寸缓移,呼吸着汲取着她的香气。“别怕,别怕”,他低缓的声音在安抚,他的手下滑摸到了她柔腻的小手,轻轻摩挲着,“皇上”,她又是一声颤呼。“在外行军打仗这半年,每日累极偷空歇下的时候朕都想着你入睡,便是苦闷中的唯一安慰了”,他轻笑了下,带着她的柔夷,让她撑在他肌肉起伏的左胸前,贴着其下深沉有力的跳搏。“知道朕反复回味的是哪幕吗?”,她低垂着眼神微微摇摇头,只是轻颤,他眼角的几丝浅纹也满是笑意,“呵,是那次你偷偷溜进承干殿”,“月光下你褪下裙子那一幕,每一个细节朕都清楚的记得,一遍遍地回味,那天的你也同现在一般,穿一件这样的浅红裹胸呢,呵呵”,他说着,手指轻轻拂过她裹胸包着的峰顶,却未做停留便滑下,伸进浅浅披在她身上的薄纱,火热粗糙的掌开始轻抚那一段柔滑的柳腰和后背。那细嫩的腰不过他一揸宽,她被他掌心的温度烫到,带着一声呜咽轻呼出声,“皇上,别”。她不安的在他腿上挪动,臀却不小心碰到一段炙热的坚硬,不由面带粉色轻叫出声,只敢瑟缩的坐着,而他不动,只带着一抹玩味的笑享受着她的羞赧,“怎幺了?怎幺不动了?”
他挺起身贴近她,“每次一想到那一幕”,唇磨蹭在她耳边,声音几近微不可闻,“朕都硬的不能自已”,他说着带着她的手摸向他身下火热的坚硬,她被那触感烫到,蓦地缩开,而他靠在她耳边,暧昧低笑。
说起她偷偷溜进承干殿,两年前的一幕回忆不约而同浮现在两人脑海,而随之悄然爬上她嘴角的则只是一抹苦涩。
秉元三年,她十七岁,入宫一年。心机费尽,乃至自荐枕席,却丝毫不得圣顾。他身边的李公公是看他们长大的老人,对她多有怜惜,才答应偷偷放她进了后宫本无宣禁入的承干殿。
在那之前,她做了各种准备,翻遍她各式渠道搜罗来的箱底书春宫画,学习各种伺候男人的路道,就差要去拜妓女为师。她娘早早去了,除了嬷嬷没人能提点她闺房之事,而嬷嬷自己一生未曾嫁人,并无多经验。她把自己洗的香喷喷,准备到自以为无可挑剔,甚至选了那个他刚处理完政事理当心情放松的夜,偷溜到他独眠的殿,像献礼物一样走近他轻褪掉身上的薄纱,露出下面只着裹胸短裙的玲珑女体要献给他,鼓着勇气学着书里轻轻柔柔上前吻他抚他,没想到换来的却只是他的当场暴怒。
他怒斥李公公,为杀鸡儆猴竟是让他从此告老还乡。他却还记得李公公临走前的话,“老奴只是希望皇上过的开心一点,不必对自己这幺苛刻。老奴看着皇上晖王玉姑娘从小一道长大,心知玉姑娘她并无其他算计,就是心中欢喜皇上,想要靠近皇上。皇上整日辛劳,少有放松。这幺多年老奴瞧着皇上委实也不真厌恶她。以老奴之见,玉姑娘反倒是宫中少有能让皇上稍有开怀一二的人,这才愿助她一臂之力。皇上,莫辜负好时光哪。老奴一介废人,这一生无子无女,老奴从小看着皇上长大,说句大逆不道的话,对皇上那看得便比亲生儿子还重,唯愿皇上余生平安喜乐,老奴别无他求”。
现在她知道了,他不愿意碰她,是怕她会诞下皇子,以致单家坐大外戚把权,甚至也不愿她得宠,让单家多添倚仗。过后她听说那夜他后来随手抓了一个身边伺候尚衣的宫女便宠幸了她。所以当时她还是挑起了他的兴致的,可笑自己苦苦求而不得的,他随手便可赏于他人。
而这宫女竟也传奇,一夜恩宠便得孕在身,还偏偏争气,生下便是个小皇子。
说来也奇,三宫六院,个个出身大家,争相斗艳,之前竟是谁都未为皇上诞下一子半女,却被这小小宫女捷足先登。这毫无背景出身的宫女所生的皇长子因是当时唯一皇子,而顺理成章被封为太子。这季姓宫女也母凭子贵,飞上枝头做凤凰,一朝便被他封做季皇后。
有人说这季皇后是床第之间手段了得,狐媚惑主,不堪小觑,乃至今上被迷昏了头、对其言听计从、立后竟全不顾出身;也有人说,此乃今上英明有意为之,以杜绝太子之位再与权臣世家扯上干系。然而事已板上钉钉,是非故事便也仅局于茶言饭后、市井流言。
她还记得自己得知册封皇后那一天的巨大失落,是她全部梦想的覆灭,失落到她夜不能寐,而晨起不知何物撑她起身,不知人生再为何求。连早上给太后的请安都差点要耽误了去,去了也便是勉强装上笑容,越发拿出各种俏皮话逗太后开心以麻木滴血的心,见了他照旧行礼,而内心却如破了个大洞般空喇喇有寒风在吹。
是的,曾经她曾如何盼着每晨给太后的请安,很大的原因便是他每晨亦必去问安,因此可以借机见到他。入宫两年,他从来不会留宿于她的毓华宫,唯二的两次路过便也是坐坐就走,全是在给太后的嘱咐脸面,而盛装梳洗准备的她在他走后空坐失落,泪满衣裳而无人安慰。
每晨的请安是唯一可以名正言顺看到他的时刻。每天的打扮她都必费尽心机,只盼他能多看她几眼,而他却永远的那般仿佛雷打不动,不加侧目。不看她也好,她可每日看到他便也是莫大的安慰和奖赏,他宽厚的胸膛,高硕的背影,不多表情难以琢磨的坚毅脸庞都带给她莫名的安全感。他是她的天神,是她心目中顶天立地、无所不能的哥哥和男人。
孤寂的夜里,她总想像着他会揽她入怀,那结实宽阔的胸腹,有力的臂膀,他的怀抱会是世界上最安全与温暖的地方,会无言的给她无尽抚慰。一个人躺在冰冷的象牙床上时,她常掀开薄被,审视月光下自己光泽的赤裸身体,那修长纤细的双腿,平坦的小腹不盈一握的细腰,丰满隆起洁白的两团丰盈,对于任意一个七十以下的成年男子来说,都会是一副刺激的画面吧。一个如此韶华的女子独自寂寞,算不算是暴殄天物,她暗自呵呵想。她也会想像如果他那副健硕的身子压上自己玲珑的身体,想想便不禁心神荡漾,要脚趾蜷起,然而她尚未领略情欲的全部力量。
每次看到他的背影她都觉得如此亲切眼热而想上去抱住他的影子,可他从未给过她机会。深宫寂寥,而她年华正好,如同一枝盛开的牡丹,在寒风中瑟瑟摇曳而无人顾,不知花期何时尽,不知孤寂是否有尽头。而每天清晨见到他,她便又生出了力量,觉得可以在这空洞的宫殿中再支撑自己一日。
从少女时期起,嫁给他当皇后便是她的全部梦想。她曾为此痛下十分功,只为配得上他。博览古今史书,她梦想做一个贤良的皇后,在他政事有疑惑时可以点播迷津,成为他的坚实后助;苦练棋技,只求成为与他旗鼓相当的对手,在他消遣时陪伴他;琢磨茶艺,只为在他在他疲累时可以为他捧上一杯可心的茶水;书法绘画舞蹈弹琴,她样样不放松,只为在他政事烦琐之余能提供给他些许娱乐消遣;容貌仪态,她刻刻不松弛,只愿能取悦于他能担当得起母仪天下的风范。
然而又有何用,全部付于东流水,他竟是挑了一个小家出身字都未毕认全伺候枕席的宫女做他的正宫皇后。何等的讽刺,而对当时的她来讲又是何等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