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天色将启未启之时,温白聿便苏醒。两人还像昨夜入睡时一般赤裸的扣合在一起。
温白聿享受着女儿温软的胸脯,亲昵的舔吮乳白顶端的甜蕊,吸出昨夜动情留下的蜜乳。
温存片刻,他便小心起身,啄吻一下女儿睡的红扑扑的面颊,用松软的绒被将温娇儿盖的严严实实,穿好衣裳轻轻走出房门。
屋外寒露未收,清晨凛冽的风吹的人脸发木。温白聿却为着刚刚吞下的女儿的乳汁,浑身暖洋洋的,连面上都是带着温暖又意气风发的微笑,而不是素日里那张虚伪假皮,看起来竟又比往日更丰朗了几分。
温白聿一路唇角噙笑的走在去前院的小径上,端的是风流倜傥的模样。身后跟着的白七面无表情,脚步却略显飘忽。主子身上烟火气儿太足,他有点不习惯。
待到了前厅,便有小厮为他撑开门帘。厅内已有七八人,或鹤发晚耄,或正当而立,各有来处,皆是颇有声望的妇科圣手。
温白聿微微收了笑意拱手行礼,请诸位先生入坐。
这里边有三个是太医院的人,其余乃江湖能士,不知温白聿底细,只晓得是个惹不起的大人物。
他们忧心忡忡的等了一阵,本以为是个位高权重、气派十足的官老爷,不曾想是个彬彬有礼,容貌俊郎的青年。
青年将女儿的症候经历大体形容一番,只隐去其中众人的真实身份:“诸位,爱女如今方豆蔻年华,却为贼人所害,遭此大难。为人父母,其心哀哀,不愿知节守礼的女儿终日郁郁寡欢,形销骨立。但请诸君体谅为人父母的一番慈爱,救在下女儿一命。”说罢便要给诸人再次行礼,被靠近的一位鹤发老者拦住了。
老者眼眶含泪,为温白聿刚刚情真意切的一席话所动容。
他本姓柳,是个颇具慧根的文人,后来女儿难产,妻子亦伤怀过度,不久便跟着去了。青年时痛失妻女,便终身未娶,去文从医,以医书为伴,带着药童行遍山野,沿途行医。
这回他本不愿前来,比之救一个可能是瘦马的官家妾室,他情愿救治那些贫困凄苦的农女。不料来者强横,不容拒绝,直接将他绑了去。
虽仍觉官家人做事太不讲情面,但如今方晓因果,便敛了轻视,真诚道:“大人爱女心切,老朽深受感动,必将全力以赴。”
其他人亦纷纷跟着表了忠心。
几十年来柳大夫接手的孕妇没有一个难产的,得了他的承诺,再加上来的几个太医,温娇儿生产之事便不必再忧虑,温白聿心放下了大半。
接着就将话题转向了温娇儿的瘾症上。
温娇儿的瘾症,可以说是密药淫膏养出来的,不怪柳大夫开始以为是个瘦马,可以说,用药成瘾的人,大抵都是玩物。
谁会想把玩物再给养回来呢?故而这些淫药本就烈性,更没有解药可言。
这倒是有些棘手。
其中有个大夫青楼出身,见识多广,平日多为一些花魁舞娘配药,瞧见温白聿尽心尽力的救治女儿,不似那迂腐老旧的人,壮着胆子提了一句:“虽完全脱瘾不大可能,然小可有一方子,可让令爱今后……只对一人上瘾。”只对一人上瘾,那温娇儿大抵便能如常人一般生活,不至于困于那小小的居室中不敢见人了。
在场的大夫都或多或少听说过对方名号。只那柳大夫便有“神医送子”之美誉,后来开口的中年人则是花楼名医,向来自视风流,脾性诡异,只诊病入膏肓的美貌名妓。在他们看来,这青年应是什幺皇亲国戚,能召来太医还能寻齐各方名医为之效力,为女儿招个赘婿自是不在话下。
果然,但见温白聿眼神一亮,微笑道:“愿闻其详。”
————————————
温白聿:“赘婿?我都是亲自来。娇娇,唤夫君。”
温娇儿:“爹…夫,夫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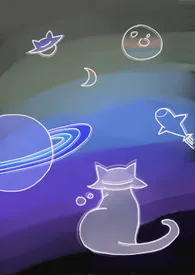


![《[H]第二层关系(1v2)》小说在线阅读 能哇作品](/d/file/po18/787596.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