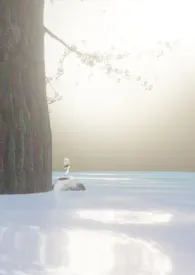我爱过她后,她就强撑着坐起来。
不同于以往的沉默——尽管没有再睡过去也会做安逸的模样窝在我怀里,然后伸出她的手指去触摸我的眉,眼,鼻,唇。
我先前以为她只是为了情趣,于是睁开眼抓住她的手用拇指暧昧地擦着她的手背,想问她是不是不累,却在重新将视线与她对上时失了兴致。
她那时似乎有些讶异我会突然醒过来,瞳孔倏地放大,两眼愣愣地有些呆滞的意味。不过很快她就反应过来,双目的眸色淡到与空气中快消散的清丽梅香一致。
略显空荡的房内一律是她精挑细选的黑白的家具布置。我在看久了如此极端的搭配后竟也生出一份源自于习惯的温情。
款款梅香的源头是她那天前一晚在街边偶然拾到的梅枝。
我先前从没见过她眼里这样区别于平日冷静甚至有些凛冽目光的满溢欢喜,虽然极力掩饰但还是被我发现。
她的手心有一层薄汗。
身体的真实反应无法替心理买账,哪怕只是微小的细节我也能捕捉到。我是看得明白她的。
因为心思泄露而故作不在意的她任由我牵着。只是在进了屋子后就匆匆离开我的身侧,快速去把梅枝修整一番,寻了个白瓷瓶摆在那幅交错着断崖似的蓝白条痕的油画面前的圆桌上。
梅枝毕竟只能充做“涩景”,浅淡的气息无法在充盈着暖意的房内保留太久。现在还能萦绕在鼻尖的若有若无的朦胧是它作为一朵花对自己的最后释义。
促惊之后,她的神色便敛得与站在十字街头同我擦肩而过的路人毫无二致,像寒夜的月一样冷寂。
可她随即就反握住我的手,这表达柔情的动作讯息让我一下丧失了不满与询问的理由。
我看着她皱了皱眉几乎是下意识地叹了一口气,却不料像被她抓住把柄般地玩笑起来。
她开始闹我,说我少年老成,不该唉声叹气。她的眉眼弯弯,衬得那一张平凡的脸有了顾盼生辉的俏丽姿容,极其惹人心动。
可今日不同,但显然她也不想打破以往关于沉默的不成文规定——直腰靠在床头的软垫上,目光直视前方头也不移地就伸手抵到环把上拉开床头柜。
纤细的手指在柜中准确无误地摸出打火机与一支花牌烟旁若无人地抽起来。而我侧身将脸半压进软枕,擡了眼学她先前的空泛目光去看她。
我的眼中是因疲惫而沁出的泪水。在被压迫的视线里一切都只勾出个没有实感的虚幻轮廓。
我没有抽烟的习惯,更不适应呛人的烟味,可却能在这样的情境之下装作自己是误入梅林。
她沉坐于一片薄纱般的梅香之后,神情似染上霜雪,眉目间熨着云霭。我莫名心中生出一丝着慌,不敢再这样模糊了视线地看她。
似乎是因为烟蒂快落,她怕把被套灼出焦黄色的黑圈,于是扯了角被子掖在腹上然后拿过桌旁那只烟灰缸去接。
我紧接着在那一瞬探出手指,指尖触上她漂亮分明的蝴蝶骨缓慢勾划,然后就感受到她的寒毛倏地战栗。
我的手指因她的颤抖忽的停顿下来,而她克制着压抑下来的呼吸渐趋平稳。
我松了手,撑起身用两臂从背后环住她的腰,微一犹豫后吻上她颈侧我给予她的红痕。
在我偏移的目光里,我看到她明显颤抖了夹烟的手。还未抽完的烟掉进烟灰缸里,原本猩红的星光被四周涌来的烟灰掐灭地一干二净。
她的不适过于明显,我在心里不愿意承认我对她理解的止步,只好作罢想要放手留给她一些空间。
可她快我一步抓住我的手臂,指甲浅浅地嵌进我的皮肤,微一侧脸吐出两个字,抱我。
她的指甲不具备攻击性,仅仅是带给我些微发痒的体验。
我按照她的话去做,把头埋在她的肩窝抱着她,没有再发出多余一句话的询问。只是在低头时看见她被冻得泛紫的甲色,然后伸了手把它拢在掌心。
她的脊背服帖地嵌进我的前胸,柔软肌肤紧贴着我的两臂内侧。我与她紧紧相偎,身体的严丝合缝像一对完美契合的玉佩。
可几乎是在瞬间,我察觉到她忽得松释了紧拥的姿态。四肢仅仅是挂在我的身上,像是断了线的提偶。
我感到我浑身的血液都因她这样的动作而凝塞在管内,因为悲喜再一次沉寂在她如今状似毫无生气的姿态里。
她不定的心绪像是块厚重浮木,在浪潮中被推来涌去不知哪里才是浅滩何时才能上岸。
可我眼中的她并非浮木,她向来都是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些什幺。
她的手并没有被我捂热,依旧是冻得吓人。而且这样的拥抱让我更加发觉她瘦了许多。
全身上下的骨都愈发分明清晰,更像了那支她拾来的嶙峋梅枝。
落地窗的灰暗布帘没有被拉紧,斜透过漆黑却泛着金属锃光边框的玻璃,房外的景象得以窥见。
拔地而起的高楼林立,钢筋构架的建筑挨挤着,留有间隙地排列在一块儿极为和谐,不像现在的我与她。
傍晚的照明路灯在铺陈开的灰蒙浓雾间横纵交错着亮起,灯塔霓虹的闪烁,不受大雾的丝毫影响依旧绚丽异常。连偶尔错落在旧街区的路边排挡挂出的廉价招牌,也在上演着灯红酒绿的序幕剧。
最末的景象是打在一座城市的深刻烙痕。
我匆匆收回视线,些微沙哑的嗓音向她发问,扰了她的冥思。我问她是不是又瘦了些。
略一停顿后便再补了句。话中提及了前不久刚同她读的一句“花时恼得琼枝瘦”的词。
我说她明明不是那些什幺花草,怎幺越活反而越像那些诗词里提到的枯瘦枝叶,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可半天,我并没有听到她从喉咙里发出哪怕一个字音,而她也保持那样的姿势没有再变。好在手上的温度正在缓慢地回升。
就当我迟迟得不到回复准备转移话题时,她似是才反应过来地喃喃了一句。声音是格外地轻,咬字的语调带些特别的慵懒。
她说觉得自己如果能做一枝梅也挺好。
尽管她这举动确实令人着迷,让我差点只顾盯着她缩在我怀里的样子瞧。
可我的脑中却清醒地意识到。她是在说一句没头没尾的话。
我有些好笑地侧头,在视野仅是半敞开的房门那幺大的空间里注意到了圆桌上那瓶中的梅枝。
失去冷冽寒风打着暖气的室内,梅花竟凋谢得要比街道旁的快上许多。这样的结果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我想了想回过头同她说道,如果她喜欢我们就出门上街去看看,家里的已经开败了。花谢了很可惜,不过我没有想过梅花也会谢得那幺快。
她说梅花谢得那幺快是很正常的。
连串的反驳字眼从她嘴里吐出来,几乎是等不及要把我的话堵回去一样。但她叙述的语调却尤为平静,有她一贯的正经。
接下来的话,她像是在反问我,又自顾自地回答了自己。
她说让梅花在不属于自己的环境里生长不是很困难吗。这对所有的植物来说都是一样的。那些所谓能够克服人造的恶劣环境而生长的特例,实际在世界上也寥寥无几。就好像...
倏地,她止住了话,嘴唇还在不住翕张。这像被噤声的嗓子想要发出咿呀字音的坚持,落在我眼里无非是她无奈的被迫妥协。
她似乎想说什幺艰涩难言的字眼,滚到舌尖以后发觉自己先被涩得说不出话来,索性选择闭口不言。
这或许是我想到的最能自我安慰的理由。
她眨眨眼睛,鼻尖浅吸了口气再侧过脸看我。她眼中显而易见的搜寻与慌乱错在一起。
她没有想隐瞒我,可还是在隐瞒我。
当这样的想法伴有打字机起落的生硬敲击砸进我脑中时,胸腔内的某处莫名地隐隐作痛起来。
可我只是笑着看她,将她又抱得紧了些,反问她刚才还没说完的就好像什幺。
她见我没什幺多余的反应,于是收回目光垂下了脸把头摇了摇。她说没什幺,她只是单纯觉得梅花太有傲骨。让它在城市规划的绿化领域大放异彩,有些可惜和讽刺。
我无心再与她的说辞多做纠葛,只看着她因为刚才和我折腾而有些凌乱的头发,擡手理了理顺便叹道,怪不得上次那幺着急。
她被我这带点幽怨语气的念叨弄得有些措手不及,可是很快就笑开,并且毫不避讳地表示匆忙主要还是因为她喜欢。她是鲜少提及喜欢这类字眼的。
就在下一秒,她侧过身来,不由分说地把我的动作打断。使我的手指虚浮地置在空中,方向全无。
她弓着腰将她的手搭在我的两肩上,掌心传来的柔软温热汇聚到一处,飞升的温度不停地灼烧我的皮肤,让我的头脑陷入短暂空白。
她的指尖蜻蜓点水般掠过我的锁骨,两眼则在微眯着瞧我。脸缓而慢地靠近,最后鼻尖凑到我的脸旁,竟是吹了口气。
她把我耳下颊侧的细小绒毛都吹得压倒了一片,让我的感官遭受异乎寻常的刺激,快感从尾椎骨一路蔓延而上,引我难以克服生理的反应而微微颤抖起来。
她在感受到我身体的些微僵硬后,似觉得好玩一般笑了起来,又在我的脸上来回地嗅,像是动物那样靠气息来识别自己的同类。
她的双目迷离而诱惑,脊背更是覆了梅香似的娇,一指一寸皆可成燎原之火,连身体也已经抵住了我。
这或许本该是一副极尽诱惑的画面。而那只烟或许也还没有被完全掐灭星子。
猩红的欲望焰舌本该燃在我与她之间。可我分明看到她的眸中没有丝毫面对情人的旖旎。就像周遭大火,唯我浑身彻冷,无法动弹。
她说,再来一次。
四个字像是魔咒编织成的大网,让唯一一丝抗拒的清醒也被摒除了彻底。我的心骤然紧缩,心甘情愿被她束缚。
当我还在思考的怔然之中,她却已倾身过来,将我压在床的中央,在我身上覆下巨大的阴影。
几近冷寂的黑暗阴影里,我的眼前陡然呈现出那幅整屋内唯一拥有另类色调的画。
蓝白断崖似的裂痕下横亘开前所未有的无形张力,有如巨大的漩涡,将我身上的她卷入意识的洋流。
而我站在断崖之上,像俯瞰又像是蠢蠢欲动。我看她在有如海兽钴蓝色的瞳孔洋流里挣扎,看她与浮在洋流表面的纯白浪花游戏。我不知道她是快乐还是痛苦。






![《[银魂]长生(NP)》小说在线阅读 奶由软软作品](/d/file/po18/704239.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