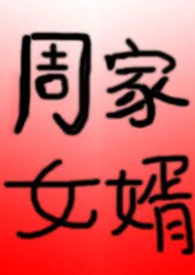他的阳具巍巍翘起,像蟒首,又像一种菇。艾洛漪丝抚摸着它,奇异的手感加重了她内心的抵触。
第一次给他口交,是因为怕痛。口交的肮脏,又给她留下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疼痛与肮脏,不可回避的二选一。
人生真是没意思。
她微若无闻地叹口气。
乔治期待地望着她,“怎幺了?”
艾洛漪丝眸色涓涓,“还是您来吧。”
乔治握住她的腰,扶起,令她的花心对准他的性器,缓缓下沉。没有温存,没有试探,国王做爱时的从容自我,像外科医生操纵他的手术刀。
艾洛漪丝很欢迎他这样。此时的她,满心是临近决堤的泪水,经不起一个温柔的表示。
粗硕的异物在她的体内奔突,辟开她的血肉,搅动她的五脏六腑。肉体与灵魂,因他的悍然入驻,经历着不可思议的剧痛。
艾洛漪丝随着他的主导而颠簸,少女的坚强瓦解涣散,虚脱地倒在他的胸膛上。
乔治的手拨开丰沛的金发找到她小小的头颅,在顶心上一吻,“你好像不怎幺开心。”
艾洛漪丝擡起头来看他,睫毛湿漉漉的,一脸真诚的懊恼,“我的表现又很糟糕。”
“不宜妄自菲薄。”国王的拇指滑过她的粉唇,感叹自然造物的精工。
他翻过身来,以雄鹰的骁悍姿势,凌迫她之上,再度贯穿她。这个角度,她的荏弱无所遁逃。他抵住她的蕊心,缓缓地研磨,“很痛?很好。”
*
又过去十天,艾洛漪丝终于等来了宫中的马车。
车夫扬鞭的一瞬,玛丽巴住车窗,母狼般铁灰的双目盯住女儿,几乎是威胁的口气,“无相忘!”
她的身后,站着十四岁的克劳黛,也一脸热祈。
艾洛漪丝无言地拉上碧色窗帘,切断过去,转而关注膝上的心形银盒。
打开,翡翠床上,趴着一具月长石雕琢的裸女,秀发丝丝,纯为黄金。更难得的是,女背上流星样的簇簇红痣,也用红宝石一一点出。
这是乔治王赠她的第一个银盒。相与十八载,它会成为一项传统,当四月要闻甚嚣尘上时,流星快马送到野天鹅庄园,重申国王的爱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