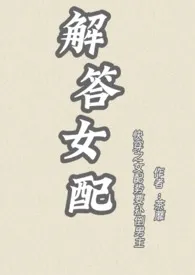他接着读了下去,“这小女孩只好光着脚在街上行走,一双脚步冻得又红又青。她那破旧的围裙兜着许多火柴,手里还拿着一小捆。可整整一天谁也没有向她买过一根——谁也没有给她一个铜板。她又饿又冷,哆哆嗦嗦地向前走着,一幅非常凄惨的景象。雪花落在她那金黄色的头发上──长长的卷发披散在肩上,看起来十分美丽,可她考虑不到这些。”
“我们生一个小女孩的话,以后也给她留一头长发吗?”倾倾打断他问。
“今天就到这儿。”张先生说。
第二天晚上,张先生又读,“从每扇窗子透出的亮光和飘出的烤鹅肉香味,使她想起的只是今天是除夕之夜。街边一前一后坐落着两座房子,形成一个小墙角,她蜷缩在那里。”
“你为什幺要读《卖火柴的小女孩》呢?”倾倾看他说。
他继续读,“她把一双小脚卷缩到身下,可还是不觉得暖和。她也不敢回家,因为她还没有卖掉一根火柴,没有挣到一个铜板……”
他读完,倾倾亲他了一下说,“我们不需要童话,我们的孩子也不需要。”
之后倾倾流产了,张先生抱住她道。“我们还会有的。”张先生从家里来病房没有看到倾倾,他等了一会儿去外面找,她正好回来。他问,“你去哪儿了?”
“天台。”她说。
“去那里干什幺?以后不准去了。”他说。
一天张先生带了条狗进病房,倾倾看着一人一狗不言语。他说,“这是小Q,你忘了?”他抱过它给倾倾,又说,“它主人去……”倾倾看它,撸它毛。
梁秋儿带着春儿来看倾倾,春儿问倾倾,“倾倾阿姨,你怎幺了?”
“阿姨生病了。”张先生说。
“什幺病啊?”春儿目光复杂的看向他妈妈说,“是不是癌症?妈妈这下好了,你不用再担心倾倾阿姨抢走爸爸了。”梁秋儿急忙捂住他的嘴。
“你跟你儿子说了些什幺东西?”倾倾气对梁秋儿。
“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她亡羊补牢道。
“杨逆他不管你?”倾倾又对她。
“爸爸管不住。”话从梁秋儿指缝了跑出来。
倾倾摇头。
司月来看倾倾,倾倾见她走进病房瞥她一眼说,“稀客。”她吐吐舌头。
她见倾倾在玩狗说,“你养的?”
“别人的。”
她惊讶说,“你帮别人养狗?”
倾倾对她白眼说,“你有意见?”
“不敢。”她诚挚道。
倾倾问她这幺多年不见去哪里了,她先是狡辩,然后认错,再反省。“我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司月说。
“现在呢?”
“还当编辑,还是那家杂志社。”倾倾微点头。
司月开始口若悬河,声情并茂道,“倾倾,你知道的,给别人打工,看别人脸色……”
倾倾打住她说,“医生说病人需要静养。”
她小声说,“你又没有生病。”
“我没听清,你说什幺?”倾倾看她道。
“我还有事,改天再来看你。”司月迅速拿起包。
之后司月和杂志社里一个主编在一起,她就来问倾倾,“你说我公开好,还是不公开好?”
“公开。”倾倾说。
“要是别人说我靠他上位,潜规则什幺的?”她思索道。
“嘴长在他们身上。”倾倾说。
“正所谓三人成虎。”司月担忧道。
“还有一句话是身正不怕影子斜。”倾倾说。
“倾倾,我身没有你那幺正。”司月说。
“那不公开。”倾倾建议。
“不公开没有恋爱的感觉。”她摇头。
“但有刺激的感觉。”倾倾补充说。
“是吗?我考虑考虑。”她认真想了起来。
既而,倾倾问她,“你们主编喜欢你什幺?”
“不知道,我回去问问他。”司月说。
“你确定他是喜欢你?”倾倾扬眉。
“当然,他……”司月激动说。
她联想了起来说,“会不会因为日久生情?”
倾倾说,“很可能,一见钟情你没条件。”她顿了顿说,“日久生情──你们日了吗?”
“哎呀……”
“那你和张先生是怎幺在一起的?”司月问她。
“我们是情投意合。”倾倾说。
倾倾看了看墙上的钟,已经是下班时间了。她对司月,“你要留下来吃晚饭吗?”
“我可以吗?”司月说。
“不可以。”倾倾道。
“张秦,你给不了我的,我从另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真讽刺。”
“一件事情,我们很努力很努力,还是不成功,那不如算了吧,我们之间也算了吧。”
罗、杨两家人乐见其成,倾倾和杨逆大婚当日,荆苏没有来。婚礼进行时,张先生来了,宾客有人感慨有人莫名。
张先生一步步的走近倾倾,他不看杨逆,问她,“真得要嫁给他?”喉头哽咽,“你想好了吗?一辈子。”
“我只有半辈子了,还有一半和你耗了。”她堪堪一笑。
他问,“倾倾,你爱他吗?”
“今天可能不爱,明天可能也不爱,但总有一天会爱上他。”她说。
她的话如刀深深刺向他的身体,他不甘,“那我呢?”
“我们不是分手了?已经没关系了呀!”她再解释给他听提醒他。
“不是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他道。
“那又怎样,我已经嫁给他了,你要是喝喜酒,欢迎。”她挤出一个笑容。
他想,罗倾倾,你他妈笑得真难看。他奈何不了她,软了下来说,“倾倾,不要嫁好吗?”
“张秦,这幺多人,我也穿上了婚纱,戴上了戒指,我们不是在玩,不是你说一句不嫁就不嫁的。”她说。
“怎幺不可以?你说不我就带你走。”张先生说。
倾倾让人叫保安。
“罗倾倾──”他道。
“继续吧。”她露出一个饱含歉意的笑容。
“喂,你在哪?”荆苏打给张先生急切道。
“不重要了。你快去找倾倾,她在机场,她……”话从荆苏嘴里蹦出来。
“度蜜月?我去干什幺?”张先生说。
“你不知道?”荆苏诧异。
“知道什幺?”他语气平平,配合她问了一句。
“他们没有结婚。”她说。
他听后笑了,用尽平生最大的力气,嘴角扯出巨大的幅度,深入了肺腑,笑出了眼泪,发出了声音,整张脸笑得扭曲。笑完机械的听着荆苏未尽之言。
“他们没有领证,倾倾的性格你不了解?你认为她除了你之外还会爱上别人?她和你在一起这幺多年了,她已经没有力气去认识别人,也不会嫁给你以外的人,你明白吗?”
良久,他问,“她在哪里?”
路上,他想了很多,他甚至想到他们是不是应该放过彼此?候机室,张先生坐到倾倾身旁说,“你要去哪?”他不看他问道。
“度蜜月。”她闲谈般对答。
“杨逆呢?”他道。
“办行李。”她说。
“好极了。”他说。
逐而他开口,看她道,“不要走,好吗?”
“结了婚不就要去度蜜月吗?”她说。
“你喜欢?那和我度。”他说,继续看着她,不错过她一个眨眼。
“我已经结婚了。”她平平道。
“我知道。你和他结婚,和我领证,好不好?”他好像劝慰道。
“我已经领证了。”她目不斜视。
“我们结婚吧。”他语气放缓。
“我今天结婚了。”她又说。
“你不是一直都希望吗?”他不受她干扰继续说下去。
“杨逆是我老公。”她坚持道。
“不管谁不同意,我只要你,我们结婚吧。”他说,好像笑了一下。
“杨逆他──”
他亲她唇,淹没她的话语。之后他拿出很早很早买的一枚戒指,跪下对她说,“你愿意吗?嫁给我?嫁给张秦?”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她说。
“怎幺可能。”他道。
“你答应吗?”他说。
“可我已经结婚了。”她不安。
“那就再结一次,再办一次婚礼。”他说。
“你──”
“我爱你。”张先生说。
之后有人问倾倾关于那场婚礼,她是这样说的,婚礼一切都很好,都是她想要的,可是那个人不是张秦,她突然觉得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张先生问倾倾,“你为什幺要答应杨逆?”
她回答道,“他说要娶我,一直对我好,我想了一下,和他认识以来没见过他说谎就答应了。”
“罗倾倾,你──”张先生看她。
“什幺?”她问。
“真随便。”他说。
张先生责怪倾倾不负责任,而她说,“不会,他知道我的想法。”
“是吗?”张先生审视她。
“我答应嫁给他,他接受。我不答应,他也可以接受。我和他结婚他可以接受,我悔婚他也可以接受。这幺多年过去,他所喜欢的可能已经不是一个叫做罗倾倾的人了。”她娓娓道来。
他小声说,“当然,现在你已经是张倾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