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赶过了东四牌楼,就是南小街。
全子咬着烧饼说:“那烧饼铺掌柜的说,徐家宅子就在这儿了。”
桂娘看她弟弟这憨吃的样子就生气,但鉴于全子刺探情报有功,也就没骂他,专心看起路来。
这地方果然是个荒凉的所在,四周寥无人烟,借着朦胧的月色,勉强看得见沿街凭空起的一路院墙,在往前走,街心蹲着两只石狮子,夹峙着中间三间兽头大门。匾额已经给摘去了,认不出字号,可左右几里地就这幺一座大宅,桂娘便叫停了全子,让他栓骡子,自己和银瓶走上台阶,到了门前。
斑驳黑油大门上了封条与铁锁,银瓶与桂娘合力推了推,只开了浅浅的一道缝隙。好在锈死的铁链松懈,她们撕破了封条,缩着身子,竟真挤了进去。
高深的大门合上,吱呀一声,惊飞了避雨的燕雀,凄厉叫着一阵翅膀,飞到那边儿去了。留下一个黑黪黪的世界,空有着轩昂的院落,画墙满长青苔,砖缝杂草丛生,稀稀落落地下着雨,像是聊斋里住着鬼的阴宅。
全子小声道:“姐姐,你觉得这世上有鬼幺?才那掌柜的说都传说这宅子闹鬼,所以才一直没顶出去——”
“闭嘴罢你!贼娘的小猢狲儿!”桂娘吓得哆嗦,更骂了两句给自己壮胆,又扭头问银瓶:“这地方,你可有印象幺?”
银瓶只是摇了摇头。
尽管不愿意承认,她却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劲——平日里最胆小的人,走在这荒宅里却并没有丝毫害怕。他们顺着府邸的中线慢慢走,银瓶惊异于自己竟真的对这里的设置有一股子直觉的知道。比如内仪门后的院子西角落栽着参天的梧桐,比如抱厦后面应当有一座小小的凉亭,凉亭与南北夹道间隔着座粉油影壁儿……
是卖油翁“熟极而流”般的熟悉,走到那里便知必有那幺个东西在,只是旧了,破了,成为了欹损垣墙,歪斜台榭的所在。
银瓶的心怦怦地跳着,莫名地有种近乡情更怯的畏缩——可这里怎会是她的乡!她头痛得愈发紧了,索性加快了脚步。府邸的尽头是后花园,山子门半掩着,并没有上锁,银瓶推门挤了进去,在月色下先看见满眼参天的枯树,一棵树下倒着架秋千。她闭上眼睛,想象它们枝叶扶疏的样子,倏然像是回到了暮春。
是了,春天,一年里最好的时节。
春日里消春困,拿汗巾在树下扎秋千,恍惚中她自己正站在画板上,在香风里高高荡起来,笑得身子发软也不肯停下。
这样快乐的时光,不会是在勾栏里。
那会是在这里幺?
秋千飞到半空,远远可以看见假山外金碧琉璃瓦的庭院。有个绫罗裹身的夫人款款走进了院门,把手搭在一个丫头的手上,然后擡起头,看见了她。夫人骤然变了脸色,立即叫丫头拿了她来教训。
她怕了,慌忙跳下秋千,跑了。
尽管看不清脸,她知道那一定是她的母亲,那座院子——如果有,也一定是她母亲的上房。
银瓶倏尔睁开了眼,转身向外跑去。银蓝的月光像梦一样,她循着梦里的痕迹,踉跄着到了秋千上看到的地方,果然见有一座黑油大门的院落。她的心荡了一荡,急不可待地迈进去,不想先给门槛子绊了一跤,人狠狠倒在地上,头也磕上了门槛。
她头痛欲裂,伏在地上打了个激灵,耳边却忽然嗡嗡作响,连淅淅沥沥的雨声都宕远了。远远的,仿佛听见前朝宫殿的锣鼓,恍惚中宣告着梦的终结。
荡悠悠的一刹那,过往海啸般涌进脑海,前十六年的人生走马灯似的回旋。
她蓦得矮了,小了,变回了小孩子,在戏台下看着自己的扮演——扮演相国的女儿,那个驰名京城的闺秀,在金玉阑干的香闺,在繁荣阜盛的京华。
宫灯的光是淡火红,映着她的一举一动,也像是灯笼上的美人。
……
“娘!”
不知道到了什幺时候,银瓶丢魂失魄地大喊了一声,爬起来撞进了门去。
宽敞的院子里,雨很小了,月亮高升,伏在正房琉璃瓦的飞檐上映出一层银霜。银瓶跌跌撞撞扑到房门上,门被锁得死死的,她把手拍搡着门。拍不开,把手拍肿了,也只是拍。
“娘!娘!”
虚胀的嗓子从她的喉咙里逼出来,眼泪混着雨水淌。
“娘,你开开门呐娘,是我,是婉婉……爹,哥哥,哥哥——怎幺都不理我了?娘——”
桂娘好容易跟上来,看这光景便猜出了几分,一把揽过跪在门旁的银瓶。
“你、你可是想起什幺了吗?”
“同喜,同贵——快开门,娘,三年了,我回来了——”
她挣脱开桂娘的手臂,挣扎着扑在门前,也像伏在阿娘的怀里。两只手臂震麻了,喉咙也哑了,说不出话来,只是放声大哭。哭得撕心裂肺,满面通红,像是出生的婴儿有音无字的剧烈的啼哭。三年前的惶骇,三年来的心酸,隔着阴阳的界限,诉无可诉,只能化作无尽的眼泪还给阿娘。可沉重的大门早已生了绣,在这掩埋在尘埃下的庭院里,只有嗡嗡巨响悲怆地回应着。
直到头昏脑涨再也支撑不住,她往后一倒被桂娘接住,眼中终于闯进了旁人的影子。她没有力气再哭,怔怔看了桂娘半晌,忽然笑了。
“我竟忘了,娘她……就是吊死在这里了。我没看见她最后一面,林妈妈不让我看。”
桂娘后背发凉,“银——徐、徐姑娘?”
银瓶移开目光,擡头望了望檐下空晃晃的鹦鹉架,“娘说,徐家的女儿,不能活着丢人,她死之前,吩咐林妈妈一定也把我勒死。林妈妈舍不得,给我换了身丫头的衣裳。我混在下人里,被官府的人领出去卖了,她却、她却——给他们砍死了。”
她脸色苍白的像纸一样,雨打在皮肤上也像洇透了纸,一个雨点子就是一滴泪。
桂娘从没见过她这样,说不出话来,见全子也跑了来,忙叫他搭着手把银瓶扶到了一处没上锁的穿堂。那堂屋里也许曾是个书房,满地破凳,折桌,坍塌的书箱,埋在灰尘里。桂娘见角落里扣这个铜盆,忙捡了过来,又弄了些书卷纸来,叫全子用火石点了取暖。
火苗子扑腾上来,银瓶恍惚着,十六年的荣华与三年的折磨打成了一片,如梦似幻,让她简直分不清自己是谁。然而她实在累得狠了,烤了会子火,也慢慢静了下来,合着眼坐在地上,倚着身后的一只桌角。
过了很久才听见桂娘的声音。
“徐……徐姑娘?”
她睁开眼,看到桂娘试探的目光,咬着嘴唇小心道:“我叫您徐姑娘,您没意见罢……”
她笑了,“我闺中有个名字叫做令婉,不过少有人叫……也好,姐姐愿意,就叫我徐姑娘罢。”
桂娘见她白绫子裙几乎湿透了,便问:“城门关了,今儿怕是要得在这宅子里过夜。徐——徐姑娘,你可要换身干净衣裳幺?”
银瓶摇了摇头。她四下里看了看,依稀认出这是娘从前抄佛经的小暖阁。
桂娘余光瞥见地上摔着把裁纸的小刀,心里一惊,忙一把拾了起来。
银瓶倒疲惫地笑了一笑:“何苦来……我可没想着寻短见,若要死,早在三年前便投了海河了。”
她坦然地提起从前,倒让桂娘愣了一愣,睁眼看着她,又试探道:“……既这幺着,咱们今儿凑合两三个时辰,等城门一开就赶紧走罢。我想着,咱们先往我家去,住些日子,等二爷打了仗回家,再想办法找上他,如何?有他在,想是什幺事都有办法解决的。”
“不成了,我见不得他了。”
桂娘唬了一跳,“姑娘这话是什幺意思!”
银瓶叹了口气,“好姐姐,有的话我不好对你说,你也别问我。若姐姐不嫌弃,肯带我一程,就连累姐姐。等我歇下脚来,就去投奔一个人,绝不多拖累你。”
桂娘忙道:“姑娘要找谁去?”
银瓶没言语,坐在地上看着火苗子,很平常的姿势,也还是那张婉媚的鹅子面,但不知怎幺就有一种美人瓶似的从容,完全地像是变了一个人。
十六年诗礼教化滋养出的富贵闲人,也不过就是怎样站,怎样坐,怎样吃,怎样睡。从前年纪小,贪吃爱玩,撒娇淘气,爹爹的君臣父子,娘的三从四德,她都不喜欢,然而有些东西早已渗入身体,镌刻进了她的骨血。等到他们都死了,都散了,飞鸟投林,天地间只剩下她一个人,她不得不为他们报仇,不得不履行他们的遗志。
隔着三年迷离的回忆,她恍惚还记得太后下旨赐婚的那个夜晚,爹爹托付她的骇人的秘密——
那个当年真正应当坐上龙榻的,是六殿下。
原来先帝临终时只留下她爹爹徐相一人,秘密告诉了他遗诏的所在,又托孤似的将奉旨查边的六王托付给了他。然而很快,七殿下的兵马以护驾为名闯进内宫,在先帝驾崩之时攻破了銮仪卫的封锁,抢夺玉玺,登基称帝。爹爹为求一时自保,便也将遗诏之事秘而不发,归顺了新皇。只是新帝登基不久便在拿旧内阁做垡子,斩杀了多位阁老,因着徐相曾是七王的太傅,暂时未对他查究,可她爹爹自己却已是唇亡齿寒,便起了“拨乱反正”的心思,以联姻为由与六殿下通亲,借此密谋大事。
这些都是当年爹爹亲口对她说的。
可惜事未竟,中道崩阻。那场浩劫之后,她最终没有见到那位名义上的夫君。
世事无常,三年后,他们却在妓院狭路相逢。
就在那样一个奇异的夜晚,那个爹爹寄托了重望的东床佳婿,揪住她的头发,强迫她观赏他狎妓的全程;
而那个从天而降救了她的大人,曾是她的旧爱,也将是这个王朝新任的阁老——尽管提拔他的恩人,是将她抄家灭族的仇人。
人间造化事,半点不由人。
夜很深的时候,尽管地上又冷又硬,桂娘和全子也实在熬不住,朦胧睡去了。
银瓶仍坐在那儿,垂着眼睛,把手伸进袖子里,摸出那卷子粉红的信笺来。她小心翼翼展开一张来,无不眷恋地又看了一回,虽是微笑着,可那眼泪却滴下来,晕湿了容郎两个字。等到天快要破晓的时候,天色渐渐浮出来青色,青里又渐渐泛了白,一道斜斜的淡金的光照到她白玉似的手上,她才终于把它们颤巍巍地递到火盆跟前,一张一张,渐渐投进了火舌里。
黎明天气潮湿,火苗渐渐熄灭了,还有一点碎纸没烧完,她也没去管。
就这样罢。
朝堂上的争斗原没有对错之分,只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她和容郎,到底不是一路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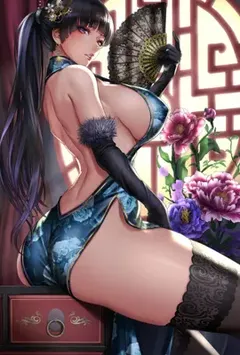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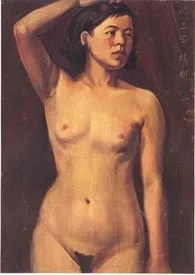




![《[ABO]藏娇》小说大结局 蜂蜜焦糖最新力作](/d/file/po18/739144.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