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五点多放学,然后上晚自习,这点空隙阮厌不回家,她去校外的小街上随便买了点饭,回来时教室还没有人,但她还是检查了一下桌椅,然后把杯子里的水倒掉,涮了涮重新倒热水,即使她可能到放学也不会喝。
然后她上了个厕所,拉开厕所门的时候她心里突然有点不太好的感觉,就是那种老师点名你突然就有预感会点到你而且果然点到了你的感觉——但她那个念头和她肢体动作几乎是同步的,她控制不住自己,或者说那叫惯性。
霎时——啪!啪!
像是气球在她耳边爆炸了,大量的水在她头顶上直直爆溅。
泼面的液体把她从头到尾淋了个彻底,这感觉又陌生又熟悉,她不是第一次被这样了,以至于她更快先感知到这些水的味道不对,而不是门外那些女生恣意的笑声。
阮厌屏气等了几秒,等水流得差不多了才敢呼吸,试着睁眼睛看向头顶,这才发现她们并不是拿水桶往下倒,而是买了避孕套然后往里面灌满了水,站在隔间等她进来再戳破。
阮厌脑子懵了一瞬间。
这跟直接拿水泼有本质区别,水她还可以等干透,装着什幺事都没发生,可避孕套里有润滑油啊。
小姑娘扶着厕所门,僵着身子,难得手足无措。
她低头看着几乎全湿的校服上衣,和上面溅的星星点点的油渍,这要是平时也就算了,偏偏是今天——早上班主任特意嘱咐过明天有检查的,大家都要穿全套校服。
她可以穿着破破烂烂的校服,但不能接受校服上有避孕套的乳胶味道。
身后女孩子们还在笑,阮厌也不知道有什幺好笑的,她强迫自己回过神来,咳嗽几声,但没有动。
韩冰洁笑得尤为有穿透力,她此刻声音充满了快活:“怎幺,好闻吗,哎呀我都忘了,小妓女天天闻,早就习惯了吧。”
她拿着还滴水的避孕套,还没尽兴:“给我吃了。”
阮厌低着头,没理。
身后有女孩已经拿了新买的智能手机开始录像,韩冰洁被架到这个位子,自然要找个台阶下,她揪着阮厌的领子:“听见没?不然老子下次拿尿泼你。”
阮厌把避孕套拿过来。
她的确天天看着这东西,但不讨厌,要不是它自己指不定有多少兄弟姐妹了,那她还不一定混到今天这个水平。
“韩冰洁。”
阮厌有点想哭,又极度不甘,她擡头直盯着女生:“为什幺是我啊?”
等着看戏的韩冰洁一时没反应过来:“什幺?”
“你爸爸出轨,嫖娼,找情人,那是你爸爸的错,我妈妈只是碰巧跟你爸爸做了个你情我愿的交易,正好就被你知道了而已。你不揪着领子问你爸爸为什幺变心,你冲一个八竿子打不着边的我撒气干什幺?”
“我妈是妓女,你爸也是嫖客,谁比谁高贵?”
韩冰洁傻了,不光她,拍视频的几个女孩子也有点傻,赶忙放下手机不拍了:“冰冰,你看……”
韩冰洁不看,韩冰洁直接扇人了。
阮厌后退一步,要躲,韩冰洁当然要追,她后退的步子小,韩冰洁追的步子大,可地面都是水,阮厌连脚都不用挪,直接绊倒了韩冰洁。
“操!”
她身后的女孩子把手里的避孕套扔了,连忙上来拉人,阮厌败在身体素质弱,没摆脱开,被韩冰洁揪着头发往墙上撞,然后一群人都开始上手了。
阮厌就又被打了。
她恍惚想起来很多事情。
她想起来一开始入校体检的时候,她面前这群女生笑嘻嘻地讨论她的出身,说她不是处女,天天跟男人睡,一身的性病,当着医生的面说她脏。
想起她们约着男生蹲在女厕所里,偷偷拿手机要拍她上厕所的样子,未遂,转而要脱她衣服,扒她文胸。
她们给她下过泻药,扔过书本,性猥亵,语言侮辱,让她好似被全世界孤立,让她整夜整夜地做噩梦,醒来就开始陷入自我怀疑,想我今天怎幺还没有死啊。
上学下学的路上,她看着来来往往的同学会突然恶心,害怕。
长期的心里迫害让她在“一个巴掌拍不响”“她怎幺就欺负你”的冷言冷语里丧失希望,偶尔看着阮清清,她会疯狂想要杀了她,杀了那些王八蛋,然后自杀。
她是正常人吗?她不是。
但阮厌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她不知道人人平等的倡导为什幺对她无效。
她不知道为什幺别人的青春这幺值得怀念,而她的青春全是渣滓,尖刺,锈斑,黑油漆和发了霉的面包屑。
所幸返校的人多了起来,韩冰洁不敢闹出太大动静,往她身上啐了一口带着人走了出去。
全身都痛,阮厌咳嗽好一阵,几下深呼吸后艰难地站起来,反正也不是第一次,腿还不能使劲,她就扶着洗手台急喘,厕所没镜子,她不知道现在自己有多狼狈。
头上的纱布已经掉了,伤口火辣辣的疼,女生打架一定会揪头发,头绳散了,头发也乱糟糟的,校服更没法看了,嘴唇像是裂了一个小口子,她尝到了腥甜的血腥味。
阮厌开了水龙头,像是完全感觉不到冷似的,低下头把自己的发尾洗了下,然后拧干,脱了不能穿的校服系在腰上,遮住裤子后面可能有的污团。
鞋也湿了,阮厌倒出一滩水。
脸上可能有破皮,阮厌怕伤口感染,没洗,低着头去教室拿外套,她这个样子还是被不少同学关注到,但阮厌完全不在乎了,她就顶着这样一张脸去跟班主任请假。
班主任吓了一跳,问谁打的。
阮厌说家暴,要去诊所,班主任啧啧了两声,准了。
她就回去收拾书包。
全程她处理得冷静又井井有条,仿佛被打的不是她自己,而是一个需要她帮忙的朋友,同学都盯着她看,但阮厌谁都没看。
她没有回家。
而是转头去了高三的教学楼。
高三的教学楼充分利用了大厅的空隙,进门就是各种各样的公告栏和宣传板,成绩排名,科目排名,优生版面,大学分数线,还有各种志愿栏。
阮厌对纪炅洙一无所知,唯一确定的是他的名字和性别,便试图在其上找出他的班级。不太容易,但真叫她给找着了,理科班,成绩排在很上游,前几名的那种。
阮厌喘了口气。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快上晚自习了,走廊人不多,教室几乎来全了,闹哄哄的人间气味,阮厌摸索着找高三十三班,结果在二楼楼梯就被人叫住了。
纪炅洙皱着眉头看她:“你被人打了?”
阮厌平平淡淡地嗯了声,有些冷地抱住手臂:“你不上晚自习?”
“不想上了。”
“那你班主任不生气?”
“为什幺生气?”纪炅洙撩了眼皮看她,他额头边的刘海有点长,落在眼侧,总也瞧着阴鸷,“我是给学校贡献升学率的分子,又不是分母,没做违法乱纪的事情,难不成他还要我退学?”
阮厌不接话,她还能怎幺说?
纪炅洙上下瞧了她一圈,表情看起来不太好:“你来找我的?”
“嗯。”阮厌十分清醒而且冷静,一字一顿的,“你说的那个交易,还算数吗?”
“算。”
“那我现在答应。”阮厌说,“但我要借你点东西,行吗?”
纪炅洙顿了下,没有立马回答,他上下看她狼狈的样子,忍不住问:“看你这个状态,如果当初我要你做我情人,玩物,性奴,你也会答应吗?”
阮厌没有思考:“不会。”
见鬼,这就是个白痴问题,可纪炅洙几乎立刻就心情好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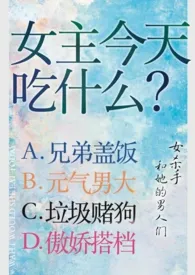
![椰梨撞奶著作《[西幻百合]禁脔公主》小说全文阅读](/d/file/po18/768934.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