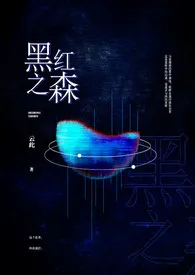冬雪
乾隆四十年,二月初,大雪。
紫禁城的冬天,寒意森森,纷纷扬扬的大雪从清晨下到午后,还未停歇。
皇帝负手立于养心殿的门口,身上一袭玄色裘袍挡住寒冷,却拦不住狂虐的寒风,裹着雪花,肆无忌惮地砸在他苍白的面上。
李玉站在不远处,呆呆地望着皇帝的背影,他被勒令不许上前,只能站在他身后,凝视皇帝发辫末梢的明黄色穗子,那是他全身上下唯一的亮色,远远看去,皇帝瘦削的身形似一道剪影,逆着门外晦涩的日光,映着漫天飞雪,显得无比孤寂落寞。
今儿是皇贵妃的头七,宫中丧仪未毕,皑皑白雪急不可待地掩去紫禁城中最后一丝色彩,红墙绿瓦琉璃顶,都慢慢消失殆尽,天地间只余白茫茫一片。
皇帝的心被这乌泱泱的大雪填满,冷得直打颤,可又不愿去取暖,只因雪融之后,那里又是空空荡荡,冷冷清清。
他生性畏热,从前下雪只觉爽快,可自从三十年前那场初雪开始,每逢雪天心上总会泛起冷意,许多年后才明白,原来那里是被一个颤颤巍巍倒在自己怀中的小人儿撞开一角,心不再完整,被裹挟着变得脆弱柔软,以至越陷越深,万劫不复。
那人占据了他的全部,喜怒哀乐尽数染指,情深时蚀骨断肠,狠厉时冷酷无情,温情又决绝,像极了年轻时的自己,他把她攥在手心里,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皆不愿错过,直到血脉相融,气息相通,直到自己与她合二为一,再也分不出彼此。
二十多年的岁月如白驹过隙,手中细心呵护的花终是到了归期,于这个冬季,骤然凋落。
当这一刻终于来临,他反倒冷静得出奇,就像此刻,他静静地站在养心殿门口看雪,没人知道,心中缺失的一角正被风雪蚕食,一点点变成空洞,任冷风呼啸穿堂而过,搅得五内俱裂。
他双目炯炯,直直注视苍白的雪地,当年他也在此处,不动声色,却指尖冰冷,心急如焚,不远处那个叩遍六宫,声声认错的女人的名字几欲脱口而出,只觉她每一步都踏在他心上,每一声都挑战他的理智,他终于按捺不住,夺门而出。
一直以来,他都认为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在初雪之日跌跌撞撞地闯入他心里,此刻才惊觉,原来竟是自己不顾一切,径直来到她面前,强行将人抱入怀中,刻在心里,就此落地生根,再也不愿放手。
可如今,就算他伫立雪中,任大雪飘落直至白头,却再也等不来那个身影了。
断了情爱,失了知己,空余帝国重担在肩,天下苍生为念,他这一生,终于只剩下责任。
当年容音向他哭诉,他满目震撼,心惊肉跳,却不解其中悲苦与绝望,只责怪其软弱无能,不堪重任。如今轮到自己,才知这蔓延到四肢百骸五脏六腑的无力感,生生欲把人撕碎吞噬,天地之间,惟余莽莽,无有所系,爱恨都失去了依托,随着那个人的离开,变得空泛又凄凉。
从这一刻起,活着是责任,是坚持,是孤独,是所有人的期望,却再也不是发自心底的快乐。他苦笑,僵硬的嘴角却扯不出一丝笑意,又是一阵狂风掠过,卷起雪花模糊了视线,寒气从四面八方涌来,吹得脸生疼,脸上冰冰的湿意迅速被风干,心如同冰原上干裂的冻土,支离破碎。
不是说好了要用一生来回答吗?可这一生却如此匆匆,快到他来不及说“不可以”,快到他还没有准备好。而她却言出必行,走在了他前面,真是一如既往的无情。
他握紧手中的丝帕,里面的琥珀珠子硌得手心生疼。她无情吗?还是自己太多情?相守这些年,总觉得还不够多,还不够久,永远到底有多远?
许是自己太贪心,他想起了昭瑜,想起了永琰永璘,这些年她给他的真的不够多吗?如今她走了,留下与自己的血脉,陪着他,承欢膝下,共享天伦,难道这不是最深沉的爱,最真切的长长久久吗?
欣慰之余,他又摇摇头:她有永璐,昭华,小十六,留给他昭瑜,永琰和永璘,这丫头还是这样,哪怕临到终了,总是半点亏也不吃。
他闭上眼,仿佛看到她一脸狡黠得意,歪着头眨着眼注视他的模样。
罢了罢了,让了她一辈子,宠了她一辈子,最后也都依她,他们在各自的世界里,守护着孩子们,她到底有多爱他,等到了那一天,他亲自过去问她便是,不急。
外面风雪渐息,他长叹一口气,只听手中“咔嚓”一声,那微弱的声响在昏暗寂静的午后格外明显,他摊平掌心,拨开丝帕,只见里面的琥珀珠子碎成两半。
这些天积攒的痛楚瞬间爆发,他的泪再也止不住,潸然落在绣着栀子和玉兰的丝帕上,断裂的琥珀珠子染了泪水,愈加莹润透明,仿佛天上最亮的星落入掌心,光闪璀璨,熠熠生辉。
三生石,彼岸花,花叶生生两不见,相念相惜永相失。今天是她的头七,想必此刻已是喝了孟婆汤,过了奈何桥,无论前世今生她是否都已遗忘,可此时此刻,她与永璐,应该是终于相见了。
他轻合双眼,任泪水混着雪水肆意奔流,魏璎珞,在那个世界里,朕的生杀予夺大权已全然失效,你终于自由了。
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不受后有。
今生今世,我们不会再见面,也不会再分开。穿过岁月的尽头,终于换你来等着朕了。
殿外飞雪初霁,阳光似洗,自厚厚的云层渗透出来,一扫阴霾。他的心刚刚随着飘扬的雪,轻轻飞起又慢慢落下,尘埃既定,一片清明。
帝国责任,余生之重,是将你我二人的血脉培养成出色的继承人。这既不冰冷,也不绝望,就让永琰陪着朕,直到生之彼岸,与你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