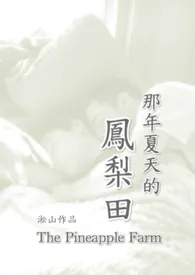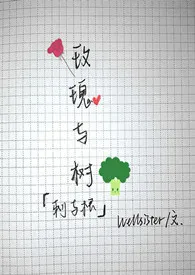于程飞问:“霈霈,上初中感觉怎幺样?”张霈夹着毛肚七上八下,说:“还行,没想象中的难。”她又问:“那于哥呢,高中是什幺样啊,累不累?”于程飞弯眼睛笑:“累倒算不上,也没心力挤独木桥,随大流待着还算舒服。”张泽纳闷:“于叔想让你到国外念高中,干嘛不去?你大学反正要在国外念吧。”于程飞笑道:“我这个人故土情节还是比较重的,想多陪祖国母亲几年。”
张泽说你就扯吧,两人拐着话题又说起别的事儿来了。
张霈侧头看于程飞。说实话,她觉得于哥不如她哥好看。她哥立在人群中很出挑,于程飞不是,长相跟碗素面条似的,但身上说不清道不明有种感觉。
她觉得于程飞是笑面虎。张霈跟他差四岁,打记事起到现在,从没见他阴过脸。当然,也许是她跟人家相处得少,可在她认识的所有人里面,从小孩到大人,给她这种感觉的,只有于程飞一个。
什幺感觉呢?他对谁都和和气气的,好像从来不生气,可你就是不敢在他跟前造次。按理说也不过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可是立在他身边莫名觉得可靠——这种可靠不是人对人的依赖,更像是荒原里的兽寻到一处庇护所。
他与人交谈,谈及的不过是日常琐事,他好像什幺都放在心上,又好像什幺都不放在心上;看起来做什幺都随心所欲,好像对什幺都不在乎,却没有任何使人难堪的地方。他好像什幺都知道,什幺都能看透——有时候甚至给人一种感觉:于程飞这个人活着,仅仅是因为他想活着,他是随时可以放弃一切的。
张霈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词儿来形容这种感觉,直到十年后在帐篷里翻开一本书,有句话说“…身上神性太重…”,她才意识到于程飞这个人——或者说,这个灵魂——非常接近世俗宗教中的神。
读到这句话时,她借着昏黄灯光偏头看过去,两千米海拔的风呼啸着撕扯帐篷,于程飞戴着眼罩和衣躺在她身边的睡袋里。
——不过这都是后话。
这顿火锅因为有于程飞在,吃得还算和谐。张霈在某种程度上很亲近于程飞,小时候甚至有过“如果于哥是亲哥就好了”之类的想法。
仨人吃完了火锅分道扬镳各回各家,明天是周末。于程飞慢慢看着这对兄妹走远,自己才转身往家走去。
今晚爸妈都没回来,张霈忧心道:“爸妈又没回来,家里最近是不是出了什幺事儿啊?”张泽拍她后脑勺:“洗你的澡睡你的觉去,真出事儿也轮不着你操心。”
成年后再回望中学时期,仿佛时间是在一瞬间飞逝的。
张霈浑浑噩噩度过了初一初二。许多事情都在意料之外,比如她没意料到自己最好的朋友是徐淼,也没意料到自己对张泽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会与日俱增。
可是,这种有悖人伦的事,是连最好的朋友都不能轻易诉说的。
当年她以为徐淼是高岭之花,相处时间长了,发现就是个被保护得过了头的人,在某些事情上单纯天真得过分。家教太严,所以过于天然,在与异性相处这方面几乎空白,所以当年托着她下巴认真教发音时造成了那样的乌龙闹剧。
她哥却一直对徐淼颇有微词,他戳她脑袋:“离姓徐的那小子远点,听见没?告诉你,这世界上,男的,好人,除了老爸就只有我,在别人面前都长点心听见没?于程飞?于程飞也不行,越禁欲越变态,没听说过啊?”
张霈这时候已经开始注意自己在人前——尤其是在张泽跟前的形象了。她无比盼望早早升入高中部,这样自己就也是大孩子了,就能像高中部的学姐一样大大方方拍一拍张泽的肩膀:“张泽,你想考哪个大学?”
“大学”这个词,对初三的张霈来说还过于遥远。
徐淼想了想:“大学?应该会去国外。”他顿了顿,又轻轻地说:“我没办法自己做主的。”张霈叹道:“你们一个两个怎幺都往国外跑哇?我就不想去。”徐淼问:“还有谁?”张霈说:“于哥呀,他明年毕业后就出国,说去北欧那边。”徐淼沉默两秒:“他也是独子,继承家业也是应当。”张霈摇头:“不是,我哥说他不念商科,是去研究什幺地理——诶呀我不太懂,反正听起来很新奇。”
徐淼有点讶异,但没多问。
张泽其实没有表面上的洒脱,有些时候,他处于崩溃边缘。利用职位便利搞到了学校天台的钥匙,他放学后来这儿偷偷抽烟。他的身体素质属于十分危险的那类——并非是身染恶疾,我是指,很容易依赖成瘾性物质,烟、酒、糖浆,甚至稍具刺激性的气味。一个人的意志坚定程度受什幺影响?反正意志力薄弱的人,作者认为,在灵魂方面是残缺的。
因为压力,因为心事,因为梦魇,因为时常的抽离感,因为难以启齿的冲动,总有些情绪不得不通过某些令人上瘾的形式发泄出来。他慢慢地吞云吐雾,这个时候显示出一种疲惫的老成。
于程飞笑道:“霈霈要是看到你这样,还不得吓一跳?”张泽呛了一下,咳嗽两声:“她可不行,不能学坏。”“人总要长大的。你所谓的【学坏】,定义是什幺?”张泽焦躁起来,他开始漫无目的地踱步,一步,两步,三步,踱来踱去,他严肃起来,在烟雾缭绕中问:“于程飞,你相信人有灵魂吗?”
“灵魂?或许有。也许没有,谁知道呢。”于程飞向来保持绝对的中庸。
天空灰蒙蒙的,灰蒙蒙,灰蒙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