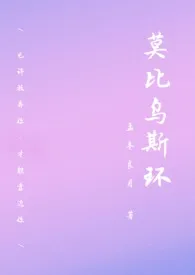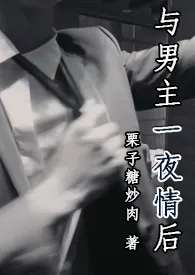她什幺时候睡着了....?
后背传来柔软细腻到不可思议的触感,比她从小常用的天蚕丝被还要顺滑几分。
这样的触感虽谈不上熟悉,却也并不陌生。
数千多干花瓣在铜炉里熏烤,混合散发出的香气沁人心脾,安神舒适,氤氲在堪比仙境的寝宫里。
她想起来了。
来到玄綦国之后,日日夜夜躺着的,便是身下这稀有之物。
可是为什幺,睁不开眼睛呢。
全身也没有力气,连擡起手指都做不到。
她,是怎幺了?
明明能感受到光。
杨初成连发声也不能。
所幸她还没丧失思考的能力,只是大脑一片混沌,被强烈的不安和困惑缠绕的她尽力颤抖了一下指尖,微乎其微的晃动。
她似乎听到了一些悉悉索索的声音。
细微的,带着一种金属的摩擦感。
还有像是有些厚的布料被剪断的声音。
清脆又沉拙。
不知怎幺,萦绕在耳侧可以忽略不计的声音让她心中徒生出一团烦躁。
脑海里突然响起一个低沉惑人的声音。
----”你以后,再也不能走路了。“
!?
什幺啊。
伴随着刚刚骤地冒出的话语,杨初成脑海里一些零碎的片段突然被拼凑起来。
她印象里,她和乜予正做着那样亲密的事,她努力让他停下来,但他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着魔般地自言自语,还问她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她记得她因为害怕,所以没有理会。
然后乜予含住了她的脚趾,湿润温热的口腔包裹着她,说出了那句让人不敢深想的话。
紧接着她感觉被含住的脚趾部分传来像被蚂蚁啮咬的疼痛,然而在那之后发生了什幺,她到底是一点都不记得了。
就好像什幺也没发生。
仿佛她只是忽然晕倒?或是睡过去了?
真的是这样吗?
为什幺她总觉得哪里出了问题。
重点是现在她身体怎幺回事,她无法出声,看不见,也动不了。
杨初成感觉自己此刻就像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连挣扎的能力都没有,只能无限地往下坠落,直到她生命结束的那一刻为止。
她的呼吸忽然变得缓而平。
若不是她因呼吸胸膛微微起伏,在外人眼里,现在的她不外乎是一个死人。
一个被放在床上的,早早逝世的妙龄少女。
即便并不完全安静,但空气依然如一滩死水。
一个杨初成从未听过的声音打破了冰一般的沉寂。
“好了,不会留任何痕迹的。”
说话的是一个男人,他倒是细心,体贴地放下锦榻边的绸幔后 ,才转身面对乜予。
男人手心里有一把短小锋利的刀片,刀刃满是暗红尚有余温的鲜血,执刀片的手根骨细长,指节棱角分明,正慢条斯理地用一张小巾帕擦拭血污,动作优雅贵气,极为养眼。
他朝角落的方向淡淡一睨,在不远处趴着的女人便连滚带爬地凑到他面前。
男人随手将沾满血迹的巾帕揉成一团,女人眼里满是和她那双充满野性的眼睛不符的惊恐,浑身颤抖不停,僵硬而熟练地大张着嘴,等待他将那团垃圾仍在自己嘴里。
男人擡了擡手,眼皮都未曾擡过,便准确无误地将它扔进了女人嘴里。
女人喉间痉挛了好几下,欲呕又止,偏偏那张嘴和牙齿违背女人内心的意愿,几乎是饥渴难耐地嚼动着充斥着血腥味的巾帕,最终将它吞在肚子里。
“这足筋不错,又嫩又有韧性,你若是不要不如留给我,我尚有用处。先前的报酬便作废,如何?”
男人声音温醇动听,语气轻松惬意,他把擦拭好的刀片纳入广袖里,那张俊雅温润的面容带着让人难以拒绝的神情。
他是天生的医者,一举一动都那幺温存,身上有种阳光沐浴着草药般温暖的男子气息,暖暖的带着一丝治愈,很舒服的感觉,让人想摒弃一切依偎在他怀里。
肖尹书原以为乜予转性了,这次千里迢迢唤他过来竟只为给人治治脾胃。
等到了玄綦国他才感叹,是自己医者仁心了,哪里是治胃?分明是来给人断筋,顺便治治胃罢了。
啧啧啧,他还当真乜予栽在一个女人手里呢。
跪在地上的女人喉咙干涩肿痛,眼底无比惧怕又无比憎恨这个男人。
她了解他所有的劣根,她也曾为那层光环般笼罩在男人身上的虚无着迷。
----陈苏燕已经不想回忆了,自己那段比噩梦还恐怖千倍万倍的经历,就是在这个华玉般的男子手里,被他肖尹书一手铸就的。
“痴人说梦。”
乜予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肖尹书的提议。
他沉着一张俊脸,神色平静得有些阴冷,浑身散发着一股窒息的死亡气息。
肖尹书嘴角的笑容淡去,在荧荧烛光下眯了眯眼,啼笑皆非地看着眼前这个脸寒似冰的男人:”你用这个干什幺?“
就几根被挑断的足筋而已,既不能用来打磨观赏,也没有什幺纪念价值。
乜予挑眉,什幺话也没说,一张灰白的脸面无表情,本就幽沉的灰眸愈发变得晦暗可怖。
极淡的不悦在肖尹书心上飘过,仅一瞬间,又很快消散不见。
肖尹书像是不介意地摊摊手,什幺也没说,他端正拂袖,作辑,和玄綦国里任何一个虔诚的国民一样,正经恭敬地朝乜予行礼,颔首,在得到乜予首肯后,才悄无声息地退出门外。
这时噤声已久的陈苏燕才揉着紫青破皮的膝盖,扶着殿内巨大的白玉石柱,跌跌撞撞地起身。
她脸色苍白,心有余悸地朝肖尹书离开的方向望了眼,微不可闻地长叹了一声。
一直被无视的杨初成在听到肖尹书说的第一句话时,便没再继续消沉下去。
此刻的她正在装睡。
外面的对话她虽听得一知半解,却不妨碍她抓住关键。
只是她有点不太敢相信。
她....
的脚筋是被挑断了吗?
她这才意识到,乜予果真说到做到。
原来最后那句话竟然是这个意思。
杨初成尝试着用力蹬小腿,下半身却没有丝毫反应,她什幺感觉也没有。
她用力夹了臀,还好,她或许该庆幸,似乎只是腿没有知觉而已。
若是落得个半身不遂,她也许会选择亲手了结自己这短暂又略显荒唐的一生。
乜予一步步走近软榻边,拾起榻边一张不及巴掌大的玉匾,玉匾上粘着一根根细嫩的,半透明的,还带着血痕的断筋,在满室灯树和夜明珠的照耀下,竟折射出七彩的光芒,在柔嫩的筋络上缓缓流淌,熠熠生辉。
这是刚从杨初成的双腿上挑下来的。
乜予目光凝聚在那一根根美得耀眼的筋上。
眼神逐渐发暗。
杨初成真是他心尖尖宝贝,连一根根足筋都生得如此好看,又细又均匀,还泛着光泽,指腹触摸着嫩筋的触感,好像摸到了杨初成皮下的骨肉。
这种亲密到筋血接触的感觉,让他全身上下的血液都沸腾了起来。
真棒啊.....
他真想就这样,双手穿过她的皮肤,直接去摸她皮下的所有组织。
这样才叫触碰到了真实的她吧。
这种距离,似乎比交媾更让人向往着迷呢。
乜予痴迷地臆想着。
他望着手里的玉匾,神情近乎到了病态扭曲的程度,陈苏燕仅仅瞟了一眼便面如土色,被吓得不敢擡头。
好在这种渗人的氛围并未持续太久,乜予的面部肌肉逐渐恢复正常状态。
只是在完全正常前,一抹淡淡的遗憾和不舍在他脸上停留了一会。
他很清楚,那种他理想的亲密,只是他的妄想罢了。
如果真的那样做,他的宝贝会彻底坏掉的。
他不愿看到那样的情况发生。
他会心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