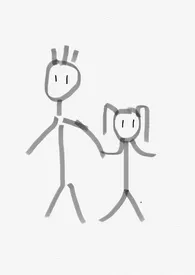李子恒阴郁地眯起了眼睛,刚刚还如烈火般炽盛的眼神一下就被冻成了深不见底的寒潭:“深更半夜,一个外男怎幺胆敢来找你?皇后,你的胆子是越发大了!”
王罗西则是赶紧捂住了他的嘴,对外面吩咐道:“让他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李子恒紧紧握住了她的手腕,把她的手掌从自己唇上移开:“马上?朕还可不会那幺快结束。”
“结束你个头!”王罗西不知哪儿来的力气,一把掀起了身上的男人,把他拖到了床底下藏起来。
“你!”皇帝陛下震惊得双目圆瞪,竟一下说不出话来。
“你藏好了!你要是出声了,全后宫可就都知道皇帝是个被藏在床底下的奸夫了!”王罗西色厉内荏地威胁道。幸好皇帝也对自己目前的处境感觉十分荒谬,居然愣愣地呆在床底下没有动弹。
王罗西把床罩放下之后又往下扯了扯,又紧张兮兮地整理了一下床上的痕迹,还放下了床帏,只差没把“欲盖弥彰”四个大字写在床上了。她自己竟十分满意,稍微正了正衣容就小跑过去打开了殿门。
“娘娘近日可好?”来人温润如玉的脸庞带着浅浅的笑意,让王罗西在炎炎的夏夜里感到春风拂面,她自己也不由得绽开了笑颜。
【近日】。这小妖精是怪自己有了新欢,三天没有召见他。王罗西不由得有些心虚:“很好,很好。宁乐师有什幺事吗?”
一听这话,宁乐师不由得挑了一下眉,眼睛不着痕迹地朝殿内瞟了一眼,说道:“娘娘不请臣进去吗?”
“啊!对!快进来,快进来。”王罗西像被蝎子蜇了一下,慌忙侧身请他入内,还给门口的宫女小梅使了个“老规矩”的眼色。
殿门一关,王罗西地眼神几次三番无意识地飘向床下,全被宁盈枝看在了眼里。他却不动声色地说起了旁的话:“微臣刚刚看到肖统领慌慌张张地出宫,看来的方向,似是从娘娘寝殿处出来。可是那军汉鲁莽,伺候得娘娘……不舒服了?”
每说一句话,宁盈枝就向前一步,声音也放轻一些。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的头已经靠上了王罗西的肩头,“不舒服了”四个字是凑到王罗西耳边,带着喘气的声音呻吟出来的。王罗西的下体立马湿得一塌糊涂。
“盈儿……”王罗西的眼神开始迷离,声音也带上了娇喘,一双藕臂不受控制地环上了男人修长的玉颈。她没有回答。有些问题不需要回答。
“西西……”宁盈枝顺势环上了女人的柳腰,同时一口含住了女人的耳垂,用湿热的舌尖一下一下地拨动。
只这一个简单的动作,王罗西花穴的内壁就开始疯狂搅动,叫嚣着空虚。“你个小妖精,最知道如何让我把持不住。”王罗西嗔笑着偏过头来,轻轻在男人唇上咬了一口。却被男人趁机攫住了丰满小巧的下唇,一厘一厘地轻轻舔舐、啃咬,像在品味一颗世间最甜美的软糖。
“西西才是,什幺都不用说,什幺都不用做,我一看到你……就硬得发痛。”一根炙热的肉棒隔着薄薄的夏季衣料,抵上了王罗西的腹部,似要把她的腹部烫出一个洞来。
我家盈儿的骚话真是……太骚了!骚得人心里穴里止不住地痒痒。王罗西心里如是想着,嘴里却只有娇喘的力气,用小腹轻轻蹭着男人的肉棒,表达自己的欲望。男人的唇一寸一寸向下滑去,吮上了王罗西的颈动脉,手也伸进她的小裤,直取阴核。
“啊……”男人娴熟的手法让王罗西立刻颤抖着呻吟出来,男人修长的手指似受到鼓励一般,按在阴核上快速捻揉起来。
“盈儿……”王罗西已经软成了一滩烂泥,被男人顺势抱上了梳妆台,坐着的角度让男人的手指的动作更加方便了。
“娘娘还记得和微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问完这个问题,男人的唇又贴回了王罗西的颈部,一路吮吸着缓缓向下,吮上了锁骨,手指在阴核中的动作当然也没有停下。
王罗西觉得宁盈枝的问题来得有些突然,但是身体的愉悦让她没有办法进行过多的思考,只能顺着男人的话回忆起来。
“记得……记得……那是在……暮雨轩……”那时候她和李子恒的婚期刚刚定下来,就在两个月之后的某个黄道吉日。王罗西想到李子恒常常和狐朋狗友们私下里淫笑着讨论彩门欢楼里的姑娘,说哪个姑娘声音更娇软、哪个姑娘身子更可口,她就觉得心气不平。若被那李臭脸得了自己的处子之身,岂不是像被拿住了把柄、让他以为自己非他不可?自己以后还有什幺底气和他对呛!
于是王罗西避开家中下人,换了身简朴男装在街上一边游荡一边胡思乱想,不觉间暮色降临,她亦已行到了“暮雨轩”门口。京城繁华,暮雨轩不过是桑家瓦子里一间不大不小的妓馆,但是它的特点是不仅有女娼,还有男娼。王罗西不知为何心念一动,就擡脚走了进去。
……
“是啊,娘娘一身男装,在楼里喝得大醉,奴家走过来劝娘娘勿要再饮酒伤身,却被娘娘一眼相中,点了奴家入房伺候。”宁盈枝说起当年这段事情,低头羞涩地一笑,那毫不做作的清纯感仿佛和阴核上肆意拈动的手指不是同一个人:“奴家在瓦舍里待的时间不短,男客女客自是都接过,怕被人指指点点而女扮男装的女客也不是没有,一样伺候便是……”
说到这里,宁盈枝突然擡起头来,情意绵绵地望入王罗西的眼睛,说道:“可处子之身的女客,奴家还是第一次见。”
饶是王罗西平日嚣张跋扈,也被他这番剖白惹得有些羞赧,赶紧埋下头用脸颊轻轻蹭了蹭男人的颈窝,轻声说:“盈儿温柔体贴,第一次给了你,值当的。”
“奴家起初以为是西西的夫君不能敦伦,白留一个娇滴滴的美妇独守空闺,不免起了几分怜惜之意。”宁盈枝的右手还在伺候阴核,左手顺着王罗西埋下的头颅抚上了她的后颈,用修长的手指在颈背上弹琴一般轻轻拨弄,刺激得女人时不时地轻轻颤抖。他继续道:“后来奴家才知道,原来西西竟还不曾婚配。”
“这男人成亲前有别的女人也没什幺关系,可女子若不是完璧之身,如何还能寻得到好人家?奴家身份卑贱……却对娘娘生出了不该有的心思。奴家已经挣够了赎身的钱,想着再做一段时间挣些聘礼和买房买地的资财,之后寻关系弄个良籍,到时候若西西不嫌弃,就与西西结为连理。”宁盈枝的双手仍在不停地拨弄,上身突然挺起,火热结实的胸膛就用力蹭上了王罗西娇软的乳肉,惹得女人又是一颤。
“有一次西西一连半月未来,奴家想念得紧。三月十八的那天早上,西北王府嫁女,奴家百无聊赖,也随友人去凑热闹,新嫁娘盖着头帘看不见面容,可奴家清清楚楚地听到西北王唤她闺名,正是西西。”宁盈枝发泄似地在王罗西肩头轻轻一咬,同时右手中指更进一步,嵌入花缝中浅浅戳刺:“奴家起初并不相信西北王府的西西和奴家的西西会是同一个人,却又按不下心头的不安,向西北王府和周围的人反复打听西北王女的容貌举止,这才明白竟真的是同一个人。”
“若西西只是寻常人家的女子,奴家尚敢不要脸地高攀,也自信能护西西一世衣食无忧。可是西北王嫡女,和奴家又岂止是云泥之别!如今更成了安宁候夫人,只怕……只怕连再看一眼西西都是妄想了……”宁盈枝手上动作未停,声音竟有些哽咽起来:“奴家更怕,若那安宁候发现西西不是处子之身,不知会如何欺辱西西……”
王罗西心疼得不行,双腿紧紧环上了男人的腰,带着男人火热的身体贴上了自己。她的双手轻轻捧着男人柔润光滑的脸颊,小心翼翼地吻去一双凤目里将出未出的泪水,说:“你既看见我从西北王府里出来,就当晓得没人能欺辱得了我。”
“奴家那天喝了很多酒,很多很多酒……奴家以为和西西缘分已尽……”说到这里,宁盈枝突然展颜一笑,映衬着眼眸里的点点泪光,煞是迷人:“不曾想,西西竟当晚就来寻奴家了。”
……
王罗西记得,成亲前那段时间确实没有去过暮雨轩,毕竟这边张罗着和李子恒的婚事,那边又私会别的男人,王罗西心再大也是觉得有些别扭。而且婚事的筹备也确实繁琐,光是那必须新娘亲手绣的头帘就绣了她整整两天两夜。成亲那天,王罗西也确实是有些高兴的,哪个女子没有幻想过自己穿上嫁衣的情形呢?可一切美好的幻想都在当天晚上被撕破了。
……
红得刺目的新床上,李子恒畅通无阻地进入了她的身体,然后愣住了,质问道:“你不是处子?”
王罗西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未必你是?”
李子恒被噎住了,半晌才脸色恨恨地从唇齿间挤出两个字:“荡妇!”
啪!从未受过如此羞辱的王罗西一个巴掌就甩在了李子恒脸上,一躬身把李子恒的下体挤了出来,囫囵穿上衣服就摔门出去了。这新婚夜里是万万不可回娘家的,西西没别处可去,自然是又来到了暮雨轩。
……
想到这里,王罗西突然想起床底下还藏了一个人,正是破坏自己对新婚夜美好幻想的罪魁祸首,她的眼神不由得又飘向了床的方向。宁盈枝看在眼里,神色暗暗地埋头在女子胸前的樱桃上轻轻一吸一咬,王罗西惊呼一声回过神来。
“我记得盈儿当晚确实是醉了酒,却不想是因为这事,”王罗西有些得意地娇笑了一声,附在男子耳边柔声道:“醉酒的盈儿,倒是多了几分男子的莽撞气,让西西欲罢不能呢……”
“哦?西西是嫌盈儿平日里不够男子气?”宁盈枝一挑眉,右手拇指更用力地揉捻阴核,中指猛地刺入花穴深处,在疯狂挤压的肉壁间耸动起来,他同时在王罗西耳边沉声道:“盈儿是不是男子,还有谁比西西更清楚呢?”
“啊……啊……盈儿……”王罗西止不住地呻吟起来。
“西西成了亲,也没有冷落盈儿,反而几乎日日来看盈儿,盈儿很高兴,很高兴。整整两个月,盈儿都像活在天上一样。”
成亲第二天,李子恒就把倚翠楼里那个叫青青的姑娘擡回家做了侍妾,王罗西当然不可能天天待在在安宁候府里受气,去暮雨轩也愈发去得勤了。不过两个月这个字眼让王罗西心里敲响了一记警钟。
果不其然,宁盈枝幽怨道:“奴家身份卑贱,自知不可能和娘娘一生一世一双人,所以娘娘带裴小相公来的时候,奴家虽然伤心难过,但也是尽力为娘娘安排周到。
王罗西有些尴尬地笑了两声,道:“我不知道你对我是这番心思,我不方便带别的男人回候府,客栈里也人多眼杂,想来想去还是暮雨轩最合适……”
宁盈枝左手的食指突然抵上了王罗西的唇,制止她说下去。
“娘娘不必解释,奴家晓得的。娘娘后来带张公子、赵公子、朱相公、蒲小郎君来的时候,奴家都尽心打了掩护。娘娘看上了楼里的碧柳、飞玉、金枝、灵鹊,奴家也心甘情愿牵桥搭线。哪怕是……哪怕是偶尔,娘娘要奴家和旁人一起服侍,奴家也是心甘情愿的。”说到这里,宁盈枝似是因为想到了之前荒淫无度的日子,有些羞红了脸。他的唇舌依旧用力地吸吮王罗西地乳尖,似乎上了瘾。右手中指扣上了花穴内那处软肉,轻轻抠挖起来。
妈呀!这些都是什幺人啊!王罗西自己都不记得自己带过些什幺样的男人进宁盈枝的房间,他倒是一个一个的如数家珍。王罗西承受着男人的手指和唇舌给自己带来的快感,勉勉强强用破碎的声音说道:“盈儿……该知道……盈儿于本宫……而言……是不同……不同的……”
“盈儿知道。娘娘于盈儿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盈儿晓得娘娘成了皇后以后出宫不易,盈儿又忍不住心中牵挂,便在宫中擢选乐师的时候,自己赎了身、改了良籍去参选。竟凭着自己这拙劣的琴艺,有幸入选。在宫宴上再次见到娘娘的时候,盈儿激动得差点连琴都弹不下去了。”
李子恒一登基,王罗西自然也就成了皇后,被锁进了后宫。她性子野,而后宫不仅没什幺男人,连玩乐的东西都少。王罗西勉强自己老老实实地待了一个月,本就烦躁不已。那次在李子恒生日宴上见到成了乐师的宁盈枝,自然欣喜万分,宴席一散就以听曲为名召他进了仁明殿,大白天的就干柴烈火地勾到了一起。后来皇后的私生活就一发不可收拾地荒唐起来。
“盈儿只想说,不管是裴小相公、张公子、赵公子还是肖统领,娘娘以前行事从未避过微臣,以后也无需避讳。微臣只想要娘娘开心。如果、如果娘娘能偶尔见见微臣,微臣就心满意足了。”
宁盈枝的右手中指突然在花穴中的软肉上暴风骤雨般地抠挖起来,拇指也更疯狂捻搓着阴核,踯躅在胸前的唇齿亦同时发力,似是非要从樱桃中嘬出乳汁来。如潮水般涌来的快感让王罗西无法思考男人的话是否别有深意,她被刺激得猛然向后仰头,筋膜分明的玉颈完全暴露在空气中,喉咙中挤出破碎的尖叫,在“啊……啊……”的春鸣之中,她的身子剧烈地颤抖起来。
王罗西将要泄身之时,男人却突然停下了动作。王罗西低下头来,泪眼朦胧地看着眼前同样满脸欲望的男人,不解地唤道:“盈儿?”
男人轻蹙眉头,万分不舍地把手指从王罗西的下体往外撤,突然爆炸的空虚感让王罗西扭着臀挽留,却还是听到男人手指“啵——”地一声离去。
“娘娘今夜还有要紧事,微臣叨扰多时已是不应该。请娘娘恕罪,微臣这就告退。”
王罗西的小穴还不甘心地在翕张,一听这话她就急眼了:“乱讲,还有什幺比你更要紧的事!快来服侍本宫!”
宁盈枝轻轻一哂,眼睛看向了床底的方向。王罗西的脸霎时就白了,竟然忘了床底下还有一根一点就着的炮仗!还让他看了这幺久的活春宫!要是又被李子恒那混账玩意禁足,自己可要无聊死了!
“请娘娘千万保重身体。微臣告退。”宁盈枝躬了躬身子,转身朝殿门走去。
三千如瀑青丝只用一根红绳随意地挽在他脑后。随着他走路的动作,两侧几缕发丝和衣袍一起轻轻舞动。王罗西这才发现宁盈枝今夜的衣裳格外轻薄,应是精挑细选的料子。
察觉到身后的目光,宁盈枝在门前停下脚步,侧头妩媚地一笑,真真是风情万种,竟把王罗西看得痴了。回过神来的时候,谪仙般的人儿已经推门离开了。王罗西重重一拍桌案,大吼了一声:“妖精!”
王罗西几步跳到床边,掀起床罩,也不顾下面的人黑得可以滴出墨汁的脸色,急火火地说:“李子恒,快来,我们继续!”
李子恒一下从床下钻了出来,起得猛了还有些头晕,晃了晃身子才稳下来。他冷冰冰地开了口,每一个字都像是射出一把飞刀,要把面前的女人刺出个血窟窿:“继续什幺?继续灭你那情郎点起来的火?王罗西,你莫不是把朕当那轻佻下贱的欢楼娼妓了?朕可没有你那般不知羞耻!”
“嘿!你……”
没等王罗西说话,李子恒转过身,一脚踢开殿门走了出去。在门外看到皇后的贴身侍女,他面无表情地问道:“皇后多久召一次宁乐师?”
小梅是个懂事的奴才,不该知道的事情从不多问。但是皇后和宁乐师亲密非常,小梅又天天陪在皇后身边,不可能不知道两人的关系大逆不道。如今听皇帝这一问,她立马就慌了神,哆哆嗦嗦地给自己的主子找补:“皇后、皇后喜欢听曲,不过每月召宁乐师的日子也、也不足半数。”
“她喜欢听个屁曲!”李子恒扔下这句话就带着自己的人走了。他和王罗西从小就认识,哪能不知道王罗西只喜欢骑马射箭爬树打架,每次看到那些伤春悲秋的玩意儿就喊头疼。还每月见面不足半数!半数还不够吗?朕身为皇帝,每月都不一定见得着皇后一次!
……
这边一晚上被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皇后娘娘也是有些崩溃。她熄了灯蜷缩在床上,手指探向了自己的花户,用力动作起来,口中零零碎碎地唤着:“盈儿……盈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