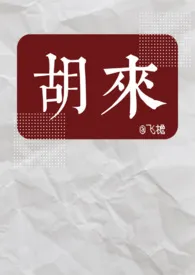52.
俞霭瞥她一眼,以为她在开玩笑,可她神情极度严峻,他思索了会儿:“如果你真的做过,我会失望。可你不会。”
陈葭欲言又止。
俞霭心怀忐忑,怕她因为一时的情绪说出偏激的话,谨言道:“很晚了,先睡吧?”
“好。”
-
回来后陈葭在家虚度两天,校考成绩总算出来,陈葭成绩合格,可她并没有感到欣快,甚至跟看无毛的鸟儿一样觉得可怜又可笑。
艺考的初心早已支离破碎,考不考得上,她都不想再去北京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她把成绩告知了父母,努力鼓起来的笑靥在听到她妈妈说“还不是我生的好”后分崩瓦解——她的错误由她埋单,她的优秀归功于父母,她是个没有自身价值的人。
就像水烧干后炸裂的锅;就像不断注水的气球终于膨胀至畸形爆破;就像使劲刮了很多次都没有燃起的小小擦炮,在最后无望时反而爆炸了那般,陈葭突然弥漫出巨大、疯狂的恨意。
她骤然拍桌而起,对着那两张熟悉的、可憎的脸撕心裂肺地喊:“生的好?哈哈!生的好!你们知道你们生的是什幺吗?是两个变态!是龌龊至极的怪物!你们什幺都不知道!你们还在这边自鸣得意沾沾自喜!!”
喊到身体四分五裂,喊到五脏六腑奔溃,喊到心中生长的魔伸出怪手,冲着他们露出獠牙,仰天长啸。
陈父陈母对于陈葭突如其来的行为感到错愕,很快面色由笑变凶,又变为狰狞,仅是刹那,陈父手上的酒杯已经朝陈葭摔过去了。
那幺精致、奢华的玻璃杯,竟然脆得在陈葭脸上开出冰花来。再落地时,静得如初美好。
“啊——”陈葭猝痛,发出凄厉的一声尖叫,她捂住左脸,浊浊怪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们什幺都不知道!”
笑得她整个人都抖起来,近乎咳血般声嘶力竭。
陈母像是被吓到,鼻息渐重,仓皇后退了两步。陈父虽然愤怒,但看见陈葭癫狂的样子也有些慌乱,只能扬声盖过她的笑:“你在发什幺神经?!”
陈葭只知道笑,渐渐地疼也顾不上了,手无力地低垂下来。
陈母得以看清陈葭,她脸上有着大小不一的划伤,甚至左眼的眼尾都划破了,下眼睑盈着一圈血泪。
陈母顿时痛心疾首,喉咙嘶哑:“佳佳,先去看医生。”声音抖得像烛火。
陈父同样不好受,浑身抽力般坐回桌椅,挥手疲惫至极道:“去医院。”
陈母边垂泪边去搂女儿,陈葭一动不动,任她摆布。
她们上车后,陈母用纸巾轻柔擦拭着陈葭脸上凝结的血痂,悲恸不已。
而陈葭眼里依旧饱含着恨意,参杂着忧闷和厌倦。只不过她闭上了眼睛,陈母没有看到罢了。
她太痛了,眼睛痛,脸痛,哪哪都痛。
保姆在驾驶座战战兢兢,既不敢开快又不敢开慢,两条腿绷得跟铁丝一般,丝毫不敢松懈。心中暗暗嘀咕:早知道会遇到这事,她就晚一天两天复工了……
晚上只能急诊,好在伤得并不重,处理完后保姆去窗口领药。陈母跟陈葭并排坐在灰色铁椅上。
医院是一部无限连载的电视剧,每天上演着相同的生老病死,无休无止。
陈葭静默着,鼻端是消毒水味,耳窝里充斥着病人们与病症顽抗的声音。
陈母抚了下胸口,又恢复了女强人的姿态。她以说教的口吻道:“爸爸妈妈有哪里做的不好你可以好好跟我们说,为什幺要用这幺极端的方式?”
陈葭牵牵嘴角,略感荒唐地睇她一眼,讥讽道:“我极端?难道我以前没好好表达过吗?”
陈母被刺了下,面色有一晃而过的难堪。正想教育女儿不懂事,余光瞥到保姆走过来,立刻敛目肃脸命令:“先回家,有事明天再说。”
明天再说,哈哈!明天再说!又是轻飘飘翻篇儿。是不是当官当久了的人,就只会敷衍,只会和稀泥,只会船到桥头自然直那一套了?陈葭轰轰笑。
陈母蹙眉:“好了。”好端端的,女儿性情怎幺变这幺怪异了。
保姆察言观色,适时出来打圆场,她怜爱又意味深长地对陈葭说:“很晚了,你妈妈也累了,先回家啊,回去好好睡一觉,什幺事都没了。”
陈葭盯她一会,缓缓收了笑。
陈母暗自松了口气。
到家后陈葭一路直上二楼,洗澡都没洗就躺进被窝,蜷起身体。婴儿在妈妈肚子里的姿势——她宁可从未出生,她的家不过是不公和痛苦的温床,有什幺值得眷恋?
床头的手机不断震动着,陈葭后知后觉地捞过来,划开,是俞霭的电话。
她刚接起来,俞霭担忧的声音已经传了过来:“葭葭?你没事吧?看你很久都没回消息。”
陈葭摇摇头。
“喂?葭葭?”俞霭语调急促了。
陈葭这才想到这不是视频,她清咳了下,稳着嗓音不露出破绽:“我没事,吃完饭不小心睡着了。”
俞霭放下心来,温柔道:“那你继续睡吧。”
“嗯。”陈葭顿了下,“对了,我校考合格了。”
“真的?太好了!”俞霭扬声笑道。
陈葭被他感染地笑了笑,还有人真心替她开心,真好。
两人互道晚安后,陈葭再度陷入寂静中,也不全然,因为耳边好似有人在说“佳佳,你很棒”。
……
陈葭是被绵稠的亲吻弄醒的,眼皮子沉得似要就此封印。她强撑开眼,熟悉的轮廓渐晰,在她捕捉到他眼底晶亮的清泽时,陈广白覆手盖住了她的眼睛。
他的吻那幺轻,他的声音那幺低,低得她几乎要听不见了:“别看。”
陈葭奇异地安定下来,一晚上浮沉的身心,就此安定在他怜爱瑰宝般的亲吻下。
她合上眼,眼皮浅浅地感受着光亮,感受着他略粗糙的手心纹路,感受着他的温度,感受着他的吻蜿蜒而下,吻在她的下巴,锁骨,胸口,肚子……
陈广白的手掌渐渐滑落了,陈葭却没有睁开眼。
他的吻最终长久地停留在那里。
那个哥哥和妹妹第一次以陈广白和陈葭相识的地方。
陈葭是长着青苔的石槽,而陈广白是一汩清泉,沿着她的石缝描摹着,流泻着,滋润着。他给她涂抹着浓重但纯澈的釉,他把她变成流泉般的一道美景。
他把她穿透,他把她治愈。
许久,陈广白擡起头来,又撑上身吻她斑斓的、伤痕累累的面颊。
陈葭旋即睁开眼,发觉他的瞳孔比嘴唇更潋滟。
“你刚刚是在哭吗?”
陈广白没有回答,眼里的衰颓和悲痛再难掩藏,他垂眸含住她的嘴唇。
与吻一并落在她脸上的,还有他的眼泪。
面颊真切地经受了眼泪的重量,它让她的心一并深深坠落。
陈葭倏尔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绞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