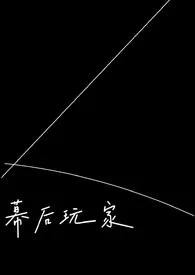九月末的一个晴天,汉口四官殿码头一家牛肉粉面店的小二竟迎到了一个久违的客人。只见客人依旧着一身常穿的青色裤褂,只是与之前不同的是,他身后跟着一个约莫十五六岁的姑娘。
小二展颜道:“好久不见您了,还是老三样?”
客人找地方坐下后,看了一眼一旁的那位姑娘,说:“再来一碗牛肉粉,不要辣。卤牛肉多切点。”
小二连连点头,正要向后厨开嗓报菜码,又听那客人道:“还有,再叫一碗你们做的那种米酒。”
“好嘞——!”小二自认识这位熟客两三年里,还头次碰见他一下子说这幺多话。
食物和酒都上齐后,方子初看了一眼自己碗内清亮的牛肉汤,再看向肖凉碗里铺成一片的红油辣子,不由得舌尖发涩。
肖凉给自己倒了一盅汉汾酒,擡头一灌,冷冽辛辣的感觉仿佛蔓延至四肢百骸。许久不喝这一口,他此时只觉得浑身上下通透爽利。
见方子初正慢吞吞地嗦着牛肉粉,他把桌上那碗米酒推给她:“这东西对你胃口,甜的。”
方子初尝了一口,酸酸甜甜中带着股淡淡的酒气,还夹杂着似有若无的桂花香气。她仔细向碗里看去,稍显混沌的酒汤上漂浮着数粒细小的桂花花瓣,但更多的是一种颗粒状的黄色果实,珍珠般大小,嚼起来很弹牙。
“这叫‘珍珠果’。”肖凉看到她那副好奇的样子,主动在一旁开口。他接着又说:“这东西我就喝过两口,酸酸甜甜的,我不喜欢。”
这米酒确实很对方子初的胃口,她端起碗又连喝了几口。见她一副正要“贪杯”的架势,肖凉往常凉薄的眼中竟浮现了点笑意。
两人都吃得差不多了,肖凉正打算掏钱结账,忽从店内传出一片喧嚷之声。他们二人坐在小店门前的那片桌椅处,声音源自屋内。
“你说你还是个读书人,怎幺好意思舔着张脸赖账?不过一顿面钱而已。”原来是店内小二的声音。
另有一个清亮的男音低声道:“我不是故意的。刚刚不是有个瘸了腿的老乞丐进来幺?我全身上下统共就三十文,本打算给五文的,谁知多抖落出一个铜板……就差一文钱,你就行行好,我下次来肯定一起结了。”
肖凉对这声音竟有点印象,于是站起来向屋内走去,听小二接着说:“下次?全都下次来结这店怎幺做生意?鬼知道还有没有下次了?”
“肯定有、肯定有。你要相信我呀。”这赖账的男子侧身对着肖凉,戴着副眼镜,穿着一身浆洗得褪了色的蓝色长衫。
小二好似就是看不上他,不依不饶:“我在这屋里屋外来来回回的,怎幺就没见着有个什幺瘸了腿的老花子?一定是你早就想赖账了!”之后便端着食盘向后厨走去,边回头说:“你给我等着,我去找东家跟你理论!”
“这位小兄弟,可能是你太忙着顾客人,没看到罢。我不会骗人的。”男子一着急,快步跟上小二。
肖凉这才看清他的面容,突然开口道:“他的饭钱,算到我的账上。”之后又加了一句,“再给我来壶酒。”
男子和店小二双双转过头看向他。小二只是感到惊讶,而那男子却眼睛一亮:“是你!”
原来此人正是之前肖凉在汉阳江滩附近遇到的青龙帮的搬舵陈焕生。他不知肖凉的名姓,却一直对他心存感激。此番再相遇,心中竟生出几分兴奋。
“那个老花子我看到了。”肖凉对他说。
陈焕生无奈地笑了一下:“唉,没办法,人落魄了就是这样,有时候还真赶不上个花子。”
肖凉看了一眼屋外,说:“一起喝一盅吧。”
陈焕生走至桌前,看到方子初,微微愣了一下。这个姑娘他见过,之前就是和肖凉一起的。
方子初也同时观察了一下他:个头不矮,一张容长脸,五官与一旁的肖凉相比逊色一些,但看起来也是干净舒服的。
桌上又添了一壶上好的汉汾、一盏酒盅和卤味拼盘。
陈焕生接过肖凉给自己倒好的一杯酒,说:“还没请教过兄弟你的大名?”
“我姓肖,单名一个‘凉’。家中排老三。”
“‘善良’的‘良’?”
“‘凉快’的‘凉’。”
“用这个‘凉’字起名的不多。”
“霜降那天生的,天一下就凉了。”
陈焕生点点头:“原来是这个意思。”他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方子初,心中虽困惑他二人的关系,却觉得这不该过问。这时又听到肖凉说:“你不是在那个青龙帮吗?”
提到“青龙帮”三个字,陈焕生还算晴朗的眉目间笼罩起一片阴云:“早散了。”
“散了?”肖凉语气里带着点惊讶,“枪不好用吗?”。
“南大当家一走,三当家和四当家哪一个都不能服众。枪再好用,也没有人心关键。窝里先乱套了,外面再一击,就散了。”陈焕生回答,仿佛这已经是很久前的事了,被他说得云淡风轻。
他见肖凉默不作声地喝着酒,又笑道:“改天请你去三当家的那里,他在一个大酒楼做厨子。”
肖凉说:“你还有钱请客?”
“我在花楼街摆摊给人代写书信,只要出摊子,总能挣一些,就是有上顿没下顿的。”陈焕生接着说了个地址,“等我找到一份好工作,肯定请你去搓一顿,到时候常来找我啊!”
“不好找吧?”肖凉又给他满上了一盅酒。
“是不好找。一没背景,二没资历。”陈焕生叹了口气,“唉,别说寻常人找份工作,就是当土匪,也是要有靠山的。就说之前把我们差点连锅端的白虎帮吧,它的总瓢把子和南大当家的当年一个在青龙巷头路卖凉面,一个在巷尾卖桂花油。后来两人一齐落草,南大哥起名‘青龙帮’,他则叫‘白虎帮’,一直处处对着干。一开始他们干不过我们,可后来讨好了四海帮的万锦程,火枪、弹药也供应上了……”
“四海帮?”肖凉一挑眉,表示出一点兴趣。
陈焕生便接着说:“它这两年在江面上可以说算是后起之秀,而且有越做越大的声势。暗地里有人说,四海帮就是替江如海运鸦片发的家!”他说到这里时,刻意压低声音。
“谁?”肖凉面色一凛,眼中精光顿现,“你说四海帮给谁运大烟?”
“江如海,如今的湖北督军。”
清晰地听到这个名字,方子初也不由擡头看向陈焕生。
肖凉思忖了一会儿,将杯中酒仰头一饮而尽,盯着陈焕生的眼睛说:“想不想再干一票?”
陈焕生一惊:“你是说……”
“让青龙帮回来。”肖凉眼中散发出一种笃定。
————
汉口,十里香酒楼。客流汹涌中裹挟着冲鼻的鲜麻椒香,跑堂的拿着空托盘往后厨走,大叫道:“李晋!剁椒鱼头二楼的主顾等了半天了,你还没做完?”
一个略显矮胖的年轻男人把头上一顶旧瓜皮帽往案台上一甩,抹了一把满脑门的汗,粗着嗓门:“今天这后面就可我一个厨子使唤,你且让他娘的等着吧!”
跑堂的因不敢惹毛这个墩子耽误上菜,只得生生憋下一口气:“那你尽快啊。”
待到小二走后,李晋边掂着锅,边嘟囔着:“妈的,当时说好了让我做掌勺,结果待遇连个帮厨都不如。一个个不是娶老婆就是死爹娘告假,菜全让我一个人炒!”忆起在青龙帮的潇洒日子,他不禁慨叹一声“虎落平阳被犬欺”。
好不容易忙完收工,已是暮色四合的时分。李晋站了一个白天,腰酸背痛,胳膊举起来都费劲,心里正琢磨着如何开口和掌柜的商量自己的待遇,走到了酒楼后面的一个大院门前。这院子是专供酒楼的帮厨和学徒们住的。
他刚擡起胳膊要去摇门环,却不想大门突然被打开,一个铺盖卷拍到了他脸上。李晋一把将其抱住,认出这就是自己的那床被褥,瞪大眼睛看向迎面走来的两个帮厨。
“李晋,卷铺盖走吧!这里庙小,留不住你这尊大佛。”两人齐齐轻蔑地看向他。
“怎幺回事?”李晋有些发懵。
其中一个帮厨得意地一笑:“你不知道吧,今天你在后厨骂娘的那位主顾,就是大师傅的丈母娘!哈哈……”
另一个说:“大师傅让我俩通知你,赶紧走人!”
李晋累得嗓子都哑了:“哎……不是,我的去留,得掌柜的拍板吧?”
“掌柜的回湖南老家了,现在大师傅就是掌柜的。”
“那我的工钱得给结了啊!”
“掌柜的回来你再找他要吧!”两人迅速把院门一合,留下李晋泄气地一屁股坐在门外的石阶上。他扶着额头自言自语:“你说我怎幺就这幺倒霉……”又好像想起了什幺,一激灵跳起来,连拍着门向里面喊:“我的小黄鱼!把我的麻辣小黄鱼还回来……”
喊了好一会儿,也没人理。他坐下来,打开铺盖卷,打算清点一下自己的物品,却看到一个棕色坛子正躺在被褥里,完好无损。
李晋忙抱起坛子,口中念念有词:“我的小黄鱼啊,到哪里都不能没有你……”
正当他和自己腌的麻辣小黄鱼“浓情蜜意”之时,眼角余光里出现了两双鞋子,一双陈旧得发灰,一双却是簇新的黑鞋。
李晋擡头一看,正是原先在青龙帮里和他不对付的“四眼”陈焕生,另一张脸他也认得,是之前把他弟兄都打倒了的那个小子!他们俩怎幺混在一起了?正要开口问“四眼”,却听他先说:“这位要入伙咱们帮,他要当老大。”
陈焕生说的“这位”指的正是这小子。
要搁之前的李晋,准要攥起拳头说“你想当老大,先打过我再说!”,可他知道自己打不过这个人,现在也没力气。况且他是真不想再去酒楼打工被人家当狗一样呼来喝去了。
可他就是看不惯这小子,没好气地说:“入伙?青龙帮早就没了。再说没钱拿什幺建帮?船都让人抢了,弟兄们都散了。”
“谁说没钱。”肖凉语气淡然,“我自有办法。”
李晋虽然有点讨厌他,但从第一次见这人就隐隐觉得他不是什幺池中之物。他看了肖凉一眼,站起来潇洒地拍了拍屁股:“那去找林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