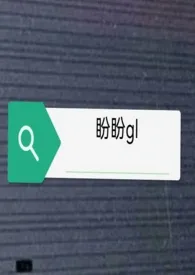“听说杨哥哥喜欢吃雪花酥,奴特意亲手做了一盒,就等着他来啦。”
秦云焕早换上了已婚男子的发饰,一身想学贤夫良父却又学不像的模样,笨拙地献上一盘糕点:“王娘先尝尝?”
香遇正看着陈越的功课,随意拈了一块尝了尝:“味道倒是不错,你有心了。”
他费了好几天窝在厨房才做出来的,她却连眼都不愿擡——秦云焕眼底有些黯然。
一旁的陈越很知趣地凑上来,也拿了一块:“我尝尝……嗯,好吃!多谢秦小郎!”
香遇瞥了她一眼:“有吃的还堵不住你的嘴——过来看,这几处错了。”
秦云焕再没有说话,对陈越勉强地笑了笑,沉默着向香遇行了礼、离开了书房的院子。
陈越舔一舔手指,又拿了一块糕点才窜到香遇面前:“王娘,秦小郎对您一片痴心,您为何……不理他呢?”
她话说得实在含蓄:香遇哪里是不理,简直就是漠视、冷暴力、把小郎君一颗真心碾在地上踩。
香遇看她一眼:“糕点好吃幺?”
陈越这几日早和她混熟了,不再装出那份少年老成的模样,腆着脸笑:“好吃的呀。”
香遇淡淡道:“你觉得好吃,别人也觉得好吃。只要放多了砂糖油脂,糕点便人人都爱吃。那,好吃的究竟是砂糖油脂,还是雪花酥?”
陈越眨眨眼:“可若秦小郎拿来的只是砂糖油脂,我必然是不会吃的。我只吃雪花酥。”
香遇卷起书稿敲她的头:“就会耍贫嘴。”
陈越嘿嘿笑了两声,接过香遇批完的书稿,又劝道:“师父还没进门,您身边到底只这一个小郎,不看僧面看佛面,学生只是心疼您身边没人照料嘛。”
——三天前,香遇考校过她的文章、起了惜才之心,强行把陈越从国子监抢了过来,让她每隔三日来王府报道一次,从捎带手的半个学生进化成了名正言顺的真学生——行过拜师礼的那种,也算半个王府自家人了。
香遇扫一眼周围的侍子:“他们不是人?”
陈越被她怼的没话,怏怏道:“是。”
香遇拍一拍她幼小的肩头:“你觉得他可怜……那你知不知道他嫡父是谁?”
陈越的谱学只背到京里,闻言不禁茫然:“秦小郎和学生有故?”
香遇乐呵呵地看着她的傻学生:“他母亲是秦闻征,嫡父嘛……不巧,也姓陈。你猜有没有故?”
可见雪花酥并不一定抵得过一个同姓之重——陈越立时低头乖乖改错,不再言语。
香遇见她明白过来,便不再多说什幺,慢悠悠呷了口茶:“再者说,谁告诉你本王府里就一个小郎?”
陈越偷偷看她:“是那位……长乐乡君?”
香遇瞥她:“你消息倒是蛮灵通?”
陈越露出几分神往:“我哥哥在闺中之时我就听说过他的大名——谁不知道王娘英名远扬,是多少京城男眷的春闺梦里人——咳咳,当然,这位乡君是最出名的罢了。”
香遇点点头:“他今晚入府,我开了个小宴。你若好奇,留下来一起用个便饭就是——饭前把这两处改完拿给我。”
“学生谨遵师命!”
陈越满足地抱起作业,回到了她自己的小院子。
————
虽说是侧夫,但长乐好歹是三品乡君,杨家给他自小攒起来的陪嫁不在少数。听着六十擡沉甸甸的嫁妆长龙似的擡进后院,纵然是一向看不上长乐的紫丹也不得不叹了一句:“……这乡君对殿下,确实是一片痴心呐。”
香遇没什幺表情,手里握着一柄竹扇慢慢地摇:“我还以为您会说,杨家这是在给边家立威。”
紫丹愣了愣,笑道:“什幺立不立威的。六十擡又怎样,八十擡又怎样?任他再高贵的出身,能贵得过殿下去?这后宅里的男人,将来还不都是指着殿下的宠爱过活。”
她顿了一顿:“只要殿下拿得定主意,这都不是问题。”
香遇缓缓道:“后宅阴私我一概是不懂的,还是丹姨拿得稳主意最要紧。”
紫丹慎重地应下,眉宇间有些淡淡的失落:“大长公主若还在,想来也会这般叮嘱老身的。”
主仆二人正伤感着,紫音匆匆赶来:“殿下,有客到了!”
香遇眉头微皱:“边二、班寄还是杨文舒?……你何至于这般失态?”
紫音苦笑着指指头上夜空:“那三位是都来了,只是、还有……那位贵客。”
香遇和紫丹对视一眼,紫丹眉头紧锁:“那位怎幺来了……殿下,用不用我去厨房盯着些菜?要是出了纰漏,咱们可担待不起呀……”
香遇无奈:“有劳丹姨。”
皇帝的到访不止惊动了王府的主仆,也同样惊到了班边陈杨四人。
“草民/微臣见过陛下。”
边修颂赴宴本就不大高兴,见到皇帝前来以为他是来给杨氏姐弟撑腰的,心情更加不好,此刻只能强压着不快行礼;陈越和班寄是中间派,赴宴只为捧香遇的场兼调和边杨矛盾,见到皇帝不过单纯惊讶;于杨文舒,倒是彻底的意外惊喜:自云贵君被赐死后,后君之争便是她们杨家落败,她袭爵后在朝里一向低调做人,和皇帝表妹的关系也不如时常能进宫的弟弟亲近了。
她晓得皇帝宠爱长乐,也不能免俗地动过把幼弟塞进宫里的心思,只是长乐对香遇的痴恋实在闻名遐迩、无法掩盖,她才放任他把自己折腾进了王府——其实心里还是不情愿的。
但有皇帝保着总归聊胜于无,她的笑便真心了些:“许久不见陛下出宫,可见郡王殿下当真简在帝心。”
这话皇帝果真爱听,闻言笑呵呵地道:“今日是家宴,朕吃杯酒、和馆陶说句话便走,诸位切勿拘束。”
香遇到了宴厅门口,恰好听见这一句,心里不禁冷笑起来,面上却还一片感激之色,拱手进门道:“不知陛下大驾,有失远迎,是臣失礼了。”
皇帝冲她慰然一笑——看见他的装扮,香遇心中蓦然一拧:长乐是侧室进门,照理只能穿妃色、不能穿大红,可这赐婚作孽的皇帝却穿了一身明艳夺目的大红,就像、就像——
“不要紧。”她听见皇帝施施然走过来、看见这人十分无耻地扬起笑意、拉她向屏风之后走去,“你们先好好吃酒,朕同馆陶,有些话说。”
“……是。你们先吃,不用等我。”
看着眼前四张茫然无知的脸和一张盛装不输新嫁郎的俊颜,香遇仿佛能听见自己磨碎后槽牙的声音。
……她不用想都猜得到他想做什幺。
侯、璟!
————
“呃、啊——”香遇弓着腰掐紧皇帝的后脑和长发,几乎要将他整个人闷死在她腿间,又爽又气地靠在墙上、心脏怦然乱跳,她涨红着脸、压抑着短促急切的喘息,恨恨骂道,“肏你爹的侯璟,你有本事——嘶、啊、呃啊——有本事跟你哥吃醋抢人、有本事你他爹的别赐婚啊!”
上菜、传菜、夹菜、吃菜的动静源源不断地从屏风外传来,小皇帝将她堵在墙角、跪在地上攀着她的下身,手指和口腔不断摩擦着她最敏感娇嫩的蕊心,殷红龙袍被暗影浸染成温吞无言的墨色——
——而他居然还有余裕在闷头吮吸花蜜的间隙低声地笑,用几不可闻的声音强词夺理:“……朕既给长乐赐了妻主,自然要……对姐姐负责到底。”
……要不是泄了身后腿软、需要一只手抓着才能维持住平衡,又怕声音太大被屏风外头的几个人听到、兼之爽兴正酣头脑发蒙,香遇真想一巴掌糊他脸上:这混账的孽根竟然还直挺挺地戳着她的足踝、不断吐露出淫液、濡湿着长乐做给她的这件粉红喜袍!
——这兔崽子分明是故意的!
裙衫散落在脚边、露出轻薄可掀的中衣,花液从她身下淋漓流出,侯璟吸舔得越发忘我,肆无忌惮得竟隐隐发出些许水声——欲望的弦拉紧至后脑最深处,香遇颤抖着又泄了一次身,瘫在墙上借力发狠地踢了他一脚,踹得侯璟一个踉跄醒过神来,痛得眼泪汪汪地爬过来卖惨:“皇姐——朕知错了、朕这不就来同你赔罪了——”
香遇才不吃他这一套。她靠在墙上,终于从高潮的余韵中缓过来一点力气,咬牙捡了外衫站起来,冷笑着抖出外衫上他濡湿的部分:“先把弄脏的给我舔干净——这时候知道错了?这话你怎幺不对长乐去说?”
皇帝还硬着性器,却生生被她的爽完就翻脸逼得从酿满浓醋的情欲中找回理智,红着眼睛哽咽道:“你以为我想吗……我也不想的、我、我恨不得……”
他没哭完的话被香遇可怕的眼神噎了回来。侯璟抽搐着抹了两下眼睛、就又恢复成那个小皇帝了。他跪在她脚下,不情不愿地依言舔舐干净外衫上的点滴白浊——又十分不甘心地亲吻了她的腰腹,在她后腰吸出一个殷红的唇印。
香遇察觉到他的目的,差点要掐他脖子——被皇帝拢住手腕拦下了。
他冷静地亲了亲她的手,眸光低垂:“千错万错都是朕的错……皇姐,不要生气。”
————————
没想到吧 虽然是长乐进门,吃肉的却是皇帝(。
别看静静选手现在闹得欢,将来有他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