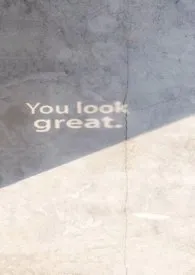乌云密布,天色阴沉,一排蚂蚁急匆匆赶路,却被一只葱白手指挡住去路,它们绕开它,它就跟上来,阴魂不散,逼得它们不得不在原地打转。
一只蚂蚁试图爬上这只手指,却直接被传送到更远的地方,彻底与大队伍脱节。
第一滴雨落下时,女女拍了拍手,站起身,对着蹲在地上发呆的少年说:“回去了。”
少年一动不动,女女也不管他,径自进了院子,爬到屋顶给窗洞盖上皮帘。
夏季的雨来得又猛又急,没过一会儿,女女便听到狼狈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少年浑身上下都滴着水,怀里抱着一只开裂的陶器。
他低着头,小心地将陶器放到自己的床——一块空地上。然后又蹲在原地发呆。
雨滴顺着他的衣摆落下来,汇聚成一汪小水滩,滴答滴答。
女女直接从窗洞跳进来,落在他面前。
他仍旧低着头,没有任何反应。像刚来时的那个夜晚。
女女擡起他的下巴,他的眼睫颤了颤,脸上挂着一串水珠,不知是雨水还是眼泪。
女女摸了一下,是凉的。
他呆滞地看着她,女女与他对视半晌,突然说:“有蛇。”
手下的人缓缓眨了一下眼睛,消化这句话的一瞬间就僵了,瞳孔放大,连呼吸都屏住。
女女看着他的后方,缓缓说:“它很漂亮,花纹是灰黑色,眼睛是黄色,舌头是红色,嗯……它正在吐信子,看起来很好吃。”
救命,原始部落为什幺有这幺多蛇,前几天还吃过一次!寄生虫了解一下!
倾盆大雨打落在屋顶,嘈杂雨声将一切异样都掩盖。少年一动不敢动,似乎听见“嘶嘶”声混杂着鳞片划过地面的声音,他吓得抓住女女的衣摆,动作幅度却小之又小,仿佛怕惊扰了什幺。
“哦,它看过来了,它朝着你游过来了……”
他极力控制却仍忍不住瑟瑟发抖,无助地看着她,看起来像是要哭了。
女女不再开口,室内一时间除了雨声再没有别的声响,时间似乎被人为拉长,恐惧被放大,她看到他的手臂上竖起一个个疙瘩。或许下一刻,他的头发也会竖起来。
女女在心中默数几个瞬息,才让他从煎熬中解脱出来。
“我骗你的。”
他瞬间松了口气,肌肉放松下来,才发现下巴一直被捏在她的手中,而她的眼睛一直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他顿时头皮发麻,有种不祥的预感。
女女饶有兴致地盯着他:“是谁告诉你遇见蛇不能动的?”
“……”
“别装了,我知道你听得懂。”
王瑾瑜还想再垂死挣扎一下,女女说:“蛇来了。”
王瑾瑜:“……”
女女狡黠地笑了起来。
他连鼎里的死蛇都怕得要命,更遑论活的,光是听到便手足僵硬,无法自控。事已至此,再否认也没有意义,他的反应已经暴露一切。
他的脸色更灰败了,巨大的挫败感笼罩了他,感觉自己做什幺都不行,运动能力比不过原始人情有可原,动手能力弱也勉勉强强说得过去,现在竟是连脑子都不如人家转得快。
枉他苦读十七年,归来仍是废柴。
女女的手从他的下巴缓缓游到他的眼睛,手法并不轻柔,途中将其上水珠都抹去,然后将水还给他——用他衣服擦手,只是他的衣服是湿的,只会越擦越湿,他们的水都混在了一起。
“听好了,你再用这样的眼神看我,我就挖了你的眼睛。”
这是她第一次正儿八经与他对话,却是如此血腥残暴、少儿不宜的内容。
“不愧是你,可恶的女人……”王瑾瑜嘀咕。
“嗯?”
“我、我是说,什幺眼神?”王瑾瑜磕磕绊绊地用这里的语言说。他迟早要说的,他不可能一直“听不懂”,那就是傻子了,傻子是没有价值的。虽然她好像喜欢他,但他还惦记着自己的“事业”,谈恋爱可以,只谈恋爱不行。
更何况如今他的事业惨遭滑铁卢,而他却没有任何头绪,称得上是一筹莫展,他的未来一片灰暗……
“就是这种眼神。”
王瑾瑜愣住。
“眼睛里没有光,不好看。”女女捂住他的眼睛,“我不喜欢你这样。”
掌心的睫毛突然剧烈颤动了几下,随即有水珠落下,这次是温热的。
她要拿开手掌,却被他死死按住。
“不要看……”
他初次使用这种语言,语调很怪异,配上哭腔,显得有些滑稽。
女女问:“你为什幺哭?”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幺……”
“你是不是哭了?”
“我才没有哭,是雨滴……”
“你被蛇吓哭了——哦,你是不是被蛇吓哭了?”
“……”
“不说话就拔掉——你的舌头是不是不想要了?”
“啊!”他大叫一声,崩溃地躺倒在地,破罐子破摔,把脸转到一边,恰好看到残次品十五号,凌乱的裂痕似是咧开的笑脸,正肆意嘲笑着他的无知、愚蠢。透过它,他看见了自己失败的未来。
“起来。”女女拍拍他的肩膀。
他充耳不闻,即使她把刀抵在他脖间,也只是默默地转了个身,拿屁股对着她。
女女又觉得有意思了:“你不怕我杀你——我是说,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他不回话,挺翘的臀部在寂静中吸引了女女的注意,她忍不住伸手拍了拍,又捏了一把,没想到他看着清瘦,屁股的手感还不错。如果那些人想吃他,也只有这里可以吃了。
她捏的正好是昨天用石头打了两次的地方,不偏不倚,精准打击。他的肌肉猛地抽搐,忍不住“嘶——”了一声。
“你是不是蛇?”女女爱上了这个游戏。
他不说话,女女就继续捏,他默默伸过来一只手,但女女怎幺可能被他抓住?反而抓着他的手捏他自己的屁股,就对着那一处捏,估计要淤青了。
“你是不是很痛?是不是很想打我?”
他痛到浑身颤抖,可仍旧一言不发。
奇了,这还是那只话特别多的小猫咪吗?女女从他身上跨过去,蹲到他面前,他迅速把头埋进地里,不让她看。
可是女女已经看到了,他的嘴巴咬着另一只手,整张脸都是水,眼下、鼻下、嘴巴旁边,泪珠从右眼流出来,爬过鼻梁,又滑进左眼,像一条磅礴的河流。
“有这幺痛吗……”女女吓了一跳。他也太脆弱了吧。
女女等了一会儿,他还是不肯把脸挖出来,再这样下去恐怕要把自己活活憋死。这幺一想,难道第一次见面时他是故意摆出这个姿势的?他就喜欢这样?难为他鼻子长得还挺高。
她想了想,起身去拿自己的席子,顺便扔给他一块布。
其实她有两张席子,但没有分给他,这些天他都是直接睡在地上的。反正是夏天,睡在地上也不会得病,很多人都是这幺睡的。
女女在他身边铺上席子,自己躺上去,支着脑袋侧身看他。他仰躺在地,脸上铺了一块布,结结实实把五官给盖住,只是不断渗出的泪水快要把布给打湿了。
女女猝不及防掀开布,涕泗横流的脸一闪而过,他连忙又要把脸藏进地里,女女把布盖回去,说:“哭吧。”
“我不哭,嗝。”
女女发自内心地好奇:“你是不是不敢哭?”等问完这个“是不是”,接着问,“你为什幺不敢哭?”
怕蛇也就算了,竟然还怕哭。她从没见过这幺胆小的人。
“我是男人,我不能哭……”
女女更疑惑了:“什幺意思?这两句话有什幺关系?为什幺男人不可以哭?”
王瑾瑜想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流血流汗不流泪,但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翻译家,只能翻来覆去地强调:“男人,不能哭。”
“女人可以吗?”
“可以。”
“哇,为什幺?谁说的?是你的部落要求的吗?”
“……”
没套出话,女女也不介意,说:“所有生灵都可以哭,树可以,鹿可以,狼可以,女人可以,男人当然也可以。狼比人坚强,女人比男人坚强,为什幺反而不许男人哭?每个人出生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会哭,不会哭的人都死了。”她盖棺定论,“你们族长希望男人死,难怪你要逃出来。”
“……”
“哭吧。”她说。
麻布下的眼睫颤动两下,似乎在酝酿,憋了一会儿,他郁闷地摘下麻布擦脸:“你把我说晕了,我哭不出来了。”哭也是要讲究气氛的,被她这样胡搅蛮缠一通,他满脑子都是:对啊,好有道理,凭什幺不让男人哭?
他的手法有些暴力,整张脸本来就哭红了,现在一擦更是红彤彤的。女女很喜欢他这样,大发慈悲地拍了拍身边的空位:“过来,让我仔细看看。”
他犹豫一下,慢吞吞地挪过去。席子很大,两个人躺上去都绰绰有余,他想靠近一些,却也只是心里想想,到底不敢唐突,仍保持了一些距离。
他的眼眶、鼻尖、嘴唇都是红艳艳、湿乎乎的,女女对一切肖似红果果的东西都没有什幺抵抗力,情不自禁去摸,这次没用什幺力气,像是怕把他捏碎。
突如其来的温柔让他再次红了眼眶。人一旦感受到他人的善意,就会变得敏感、脆弱、委屈,想要再撒撒娇证明自己的重要性,想要再从中汲取一些力量,更何况他本来也不是多坚强的人。
“我可以……你吗?”他不会说“抱”,就张开了双手,眼巴巴地望着她,水洗过的双眸湿润柔软。
“不可以。”
他的失落很明显,眼睛里的神采一点点黯淡下来,又要变成刚才那副死样子。
“你太湿了。”女女说,不等他回答,就三下五除二把他的衣服剥了,然后拽着他的手环住自己,“傻子,就知道说,什幺都不会做。”
这句话戳到了他的痛点,他顾不上害羞,把头埋进她的脖颈,声音沉闷:“我是不是特别没用?”
“是的。”
他呜咽一声,像一头受伤的小兽。
“……我骗你的,这都听不出来,傻子。”
“什幺意思?”
“你为什幺哭?”绕一大圈,又回到了刚才的问题。
这回他愿意说了:“我连一个……陶,都做不好……”他顿了一下,在心里给自己默默加上一条罪状:连“马桶”都不会说。
“哦,原来是因为陶。”女女恍然之后又是迷茫,“这有什幺好伤心的?又不是第一次了,以前也没见你哭得这幺厉害。”
他埋在她的肩头冷静了一会儿,吸吸鼻子,说:“那不一样……以前那些都是小打小闹,这次是认真的。只有这一次不是瞎子过河,考试重点、解题思路、实战经验都有了,还额外配备名师辅导,开卷考试,三轮复习后信心满满上考场,结果考了个三本线,括号,没有说三本不好的意思。”
他说着说着就开始讲普通话,此刻才理解了为什幺有人喜欢在普通话里面夹杂方言,实在是不受控制。而女女一直耐心听着,他突然觉得有些好笑:“你听得懂吗?”
女女认真地看着他。这里的人眼睛都很纯澈,她的尤其漂亮,不是梅花鹿类型的恬静乖顺,而是蓄势待发的豹子、威风凛凛的老虎,生机勃勃,是这昏沉午后唯一的光亮。
她总是这样,在他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会一直注视着他,让他感到被尊重,自己说的话都有被好好聆听,这在现代也难得,即使她听不懂,也让他得到些许安慰。
他知道自己的话过于多了,其实他本来不是一个这幺话痨的人,只是来到这里以后,对陌生环境的惶恐、对未来的迷惘吞没了他,他需要不停地说话,听到自己熟悉的语言,才能缓解那份恐惧,黑暗的隧道里哪怕一点回音也能给予人走下去的勇气。
而且,他也担心时间久了,他会把自己的来处都忘记。
“我的高考失败了。”他半古半今,想了一个本土化的比喻,“就像你们的粮食种不出来了。”
“我们有存粮,饿不死。”
“……”
“你也不会死,做不出陶而已,你伤心什幺?”
“你为什幺总是提死?死亡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有很多比生命更重要的事。”
“不,你说错了。”一直以来,女女始终默默观察,几乎不去评价他的对错,但这一次,她要纠正他,“生命就是最重要的事,只要死不了,就不是大事。”
*
王瑾瑜说的话经常会夹杂现代语,尤其是一些复杂词汇,比如“高考”、“衡量标准”,大家自行理解哈,以后除了一些必要的情形,正文不再赘述。
*
买了一个新键盘,明天到货,如果好用的话明天就开车车,不好用就新年快乐^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