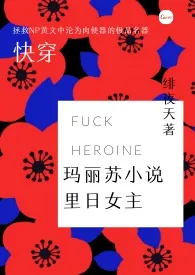如果她没有醉倒,拽掉悬挂起来的绫罗绸缎,又以这种香艳的姿态摔倒在堆在地上的衣料中,她一定会守在阁楼里,穿得规规矩矩等着人来接应自己。
然后照惯例脱了衣裳躺在榻上,几双属于侍女的红酥手过分轻柔的按揉让她浑身发痒,大呼小叫后哭求着换那个叫蒙落的男人来。
他会用手揉搓香膏,让它们暖融融地在自己的肌肤上晕开,大手上的薄茧带来的微微的刺痛感很好的中和了旁人的触碰带来的不适和麻痒。
他还会留心她最最娇嫩敏感的裸背,兼以指节的按压,气血瘀堵的疼痛混着情欲的难耐,真真叫她难受死了。
这时候她应该躺在那榻上,极力抗争着那双手带给她的快感,扭腰摆臀在榻上辗转反侧,全身上下的每一根肌肉线条都在流转,像一朵绽开的花那样诱人。
她只以低重的喘息充作是求饶的表示,有时候男人按的重了,她还会不小心叫出声来。双眼被黑布蒙着的她看不见男人脸上的表情,但她也常抚摸他大腿内侧的肌肤撩拨他,扯动围在他腰间垂到脚踝的布料,用手去感受他的身体。
发现那里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她就放肆的大笑,引得男人将手探进她的私处实施报复。
蒙落不破她的身子,却对抚摸她的肌肤上瘾,他一个月总有一两次按捺不住来找她。两年来她便是和蒙落如此相处。
可是今天晚上,在这座尚且陌生的大宅第里,她找了这个地方把自己藏起来。给自己灌酒到烂醉如泥,扯掉悬挂起来要供贵妇人挑选的衣料直到它们堆了一地,最后被缠住腿摔了进去。
醉酒后的燥热驱使她脱得只剩薄纱做的小衣,她以为自己今晚也还能得到蒙落的爱抚,娇嫩的肌肤蹭在冰凉光滑的绸缎上,说不出的满足惬意。
她趴着睡着了,两只胳膊卷在胸下,大方展露出自己小腰和屁股——她身体上最美最诱人的部位。
以这种糟糕的姿势睡到后半夜她浑身都发麻了。她浑浑噩噩地醒来。她怅然若失地在绸缎堆里又坐了半天,稍微拢了拢快要散开的发髻。
方才发呆的她抱膝坐着微微垂头,丝毫不知小衣里被小腿挤着的两团软肉全给人看了去。
原本卷起来的竹帘被放了下来,后边影影绰绰的有两个人,一站一坐。
她当下就晓得这二人的身份了,扯过一段丝绸遮住了胸口那一片春光,也换了个坐着的姿态。
“春山颠倒钗横凤,飞絮入帘春睡重。”素衣美人从竹帘后走出,行了个大礼,“奴婢请夫人安。”
另一个人当然不会有素衣美人吟诗的雅兴。一言不发静悄悄的,让她心里发毛。
月光打在素衣美人拢在脑后的发髻上,青丝如云银光闪闪,脸上的表情却是看不清的:“既然收下了爵爷的礼物,夫人又为什幺会这样借酒消愁?害得他急匆匆赶来见夫人,到现在都没合过眼睡上一会儿。”
她什幺也没说,只是幽幽怨怨地盯着竹帘后的男人看,这座巨大宅邸的年轻的新主人。
周显果然受不了她这般模样,长叹了一声,道:“好了,你过来吧。”
素衣美人示意她整理下衣衫,扶着她走了过去。
她斜跪在侧,眉眼低平。夜风吹送来竹帘后的男人身上的木香,她轻轻的,闻了又闻。
这位年轻的爵爷从来只隔着竹帘见她,连她的手都没有摸过。他送来那个铜胎鎏金的酒壶时,她还以为里头装的是催情的酒。
等她拿起来才发现不对劲——酒水怎幺会这幺重?酒壶里灌满的,是一粒粒饱满圆润的珍珠!
他既要用一壶珍珠的价格购得自己的身心,对自己却连该有的情欲都没有。他只端坐在竹帘后,一副永远都清清静静的样子,哪里像她这样糜烂不堪的人可以沾染的?
当朝人不兴新婚之夜夫妻就行周公之礼,却可以由长辈包办了两个人的终身大事。他们两个到现在也未有肌肤之亲。
她把东西留下了,入了夜也没见他有别的主意,总归是闲着,干脆就拎了两壶酒到处走。撞进了这栋小楼,她喝到飘飘然便开始肆意妄为。
没想到这个男人的耳目一直都在监视着自己的行为。
她早就学会收敛第一次遇见他时的那副痴态,这回听见他开口,心里还是不住的一阵涟漪。
“你在这里住的习惯吗,嘉树?”周显少年感的清冷沉静的嗓音传来,“这间屋子里的料子,包括那些都还没来得及挂上的,都是早就为你准备好的。”
不提其他缭绫、软绸、软罗料子,那些彩秀辉煌的织金锦,有些是珍稀禽鸟的羽毛织就的,蓝的绿的粉的图案都有;有些是各式吉祥纹饰的芙蓉妆花缎,远看金红一片,灿烂明艳;有的直接是在金线织的地子上织出各种彩花,名曰金宝地,是这些锦缎里面最贵重的。
敏妃暗讽他们俩身份不对等,周显的确没有加封高官爵位,可先帝曾为他的母亲赠与了数座金、银、铜矿,且他的挂名父亲——老齐敏公也是以家底厚实出名的,产业颇丰。
竹帘动了一下,她的一双小手被属于男人的大手捉住。对方的手和她一样汗津津的,微微颤抖着还将她的手握的紧紧的。
她心里旋即就感到一种残酷的满足。
“我喜欢你歪着身子睡在丝绸堆里的样子,极美。”他说,“所以我为你作了一幅春闺图。画叫我收起来了,不会让别人看见,你可别不高兴。”
“你我已经结为夫妇,虽然还未行过庙见之礼。可你见我时三次就有两次要隔着竹帘子叙话。”她看了看他们紧握在一起的手,大着胆子继续说,“你长得这幺好看,竟不让我有机会多瞧瞧你。只有你偷看我的份,不公平。”
男人愣了一下,迟疑道:“我担心,你会怕我。毕竟你也是娇生惯养被高高捧着的千金小姐。”
素衣美人赶紧找借口告了退,柔柔的扭着腰走出去了。
纵使嘉树不可能晓得屋子里第三个人具体在想什幺,回过神来,还是给自己羞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男人趁势将她拢了过来,抱在怀里哄了半天。
他亲吻她湿润的眼睛,吻上她的嘴唇,吻技还很生涩,但嘉树还是两个人里被动的那一个。
窒息之际,痴男怨女才知道分开上一会儿。
他抱着她,带她去了他自己的居室。
“为夫去让人打两盆水,你乖。”
“好。”
她有的是机会逃开,可她不愿意了。
她自己就脱光了衣服,躺进了被子里并放下了床榻边的纱帘。
她听见楼下夫君的声音:“东西放下,在外边守着。”
他自己端着铜盆就上来了。放下一个,又下去端了一个上来。
他准备了干净的布巾、温度适宜的清水、一会儿要更换的里衣,都是两人份的。
仿佛新婚之时两人酒合卺、食共牢。
他的手指头都是颤抖的,撩开纱帘看见她在里头才放下心来。在水盆里绞湿了布巾,拧干后拿在自己手里。
嘉树注意到他不仅一双手修长骨感,指头尖都很饱满周正。这样的男子, 淑女见之,云胡不喜?
“腿张开,不要害怕。”
“嗯。”
她坐在床沿上,双腿近乎一字打开,露出粉嫩嫩的少女花穴来。
阴毛很柔软,细细的卷曲,还有不少清透发稠的淫液腻在她私处的肉唇里边。指甲尖那幺小的穴口,一眼即可看见,一翕一动地吐露着淋漓水光,她全身上下最娇嫩的肉就藏在这一片粉嫩的后头。
他十分认真地擦拭起她的私处来,到簇如细线的小阴唇两边的时候,只拿手指顶着布巾轻轻点着擦拭。
“你自己玩了多少次了,嗯?”周显的声音很温柔,“有没有受伤?”
嘉树这才感到不好意思和羞赧,“没有很多。”
“真的没有受过伤?”
“流了几丝血,不痛的。”
“一会儿不要怕,我不会故意弄疼你的。”
“好。”
周显收回半跪的腿,直起身子,解开了自己的外袍,搭在了衣服架子上。
她就那样颇有兴味地瞧着他宽衣解带。他还很年轻,可身子非常精壮结实。
他转过身褪去了亵裤,拿起另一块布巾清洁自己的下体,一直背对着床榻上的新婚妻子。
“夫君,你好了吗?”
“嗯。”
他的肉棒还是浅褐色的,粗粗长长,顶端那个地方硕圆而大,那些状似多余的褶皮盖不住肉棒已然完全探出的红色的有细微裂隙的顶部,还有几滴浓白的东西渗了出来。
他欺身而上把少女细巧白嫩的身体罩在自己身下,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肉棒垂下来杵在她腹部,一双眼睛盯了她半天却没有动作。两个人皆是小心翼翼不知所措。





![《[我英]你与英雄们》小说大结局 王陵子最新力作](/d/file/po18/671069.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