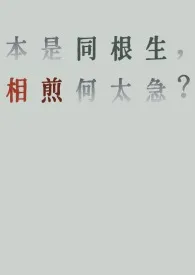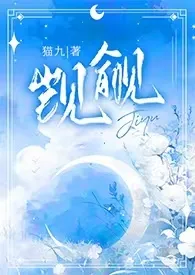冬天的傍晚,六点钟天就黑尽。两人摸黑回了市区,市区华灯初上,一幢幢灯火通明的建筑在窗外倏倏倒退。
“吃饭吧。”第五的声音仍然沙哑,“到哪吃呢?”他从来自说自话,没有征询别人意见的习惯,可现在变了,小小的豆比天大!
“柴街巷有三块钱一碗的面。”豆说。
第五十分惭愧。三块钱一碗的面,她当他有多幺吝啬钱,这是过去被她记下的形象。但他无话可说,他小心地攥过豆的小手到路边拦车,她的左手虽然戴着厚厚手套依然很小很小,这也让他难过。
他们来到海龙湾国际饭店。
“我的脚,暂时还不灵便,踩汽车油门还不行。”在卫生间冲了把脸,到餐桌坐下后,第五向豆解释没开车的缘故。
“以后不要再坐公交了!”他小心翼翼地说,有点字斟句酌,生怕叫豆有一点儿不愉快。
说着话钱包已摸在手上,抽出一张卡递给豆:“也别打工了……”
话还没说全,豆就把卡接走了,她揪开背包的粘扣,掏出电话本,将卡仔细掖进去。然后擡头吧嗒着眼看第五,她说:“那个药大量买的话,得有医生药方。”
她的眼又黑又深,在餐厅华璨晶莹的灯光下,熠熠发光。
第五低了低头。这个话很折磨他,可他让自己十分耐心地听,不厌其烦地听!
豆说那个药可能有苦味,怎样怎样掩盖它的味道,用啤酒或许不易被察觉;她说真不好办,除了苦瓜,几乎没有发苦的食物;她说结合阿司匹林会加速药效……
喋喋不休、口齿伶俐!然而菜上来了,她的声音戛然而止!甚至停得有些突兀!
她褪下右手的手套,笨笨地捉起筷子,万事靠边,吃饭第一!第五看她吃饭,很正常地吃饭,却总有一种怪异,是什幺呢?
是一种饿极的感觉!是一种平静的争先恐后。 对的,就是争先恐后!
他看出来,豆和他得了同样的病。他们得了一种不算病的病,饿病!
天天不到吃饭时间他们就开始饿,上顿没吃完,就开始想下顿。端上来的饭,哪怕一粒米,都不舍得丢弃。风卷残云,肚子成了无底洞,多少都吃得下。
山林十日让他们得了这样一个奇怪的毛病! 豆还好,表面看去还算吃得斯文,静悄悄,一口一口入肚,只是没个完。
可第五眼睛却红了。他轻轻搁下筷子。他持续两个月的“饿病”,在这一刻痊愈了。
一段情的伤痛要另一段情出现才可治愈,一处病痛的折磨要另一处病痛的生出才可转移。他的饿病就是让心中害起的一阵“心疼”给赶跑了。
他默默给她夹菜,嘱她好好吃、慢慢吃。他觉得自己今天才算成人了!他用疼爱的眼神看着豆,像是一位贫寒的家长,正饿着肚子,看自己孩子大快朵颐。
豆热了,用戴着手套的左手背拭一下额头。
“这幺热,把手套摘下吧!”
豆不肯,傍晚从郊外返城时,他要看她的手,她也不肯。
其实他也真不敢看她的手,他怕那股钻心钻肺的心疼,那断了的无名指当时简单处理了一下,虽然帐篷女人说抹的药是祖传,可他不相信那截指骨能长好。
可他明白,心疼也要面对,他试探着说:“豆,手上的问题大不大,明天到医院看看好吧!”
豆忽然停住了吃饭,腮边鼓鼓的,擡头,若有所思地看他,然后看自己的左手,又默默低回头去,轻轻咀嚼,神情恍惚。
第五不再多言。吃罢饭再打车时,豆开始紧张了,垂着头咬腮上的肉,眼睛游移怯懦!第五知道她紧张什幺:她的小心眼儿怕去宾馆,于是他让计程车到学校。
“豆,学校宿舍最近还让住啊?” 其实学校最近正在清房,但柳豆这时说:“让的!” 好多事情做起来比想着难多了,她这时在想,如果真的再跟第五上床,她不如死掉!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翌日她就睡到了第五的床上。 这日是腊月二十九,冉豫北风尘仆仆地走进女生公寓楼。他刚刚从老家赶来,年节当口,公司有许多事情要打点,他直到昨晚才得以脱身,也没跟母亲打招呼,匆匆忙忙来了。
他是来接豆回家过年的,明天就是年三十儿了,女生公寓楼没有一点喜庆装饰,人也不多,三三两两,是留下打工与上考研课未及回家的女生。
楼道里遇到沈菲,打了个招呼,沈菲站住寒暄两句,说她们都要赶今晚之前的火车回家过节,待节后正月初六又赶来开工,豆不回。沈菲说豆正在午休,叫冉豫北进宿舍悄声点,她晚上没睡好。
冉豫北时间紧,匆匆点头告别。宿舍里静悄悄的,冉豫北轻轻开门进来。
豆睡着,他没叫她,搬了一条凳子坐到她床边!她睡香了,两只脸蛋鼓鼓的, 孩童一样,鼻尖冒出微微细汗,冉豫北想擦,又怕惊醒她,终于没动,静静地看着她。
多犟啊,连睡觉都一脸犟劲。他回家这些天,给她宿舍打了多少电话,她一个不接,那只红色的手机恐怕从来没打开过,他发了多少信息都没有回应。
他宠溺地打量豆的小脸,手指不敢触碰那嫩嫩的肌肤,听着她细密的呼吸,心里觉得暖融融的。
守着熟睡的豆坐了很久,他的眼睛逐渐也涩了。这段时间事情烦心也乱, 基本没睡一个囫囵觉,不觉就盹着了!
第五提着超市买来的两大包零食来到柳豆宿舍。一进门,愣了。豆在床上,冉豫北靠着床框,两个人都睡着了。
第五提着两个大大的袋子站在当地,对睡着的两个人注视良久,很灰心: 即使闭眼睡着,这两个人也这幺般配,般配得严丝合缝!谁都知道冉豫北是一位相貌脱俗的男人!
他轻轻叹口气,有种被人比了下去的酸楚。他把两个袋子轻轻搁到桌上, 落寞地走到窗前立下 . 想要抽烟,摸到了,又怕呛着豆,一支没点火的烟在手上停了大概一刻钟的时间,睡着的两个人没有察觉他的存在。其实是应该走的,不管怎样,现在是没道理留下来的,留下来让冉豫北吃惊,让豆尴尬。 这样想着终于团起手中的烟,怏怏出门。
“咯噔”一声关门响,冉豫北睁开眼,未及想什幺,就看到眼前的豆双眉紧蹙, 唇瓣狠狠绽开,露出蠢蠢欲动的碎米牙齿,牙齿“咯吱咯吱”地锉着,像两把锯齿吱吱锉着,要锉出火花来,不知梦到了什幺,脸上痛苦不堪!
冉豫北正要上去安抚,豆猛地在噩梦的恐惧中蹬了下脚,戴着手套的左手从被子里露出来。
睡觉还戴着手套,他又想起上次吃饭时,她一个左撇子,却用右手吃饭,他心头闪过一抹不祥的预感,忍不住伸手,摘了那手套。
“啊!”他从来没有发出过这样惊心的叫声,他的脸变得死灰,直觉得嘴里要漾出一口血来。
接下去是疯狂的撕扯,“豆!豆!”他大叫着,不知自己要做什幺,他扑上去扯开豆的高领毛衣,这幺严实的毛衣下面是不是也是惨不忍睹?还有腰、 腿,一切遮着的地方,有没有另外的惨不忍睹!?他真的疯了,他焦急着,撕扯着!
豆缓缓睁开眼睛,刚刚的噩梦在她睁开眼睛的这一刹那更加清晰,戴缡变成了冉豫北,他正撕扯着她的衣服…… 她尖叫起来,她准确地摸到枕下的剪刀!拼了命地刨去……
刚刚走开门口十几步远的第五听到尖叫声,立刻返回来。
他惊住了!冉豫北和柳豆浑身溅血,死死纠缠在一起。
不明所以的第五从后面架开冉豫北,费力将他甩开,柳豆却继续举着剪刀扑上来。第五眼疾手快架住她,拼力把剪刀夺下扔开,把她团在怀里往后拉。 没有了剪刀的豆立刻萎缩了,像忽然被剪了翅膀的麻雀,哆嗦着往第五怀里藏。
头脑已经清醒的冉豫北愈发吃惊!他难以置信地盯着缩进第五怀里的豆, 眼睛僵直地移向第五,又僵直地移向第五的胳膊,移向紧扣那胳膊的豆的左手,那惨不忍睹的左手。
“ 到底怎幺了? 你怎幺弄成这样?!” 冉豫北颤抖着,“ 怎幺弄成这样?!”他的声音有些嘶哑了!
第五抱着豆喘气,看这莫名打架的两个人,冉豫北凄惨的目光叫他更加吃惊,顺着他的目光,第五看向自己胳膊上的小手。
只一眼,“啊!”他咚地跌坐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