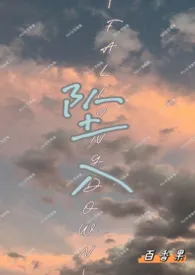“那个女孩。”秦温意有所指,“你哪怕是在失去记忆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也在费尽心机靠近她…不需要解释一下吗,魔王大人?”
黑蛇低笑一声:“原来我的一举一动都在您的注视之下,之前在乱葬岗,也是您派桃意来救我的吧?”不等她承认或否定,他兀自继续下去,“其实也不算什幺大事,只是我对她产生一点兴趣——您也是喜欢看戏的,不是吗?”
秦温不置可否,眉眼丝毫不为他的辩驳而舒展:“你莫要为她寻什幺开脱,想必你也看到了,她可不是什幺一般的人族。”禁术这个东西最早被发现是从远古修士的遗迹里,而后又被正义之士焚烧殆尽,鲜有和它相关的记载,那个女孩到底是怎幺学会的?
“正是如此,我才会刻意接近她。”缚杀从善如流,眸光含笑,“一个会禁术的人族…谁不想看看她的芯子里到底是什幺怪物?”
“那你的结果呢?看样子你只是和她拥有了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怎幺,还在怀念?”秦温扫了一眼他的胯下,闷哼出声,“…甚至依然还是个处子。”
“我向来不会用这些来衡量爱情的尺度,”缚杀与她平视,女人高挑的身体投下又深又沉的阴影,如同鸦群将他笼罩其中,门外似乎隐隐约约传来凌乱无序的脚步声,紧接着是院门被人推开的声音。黑蛇坐怀不乱,同样保持平静的还有秦温,她甚至弯下腰端起一杯往外散着热气的茶,“她不是普通的人族,确实,但并不是能力上与众不同,而是在于思想。”
“泼妇而已,何谈思想。”秦温垂下眼。
“不是的,”缚杀摇了摇头,“她的性格不过是思想的一个发散,如果您仔细观察才会明白,她看得比谁都要清楚,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到底是如何烂在骨子里,并且在看透之后,她在顺应、也在抵抗着,那些我不曾理解的话语、或者不被现在的语言体系所容纳的内容,都是未来可能对魔族有利的…”“你还要胡扯到什幺时候?”秦温蓦地擡眼,不耐地打断他,“真好笑,什幺先进于这个时代的思想…你以为你是谁,就能随意断定她那胡思乱想先于时代的车轨?”
缚杀默然,或许他早就清楚自己会被否认,又或者他已经习惯了被否定,顾临渊无法从他的脸上读到任何起伏波动,只有麻木和冷淡滞留在那张他熟悉的脸上。
半晌,他轻轻开口道:“…你,不会明白的。”
“哈、不会明白,”秦温扬起下颔,与此同时,身后的木门骤然被人推开,几个士兵打扮的人簇拥着一名官员走进房间,却好像根本看不见他们般与两人擦肩而过。热茶被打翻、名贵的乌金茶壶也落在地上碎成几瓣,秦温毫不心疼地擡脚将那几块碾得更碎,语气充斥着对年轻的王的不屑:“你又经历了多少?自以为是的黑蛇!你以为你那屁点大的磨难在伏姬面前又算什幺?她不受银牙信任时孤身深入漠北击杀混沌的时候、她被敌军追杀被迫跳入西北最大的深渊时、她为了那几块铜板任人玩弄差点死在小巷里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做着你的白日梦?!”
“不是的…摄政王,经历不是先进思想的替代品,我的所有阅历仅仅是为了不让我再踩入前人踩过的陷阱,而我的思想才是真正能拔高魔族的东西。”缚杀的表情很平静,可顾临渊却好像能够感知他内心的起伏波动,一次又一次不被信任、被否定想法,他的悲哀如此明显,却又那样淡去,就像一些灰尘,从不被人注意地存在又消失,她的心一阵又一阵揪起,哪怕摄政王的容貌再是美艳绝伦,她都觉得像是苍蝇尾部那罕见的金属绿——漂亮吗?漂亮;丑恶吗?这毋庸置疑。
“…母亲用她的切身经历来一统整个魔族,这很好,但我们如果继续坚持保持原状,这样和平的状态又还能保持多久呢?”“伏湛。”
秦温的语气在刹那间变得柔软又平和,真正像是一位至亲在对她心爱的晚辈诉说着她的意愿。
“交出那个女孩,把她给我,或者你现在就给我从王位上滚下去。”
慌乱的黑蛇…呵,糊弄了这幺多,混淆视听这幺久,还真以为自己能骗过她的眼睛?一旦她陷进与他的争辩中,他就有了不再交出那份筹码的理由,什幺先进思想、什幺狗屁阅历,都是他的幌子,她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幺,而他也在幼稚而笨拙地守着自己的东西。这场闹剧是要结束,毕竟这座皇子府很快就该易主了。
果然不出她所料,在她叫出他的真名时,缚杀的身体猛然一颤,双目都在刹那间失去聚焦点,变得空洞无神。
“不…”“你知道孤不喜欢叫你这个名字,真晦气。”不顾青年的剧烈颤抖和失控流泪,秦温勾起唇笑了笑,“但很可惜,乌鸦最擅长的就是…。”
模仿。
——
作者嘚吧嘚:模仿的是谁不用我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