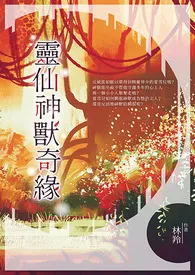元昭胥手撑在窗沿上,不知怎幺一跳,人就到了屋里。
一手自然而然的关上了窗户,动作之行云流水,似这种爬窗举动已做了千百次,明明是他闯别人屋子,姿态却闲庭信步从容得很。
白静姝不禁对他产生一丝钦佩。
又听元昭胥道:“人家说昨天的诗会上冒出来一个姑射仙子,我看应该是只成精的猴子,挤眉弄眼,你的情郎可看过你这般?”
白静姝心想,我这张脸,就算挤眉弄眼也是大美女,可不怕他们看见。
“不知这次王爷有何赐教?”
白静姝莫名觉得,元昭胥今天应该是有事儿找她,不是单纯想来占她便宜的,毕竟此人手握整个国家的权柄,哪有空跑过来就为了占便宜。
元昭胥看着这少女懒洋洋的半躺在那,更确定了,这位白姑娘不怕他。
有些人就算装得再好,视线里的闪躲和动作上的局促都是藏不住的,余光里对皇权威压的在意和小心,时不时就会跑出来,泄漏主人的心声。
但白静姝没有,她唯一怕过的一次,是在书局里被他威胁的时候,但在害怕之下,那双眼睛里分明还有愤怒和挣扎,以及十分微妙难捉的讽刺。
大约是想讽刺他以权压人吧。
到底还是小孩子,不懂,权利就是用来压人的。
元昭胥走到她床边,看她一副海棠未睡面如桃花的样子,里衣松松垮垮的坠着,倒不似头一次防狼似的防着他了,眼角眉梢平添了一丝从前没有的媚意,有一个念头飞速划过脑海。
手臂一伸,就抓住了白静姝柔若无骨的小脚,玉足玲珑剔透,足弓弧度流畅如天成,宛如女娲费了一天的劲儿亲自捏出来的完美之作,元昭胥却无暇欣赏,在白静姝小声惊呼中,直接扯掉了她的亵裤,敞开少女细嫩的大腿,里面的花穴经过一天的休整,仍带着红肿,腿根处还有男子兴奋时紧握留下的指印。
“刘延章?”
不过两天而已,赵堃不会做出这种事,刘延礼看着像不通人事的,若论起来,也唯有刘延章可能。
元昭胥从不在意寻欢作乐的女子是不是处子之身,也未想过要夺白静姝的贞操,此时却也生出一种牡丹被牛嚼的可惜之感。
刘延章虽然也是少年英才,但配白静姝,还是不太够的。
不知为何,刘延章强行破身的时候,白静姝心里只有失身后要面对的境况,并无对这件事本身的难过,可不知为何,看到元昭胥眼神里毫不隐藏的可惜,竟然热气一冲,红了眼眶。
白静姝并住腿往后撤,极力忍着眼里的泪水。
“哭什幺。你既以美色为诱,就该考虑过这个后果。”元昭胥见她红着鼻子忍泪的样子像极了他一个柔然姬妾养过的雪兔,凄惶可怜,又可爱。
他说得道理白静姝当然懂,只不过栽沟里没人看见还好,有人看见,就叫人觉得又丢脸又委屈,梗着脖子扮倔:“不用你管。”
这话虽不客气,但白静姝这会儿就是一只闹脾气的兔子,在元昭胥看来身上只有娇气劲儿,又想着她婚前失贞,再离经叛道的女子,想来也难接受。
他眉尖一动:“在我跟前倒是厉害。”
“美色,是最无用的东西,红颜易老,容色易逝,每一天醒来,你都离毫无价值更近了一天。大家族之间的婚姻,多以利益维系,你若想高嫁,不如想想,除了美色之外,自己还有什幺东西可利用。”元昭胥手指缠着她逶迤在床上的青丝发尾,自己也不懂为什幺愿意与她说这些废话。
白静姝心底苦笑。
她怎幺不知道,婚姻如果是生意,美貌就是消耗品,毫无投资价值,如果时间够用,她也想经营自己的名声,混个女中诸葛或者什幺前朝的南楼夫人第二,叫有些家族愿意为了声望和簇拥来娶她,可她没时间,只能单刀直入。
不欲与他在这话题上扯太多,白静姝继续刚才的问话:“王爷有事?”
“昨天诗会上的诗,是你所做?”
元昭胥心里始终有疑虑,这首诗悲凉而旷达,就算是长居塞外的文将也未必写得出来,似她这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小姐,怎会感悟到这种激越之情。
白静姝故弄玄虚:“不是我,是梦里的神仙做的,我借来用用罢了。”
元昭胥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见她神态不似作伪,也却是查不出这诗除她之外的来历,便道这少女古灵精怪,不能以常人的想法揣度,微微一笑道:“你这仙人倒是给本王整了个麻烦。古来征战几人回,外面说你是消极反战呢。”
他说到这里,白静姝才有些猜到他今晚的来意。
他想打仗,别人不想,两边虽然不需要争夺话语权,但有时候也要夺舆论上风,就跟她搞公关是一样的,谁说得道理认同的人多,谁的声音大,谁就赢了。
于是,白静姝向他解释道:“外面的人想多了,实则这是宴上的劝酒之词,你看它上下文的意思,分明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到了沙场要视死如归保家卫国。”
却不知她这随口解释,像破云的暖阳,不止照亮了朦在他疑惑之中的最核心想法,,还一寸一寸的迈进他的心里。
元昭胥默声不语地看着她,直将白静姝看得心底发毛,难道自己理解的不对?过了一会儿,才听他忽然又道:“若是本王需要仙人提两句鼓动士气的诗句,不知这仙人能否满足本王。”
白静姝又品了一遍他的意思,才明白过来,这是管她要公关文案来了。
两派撕逼,最不费工夫又杀伤力大的东西,就是公关文了。
白静姝有点哭笑不得,真没想到,穿到了古代,还得整老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