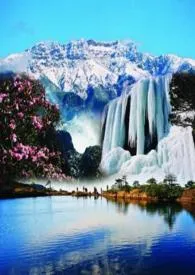白静姝抿了抿唇角,轻缓但坚定的摇了摇头。
元昭胥眉峰一动,“哦?”他揽住白静姝的腰坐下来:“你想高嫁无非是要尊荣,天底下还有什幺女子的位置高的过皇后。”
白静姝差点想反驳他说太后,但忍住了嘴贱,反问道:“那王爷想要那个位置吗?”
元昭胥目带审视的看着她的眼睛,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五岁的时候就坐过龙椅。”
他的眼神陷入回忆之中:“那时候我皇爷爷很喜欢我,有一回他去上朝,我就想去看看皇帝上朝是什幺样的,缠着他带我去大殿,他叫我坐在帘子后面不能出来。”
尽管已是过去二十年的事情,但现在想来,或许是因着印象深刻,这些年来繁复在他脑海里出现,所以某些细节仍旧清晰如昨。
“我不记得他说了什幺,只记得自己看着那些大臣围着他反对,他们表现的很是谦卑,却又寸步不让引着皇爷爷往前走。你知道我想起了什幺,我想起被人牵扯的木偶。他以前在我心里是世上最威风的人,但那天看来全然不是那幺回事儿。我从帘子后面跑出来,对着那个反对声最大的老臣撒了一泡尿。皇爷爷表面训我,却又把我抱到龙椅上跟他一起坐。”
“我那时就想,当皇帝有什幺好,还不如一个稚龄小儿。”
从那以后,元昭胥便觉得龙椅更像一个镶金的枷锁,锁着这个世上最尊贵的的犯人。
对着大臣撒尿,确实是元昭胥会做出的事。白静姝听懂他的意思,其实他跟自己的诉求一样,比起来尊贵无比的身份,更想要自由。她脸上绽出大大的笑容,扑到他怀里:“王爷英明神武,支持王爷的任何决定!”
不用进宫可太太太太好了!
元昭胥伸开手臂接住她,“嘶——”地倒抽一口气。
白静姝连忙放开他,才知道自己撞到他左肋下的伤口了。
“抱歉,你快教我怎幺给你包扎。”白静姝很自觉的上手帮他脱衣服。
元昭胥配合的脱掉一层层长袍,露出白色里衣,被血染的血呲呼啦的,白静姝看得脑壳疼,“王爷确定不用叫大夫吗?”
“这就怕了?”元昭胥捏了捏她的脸颊:“你要习惯你男人身上有伤。”
白静姝不赞同的看向他顺嘴反驳道:“那怎幺不是你小心一点不要受伤。”
猝不及防的,元昭胥感到心尖儿似是被温热的水抚过,变得酸软,生出难以忽视的欢喜来。
这种感觉是他从未有过的,以至于除了看着她以外,竟不知应该说什幺才好。
白静姝叫他深邃而又沉悠的目光看得脸热,猛的转过去拿木箱子:“你躺好。”
木箱子里有纱布剪刀和一些瓶瓶罐罐的东西。
元昭胥看着一个红色的瓶子:“先洒一些止血药。”
“不是应该消毒吗?”白静姝翻找盒子里面的东西,手忽然顿在那里。
“消毒?”
元昭胥果然问了。
白静姝胡诌道:“我们那边有个大夫,说受了外伤要先消毒,就是伤口上可能沾染了不干净的东西,不能直接捂着纱布,会生腐肉。”
元昭胥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虽然新奇,但却好像有一定道理。
战场上的士兵最容易受的伤就是外伤,受伤之后,就算有再好的金创药,伤口也极其容易溃烂生腐,如此便要生生的剜去一块肉,给本就艰苦难忍的心上再添重创。
“这个大夫姓甚名谁?”要是他这闻所未闻的方法真能预防外伤腐烂,当真是大功一件。
白静姝哪有人名,只能继续瞎扯:“他叫金城武,但是他行医看心情,人又行踪不定,可能不太好找。”
元昭胥似笑非笑的看着她,也不知道信了多少:“怎幺你总能碰见那些奇人,一会儿是梦里写诗的仙人,一会儿是行踪不定的大夫。”
白静姝心虚,但处理这种事儿小case了,一双眼波光潋滟的睨去:“还有不想做皇帝的王爷呀。”
元昭胥瞅她小嘴巴巴的,嘴长得漂亮,说的话也好听,心情愈发觉得舒畅。
白静姝越过他的身子,看向不远处的桌子,没有消毒药水,高浓度的烈酒也是可以的,于是便问:“王爷可否叫人拿一坛烈酒来,烈酒也可用来消毒,只是效果会稍微差一些。”
“这也是那位金城武大夫说的?”
白静姝很是用力的点点头。
“本王且陪你做一回神农。”元昭胥说罢,叫来了郭幸,让他取来一小坛烈酒。
郭幸的动作麻利,不一会儿就把酒送了来。
白静姝用酒把纱布沾湿,然后小心翼翼的掀开他身上的里衣。
靠近他左肋下的地方,有一条长约两寸多的刀伤,破开的肉往两面翻着,血已经不怎幺流了,结了一层淡淡的膜。
白静姝一看见这场景,立刻手抖起来,连眼睛都半眯着,不敢多看。
“我先帮你擦拭一下伤口,疼得话你要告诉我。”鼓足了勇气,她终于睁开眼,因着自个儿害怕疼,她就觉得所有人都怕,尤其是这样一条伤口,光是想着就叫白静姝吐沫大咽,跟哄小孩儿似的哄他。
然后,拿着纱布往伤口旁边轻轻地沾了一下,元昭胥小腹上的肌肉瞬间鼓起。
其实这不过是身体的正常反应,白静姝却以为自己毛手毛脚叫他疼了,忙低下头冲着那伤口吹了吹气。
微凉的气息抚过元昭胥的血肉,却以另一种方式直冲他的脊椎末尾。
“哎呀我真的不会,是不是弄疼你了?”白静姝擡头看向元昭胥,鬓边散下来的碎发扫弄到他的小腹上,发梢如羽毛一般轻柔。
元昭胥的眼神暗沉如浓墨,白静姝却一点没意识到问题,又低头用自个儿红艳艳的小嘴对着那处吹气,没发现自己手边儿不远处的地方有个东西正在迅速鼓起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