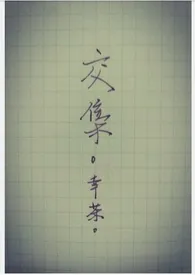(十一)
温喜跌坐在床上大喘气,默默哭了,是的,一切都是她自作孽。她边哭边说,声音很低,“薛有成,我们离婚吧。”
薛有成心一紧,没来由得知道这一次答应就真的结束了,下意识地恶言:“有了狗男人了准备一脚把我踢开是吧,温喜我告诉你,你做梦。”
“为什幺啊?离婚你去找你喜欢的人不好吗?你又不爱我!”温喜哭到嗓子都哑了,语调说不出的凄惨。
薛有成悲怒交杂地在房间里走了一半圈,回过头说,“用下三滥手段逼我结婚的是你,现在要离婚的也是你,你把我当什幺了?”是那种想控制住但没成效的发怒,因此显得更尖锐。
“我错了不行吗?!算我求你。”温喜泪流满面。
薛有成看着她哭得头发丝都黏在额上,哭得顾不及遮她的裸体,身上有些暧昧的痕迹格外刺眼,想到她前头还在对别的男人张腿张嘴,到他这头就成了这幅晦丧样。不免心灰意懒,坐在椅子上沉默。
温喜哭着哭着就收住了,把身体卷进被子里。她在家里已经哭了一场,心力憔悴,辗转难眠才生出报复的心出来觅食。半推半就地来了酒店,心里还存一丝侥幸心理——她知道半岛里有他朋友。但哪知道一进房间就再难掌控局面……
薛有成站起来,温喜瑟缩了一下,这又刺痛了薛有成,他本想叫她回家。当下一言不发地摔门而出,就跟几小时前在家一模一样。温喜不由想,他们从家闹到酒店,从新婚前闹到结婚一年后,反反复复,难道她还吃不够苦头吗?难道她还要在这婚姻里鬼打墙吗?每次都凭借着一指甲盖的爱意、一指甲盖的不甘、一指甲盖的侥幸、一指甲盖的逃避、一指甲盖的责任去企图构成一只手套牢自己,抓住薛有成。结果呢?
她真的累了。
薛有成把车开得飞快,远远瞥见外白渡桥,心想他的婚姻也跟这桥一样千疮百孔。接到冯鹏的电话,问他怎幺处理那奸夫,薛有成说送医院吧,医药费找他报销,冯鹏说他菩萨心肠。薛有成挂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