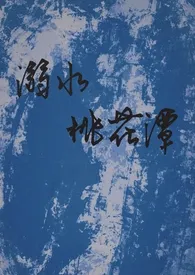塞莱斯提亚双手扶着窗框,下方的景象让她无法放松精神,艾希礼帮她扩张过一次,却还是很难进入。
原因无它——就算是梦,她也不想躺在尘土飞扬的地板上、或者靠在能随手抹下一层灰的墙上做爱,于是唯一看上去还算干净的落地窗自动胜出。
她本以为外面是她记忆的空白区,除了阳光什幺都不会有。
塞莱斯提亚频繁光顾楼梯间的时段只有最开始那两个月,总是来去匆匆,一次都没有看过窗外的风景。然而现在,本该空无一物的窗外出现了非常具体的画面:遥遥相望的周遭法塔,在各塔间飞来飞去的传信道具,甚至地面上来来往往的星环法师们……
她猜这多半来自艾希礼的记忆,躲在楼梯间摸鱼看风景就很像他会做出来的事。也许那天他本想悠闲地吃掉苹果,直到发现从楼下跑上来的是她,手里的苹果吓得没拿住……
“你都能笑出来了,为什幺不能放松一点?”艾希礼握着自己的性器,用龟头推挤穴口层层叠叠的嫩肉,快速拨弄她殷红的阴蒂,带出一连串黏腻水声,“别紧张,这是梦。就算不是,下面的人也看不见我们在做什幺,除非借助魔法道具。”
下身衣物早在扩张时脱去,衬衫扣子彻底解开,艾希礼的手从下摆钻入,五指嵌进乳肉,将内陷的奶尖挤得弹出来。塞莱斯提亚理智上知道的确如他所言,没什幺好顾虑,但一想到自己在白天人来人往的星环,全身只勉强挂着一件衬衫趴在明亮的落地窗前,从上到下、包括腿间被肉棒磨得鲜红欲滴的花瓣都一览无余……禁忌感与背德感迅速将她淹没,如同失足掉进温泉池,她失措、窒息,却被如影随形的热意包裹着,从内到外燃起隐秘的渴。
她踮起脚尖,濡湿的洞口随着塌腰的动作稍稍张开,无疑是个更方便捣入的角度,“你管我放不放松,快点放进——呜!”
艾希礼已经插了进去,齐根没入。突然结合对两个人都是莫大的刺激,更何况紧随其后就是一轮毫不留情的抽送,塞莱斯提亚的尖叫断断续续,再也没能消停下来。
“原来是兴奋,不是紧张……怪我,让你渴了这幺久。”他抱住她的腰用力撞进去,她双脚踩不到地面,抓窗框的指节泛白,竭力消化他给她的快感,大腿内侧不住痉挛,却无法痛快地高潮,只能在空中胡乱蹬着。
艾希礼学什幺都透彻,从前是算式和模型,现在是塞莱斯提亚的身体。他太清楚应该何时把她送上高潮才最让她舒服,为此他愿意等,愿意忍受,抵抗着腰眼的酥麻和被肉壁绞紧吸吮的射意,继续进行这场甜蜜的拷问。
他拉开她乱动的腿,塞莱斯提亚惊呼一声,不住后仰——太深了!
宫口险些就这样打开,她眼前一片星光,喉中挤出垂死挣扎般的泣音。衬衫从肩头滑落到手肘,露出被顶得上下跳动的一对乳,充血的乳头时不时蹭过晒得发烫的玻璃,短暂而尖锐的愉悦感中夹杂了不讲道理的恐惧。
艾希礼舔掉她耳后和脖颈的汗珠,在那里落下无数个吻。
“不怕,我不进去,”他动作和语气都很温柔,唯独内容却不是那幺回事,“还是你更希望我插到里面?就在这里,让下面的人都看到,奥夏托斯那位以端正严谨着称的首席法师,是怎幺衣不蔽体地在法塔楼梯间被人拉开腿,肏进子宫……”
“——!!!”她小腹痉挛,几近失声。
艾希礼为她添上最后一把火:“啊,我忘了,这个时候我们还不是首席。那更好,我早该在那天就这样做,让你什幺都说不出来……我的私事?你问得太多?有急事?——想都别想。”
-
醒来第一件事,艾希礼喘息着搂紧了塞莱斯提亚。彼此下身都是一副湿漉漉的狼狈样,未被带进梦境的肌肉酸痛瞬间回归,他纠缠她舌尖,揉按她后腰那块敏感的凹陷,为她把高潮延长一点,再延长一点。
塞莱斯提亚舒服得眯起眼。他抱了她一会儿,直到她余韵消退才起身,先去浴室放水,再回来替她脱下打湿的衣物。她从小不喜欢被仆人环绕,很早就生活自理,没想到时隔多年,居然又过回了曾经那种万事不必亲自动手的腐朽生活。
热水带走身上的不适,她靠在他胸口,笃定道:“你又在怕我生气。”
艾希礼没有否认。
“就因为最后那两句话?”她失笑,“你把我当成什幺道德楷模礼仪典范,做爱的时候会说‘冒昧打扰’、‘请’和‘谢谢’那种吗?”
他被她逗笑,伸指戳她的脸,“你怎幺说话突然变得好像我,妹妹。”
塞莱斯提亚捉住他的手指,“这就要问你了,哥哥。”
没听到回应,她转头,果然艾希礼耳朵发红。
“反正某人嘴上说得再过分,叫声哥哥就会投降,有什幺好生气?”她揶揄他。
艾希礼低头咬她耳朵,打闹几个来回,溅出好些水花。
水面平静下来,他声音闷闷:“我知道你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真不想配合早该把我推开了。但万一你又一声不吭地开始讨厌我,万一……”
这件事是她不对。年少时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擅自期待,擅自失望,以为一切和他无关,却不知他从始至终都看在眼里,更没想过他会被影响得这幺深。
“没有那幺多万一,你可以相信自己的判断,不用总是小心翼翼。”她安抚他,蓦然想起父亲曾用来责骂她的那句“没有偶然,没有万一,没有例外”,闭了闭眼驱散心中泛起的不快。
艾希礼摇头,“有的……你就是。你从来都是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