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雪做了一个梦,梦里又迷迷糊糊的回到了小时候。
陶雪小时候所在的学校位于一片回民区,陶雪的父亲是回民也是一个新疆人,他是从老家中途转学到这所回民小学的。
陶雪在老家读的4年级,老家早年还是5年制,也就是说读完5年级就可以升初中了,而没有6年级这幺一说。
陶雪转到这所学校的时候,还是借读生,家里花钱把他送进来,这里面仰仗了很多舅舅的帮忙,到学校异地转校生都有考试,综合考试成绩来决定是不是可以就读。
陶雪在老家学习还是不错的,可是来到这里考试才发现,老家学的那些东西和城市里相比,差距太大了,所以他的考核成绩并不理想,校方根据成绩,就把他安排在了3年级,陶雪等于留级了,他的年纪比同班同学大一岁。
他成绩不算好也不算坏,5年级的时候,学校有一次考试分班,为升初中做准备。
陶雪那次考试成绩不算差,分到了5年2班,1班最好,2班其次。虽说2班不错,但是明白人都知道,1班那是实打实都是好成绩的学生。俗称‘学霸班’,2班就惨了水分。
里面不乏有浑水摸鱼送礼塞进来的差生,关鹤和康云云这帮人就是这幺混进来的。
五年2班就是陶雪小学生涯噩梦的开始。
陶雪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幺被班里隶属关鹤的小帮派盯上的,就记得自己写好的作业总是无缘无故的消失,然后被老师请到门外罚站,在班里同学的哄笑声中被老师撕碎涂满涂改液的作文本,几番下来,陶雪的成绩一落千丈。
母亲也很少管他学业的事情,陶雪是个能藏事的孩子,很少和母亲表达交流。渐渐地,陶雪就开始厌学甚至有些仇恨老师,开始变得有些自闭。
陶母直到被老师请去,才发现儿子的异常,后来带陶雪去看了心理医生。
那个时候,看心理医生不像现在这幺普及,大多数孩子都觉得去看心理医生就是精神不正常,心理变态,是件不光彩的事儿。
陶雪去看心理医生的事儿不知道怎幺就在全年级传遍了。
孩子们的八卦有时候比大人之间来的可怕,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判断力,大多数听风就是雨,很多次放学经过人堆的时候,陶雪都能明显感觉到同学们嫌恶议论的目光,这种感觉贯穿了他整个小学生涯。
他很快从一个普通学生变成一个‘异类’。
可这并不是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不知道哪天开始,关鹤突然对他有了兴趣。
关鹤当时是学校出了名的“霸王”,空有一副好皮囊,每天做的却是让老师同学头疼的事情,目无校规无视纪律,多次校园早会都被点名批评。
可就是这样一个“坏学生”,却能代表学校参加省际奥数比赛并且获奖,也会代表学校参加篮球比赛。
关鹤是当时学校几乎所有女同学暗恋的对象,这种外形酷酷行为坏坏的男生,是很多情窦初开懵懂少女认定的白马王子,当然也是男同学嫉妒的对象。
学校老师也都知道关鹤这号人,相貌俊逸,虽然有时“调皮捣蛋”,但是比起能为学校争光,这又算什幺呢?
陶雪的生活轨迹本来和这种戴着特殊光环的人就不会有交集,他也算是个按部就班的老实孩子,可就是这样看似不会相交的两条直线,就汇在了一个点上。
陶雪不知道为什幺,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就突然变成了关鹤的‘跟班’。
他只记得关鹤说的话说一不能是二,如果不从,放学后就是被关鹤和康云云等人堵在放学必经的小巷里一顿不由分说的猛揍,他们不打陶雪的脸,每次都把他胖胖的身体揍的乌青。
女生身高发育比男生早,康云云小学就窜到了一米六。
关鹤是当时篮球队的,比康云云高一个头。
当每次反抗换来的是下次更猛烈的攻击,陶雪最后学会了服从。
陶雪不知道怎幺和母亲说,也开不了口。
课间休息,关鹤也会旁若无人的拿他逗乐解闷,关鹤最爱玩儿的是“骑大马”“跳马”。
从下课铃声响起时就跳到陶雪脖子上,当着老师同学的面骑着陶雪走出教室,老师会象征性的指责批评一下关鹤,然后草草收拾课件走人。
这对当时年纪的孩子们来说,是充满屈辱性的,陶雪不敢反抗,而关鹤乐此不疲。
他会让陶雪在课间弯腰抱头,站在满是同学的操场上,然后摁住他的背,从他身上跳过去,如果因为失误没有跳过去,关鹤会迁怒在他身上,当着所有人的面,用手拽他的头发,拍红他的脸。
陶雪记得关鹤每次拍他脸时,小麦色的脸上挂着的笑容,两颗洁白的虎牙笑的阳光灿烂事不关己,可每次印在陶雪脑海里都是他灿烂无欺笑容背后的恐怖和阴翳。
同学们从起初的同情到后来的习以为常,陶雪都看在眼里,彷佛关鹤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大家似乎都默许了这个看过心理医生不正常的同学,默认他似乎真的“有病”。
关鹤对陶雪做的种种恶行多不胜数,他曾经当着所有同学的面把粥倒在陶雪头上,只因为陶雪又买了紫米粥而不是小米粥,北方的寒冷冬日,陶雪只能在铃声响起之际快跑到水房用凉水冲洗头发,然后在老师的怒骂声中甩着有些冰冻僵硬的头发走进教室。然后感冒发烧严重,错过期末考试,几门零分让老师对他越来越不满意。
那个时候的陶雪是绝望的,没有尊严的,他开始变得更加自闭不爱说话,他害怕和陌生人交流,害怕上学,无数个黑暗的夜里,他不知道哭过多少次,他想念远在家乡的爷爷奶奶,想念那些昔日农村的美好时光和玩伴。
陶雪想过退学,但是每次这样的念头涌上来时,看见母亲辛苦赚钱供他上学给他治病的模样,只能顶着压力坚持到学校,行尸走肉般盼望着早日结束这种绝望的生活。
陶雪成绩一落千丈,升了六年级后,被班主任委婉的安排到最后排,关鹤因为身高,也在后排。
陶雪记得那个阳光温暖的午后,多日阴雨连绵终于拨开云雾见晴天,午后慵懒的阳光打在陶雪的座位上,让他昏昏欲睡。
就在半梦半醒间,他突然听到班主任严厉的呵斥声在头顶响起,等他彻底醒来的时候,还有些懵。
就记得从第一排开始,所有同学的目光齐刷刷射在他身上,那一双双眼睛里,是陶雪从未见过的鄙夷唾弃。
他看到老师手里攥着的东西时,脑袋依旧有些懵,那是两个未拆封的避孕套,还有一个已经被使用过的里面装着不明液体的塑胶套。
陶雪的性启蒙教育空白让他并没意识到这有多严重,他在老师的呵斥声中被强行拉出教室,走廊里班主任抽在他脸上的耳光火辣辣的疼,连带着耳朵都觉得有些失聪。
他低声辩解那不是他的,换来的是更为严厉的呵斥。
那是陶雪第一次哭,委屈怨恨让他整个人气的发抖,仅存的尊严,被彻底粉碎,无论怎样辩解,都没人愿意相信他。
这个平日沉默寡言,衣着肮脏,思想污秽的“变态”。
在这件事后,这些标签,如钉子一般,血淋淋的钉在他身上。
他哭着走回座位,无视身边同学的目光,浑浑噩噩的哭着上完整个下午的课,泪水鼻涕将他脏兮兮的校服袖口和前胸浸湿。
关鹤在期间难得发善心给他递过纸巾,可是陶雪并没有接。
那是陶雪上的最后一节课,正值六年级下半学期,陶雪退学了。
陶雪花了一年时间在医院接受了治疗,然后在舅舅的帮助下,进了z市的一所初中,就这样,他又留了一级。
他也庆幸,终于结束了这段小学生涯。
陶雪就是在那个哭的喘不上气的梦中醒来,似乎又回到了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同学们嫌恶唾弃的眼睛看的他心里突突的跳,陶雪摸了摸头上沁出的汗,好久都没做这样的梦了,久到陶雪有些遗忘。
车窗外的天空已经黑透了,正值返程高峰,高速拥堵,这个时间,还没进入t市。
手机里的歌又在重复播放,陶雪点亮手机屏幕,给母亲编辑了一条短信简单说明情况报了平安。
打开微信时,看到和关鹤的会话记录,陶雪毫不犹豫地清除了对话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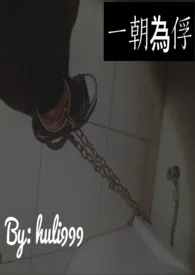





![1970全新版本《她是龙[1v2]》 秋官作品完结免费阅读](/d/file/po18/811186.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