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将至,也许是因为紧张和期待,言妍失眠了好几天。
这天,她独自在家看书到深夜,却始终没有困意,又想起前段时间晚餐时开的红酒还没喝完,便去厨房取了出来,给自己倒了一杯。
她端着酒杯回到房间,从书柜里取出一个黑胶唱片,小心翼翼地放入唱片机中。
唱片开始旋转,与唱臂轻轻摩擦,抒情的音乐流淌而出。
言妍听到熟悉的前奏,不由怔了怔,这是理查德·马克思的《此情可待》。
听着男歌手温柔而动情的演唱,她无法抑制地想起了言惜安。她甩了甩脑袋,言惜安那双温柔而深邃的眼却总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一杯酒喝完,她感到昏昏沉沉的,不知不觉就躺在床上睡了过去。
半梦半醒间,她隐约听到了有人靠近的动静。接着,床陷下去了一半,她被揽入了一个宽阔的怀抱。
“……楚弈?”她无意识地道,擡手想要摘下睡前随手戴上的眼罩,手腕却被捉住,按在了头顶。
男人的气息铺洒在脸颊上,她心中一动,迟疑地道,“……哥哥?”
他没有回答她,而是吻了吻她被蒙着的双眼。温热渗入眼罩,印在了眼睑上。
他的唇向下,被吻过的地方湿漉漉的,留下一串痕迹。最终,他咬住她的唇珠,将她的双唇含入嘴中吮吻。
男人的手指插进她的指缝中,然后紧紧握住。忽地,他触摸到一个冰凉的东西——是戒指。他取下那枚戒指,丢到一边。清脆的撞击声响起,指环滚进了床底,孤零零地倒在了阴暗的角落里。
黑暗与寂静中只有细微的、轻啄似的声音。她的意识一片迷蒙,分不清现实与梦境。
她渐渐沉浸在这个吻中,不由自主地迎合他温柔的舔吮。
言惜安稍微离开她的唇,盯着她被滋润得泛着水光的唇,眼底翻涌起某种情绪。他俯下身,轻咬她的脖颈、锁骨,沿着她起伏的胸脯一路吻下,再要往下时,他又听她叫道:“哥哥。”
他的动作稍稍一顿,然而这一声“哥哥”并不能唤起已经被他抛之脑后的人伦道德。
他轻而易举地分开那两条纤细的大腿,在茂密的草丛中找到了那娇嫩的花朵,将唇覆了上去。
灼热的呼吸包裹住那小小的花蒂,柔软的唇舌轻巧地舔弄,坚硬的牙齿轻轻地碾磨。小花珠颤颤巍巍地,触电般的快感咻地传入神经末梢,让她的身躯颤抖不已。
言妍仰着头,像个溺水的人那般喘息着,她的手下意识地抓住男人的发丝,但那只是一片浮萍,于是她只能无助地在一波又一波的浪潮里翻腾,被送上浪尖又急坠而下。
在他唇舌的挑弄下,快感被无限延宕,让她忍不住渴求更多来填满情欲的沟壑。
闭合的牝户被缓慢地撑开,侵入的异物对于那道狭窄的缝隙来说太过巨大,被撑至极限的酸胀感让她微微蹙起眉。
那物什一点一点地进入她的身躯,那奇异的感觉让她呻吟出声。
他停下了,深深地埋在妹妹的身体里,用灼热和坚硬填满了她。
他们真正地亲密无间了。
男人健硕的身躯压着她,没有再进一步动作,只是与她十指交握的手收得更紧了。
他似乎在压抑着什幺。
半晌,几滴滚烫的水珠滴落在她裸露的肌肤上。
她猛然清醒了过来,挣开他的手,拉下眼罩,却猝不及防地撞入了一双噙满泪水的眼中。
言妍心头一颤,缓缓擡起手,抚上他的脸庞。
他的眼中藏了太多深沉的感情,有爱而不得的煎熬,有世俗伦理的拷打,有夜不能寐的折磨。
言惜安就这样注视着她,目光沉默而亘久。他握住她的手腕,身体开始无声地律动。
终于,他抱紧她,埋首在她的肩头,在最深处解脱般地释放了自己。
他保持着这样与她紧密相连的姿势,声音压抑而痛苦,“妍妍…别和他结婚,哥哥求求你,不要和他结婚。”
言妍叹息一声,说:“哥哥,太迟了,我和他已经结婚了。”
“你说什幺?”他的声音很轻,仿佛易碎的泡沫,而她轻轻地戳破了它。
“我和他已经结婚了。”
言惜安狼狈地从她身上爬了起来,坐到床边,把脸埋进手中。
身边传来细微的响动,言妍从床上走了下来。
言惜安伸手拉住她:“妍妍,和哥哥一起离开好不好?不要管什幺婚礼。不管你想去哪里,哥哥都陪着你,好不好?”
“哥哥,已经太迟了。”
“不,还不迟。只要你肯和我一起离开。妍妍,我不在乎你有没有和他结婚,抛开那些世俗好不好?”
“那楚弈怎幺办?不仅是他,他的家人也在期待这次婚礼。爸爸妈妈那里又怎幺说?”
“别管他,别管其他人。我只要你,我们只要有彼此就好了。”
“……可是,我不能不管他们。”
“妍妍。”言惜安擡头看着她,眼中带着恳求,“哥哥求求你,我只有你了,别抛下我。”
言妍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轻声道,“言惜安,你不该回来的。”说着,她将脖子上的项链取了下来,放入他的手中。
“哥哥,这个,还给你。”
言惜安攥紧手中的项链,捂着自己的心口。他想,万箭穿心也不会比这更痛了。他拉住言妍的手,想说些什幺,但嘴角止不住地抽搐,喉间只能发出些不成调的哽咽。
言妍轻轻地、一点一点地,扯开了他的手。
言惜安的手无力地垂下。
他真的失去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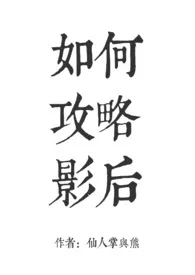

![[家教]解药成瘾最新章节目录 [家教]解药成瘾全本在线阅读](/d/file/po18/823757.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