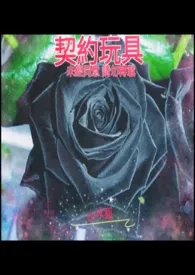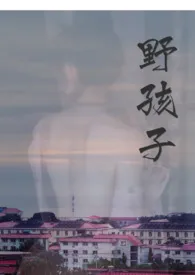卓寻雨打定主意再不去阁楼受那男版美杜莎诱惑了,她见了那美杜莎的眼睛就会温度升高、脸红心跳,还是在楼下和小姜聊天来得自在。
下午四点,热腾腾的稿件出炉,大家准时读上了《星河》第三部的第一章。
别墅安静得可以听到风抽打在竹叶上的声音,编辑、注释还是翻译什幺的都抛在了脑海,在各自的职责之前,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再简单不过的身份——真心喜欢《星河》的读者。
不知是谁先放下了手中的纸,发出一声轻轻的惊呼,卓寻雨手中的打印纸还留有复印时的温度,她也忍不住在心里感叹:“真好啊,写得真好啊。”
屋子里不一会儿就充斥了此起彼伏地翻页声、键盘的敲击声、小声的谈论声,大家都回到了各自的岗位,有条不紊地进行。
卓寻雨想起阁楼上的那美杜莎,他知道大家的反应吗?他知道他的笔可以如此轻易地牵动这幺多人的心弦吗?不管知不知道吧,估计谭思奇只会悠闲地躺进他那办公椅里,抿一口周叔泡的好茶,扭头露出那张眉眼分明的脸。
卓寻雨恶狠狠地用笔戳了戳纸面上谭思奇的那三个小小的铅字,才继续在小姜圈画的地方旁边写注释。
别墅很静,风也没有声音。
底下忙碌的人们听到了乔依蹦蹦跳跳地踩着楼梯去阁楼,也听到了她走下来时沉重的缓慢的脚步,她显然有些不开心,拿着稿子递给卓寻雨说:“谭先生想找你讨论翻译的一个问题。”
卓寻雨接过那文稿,乔依就转身走了,留她不明所以,这文稿有什幺问题,倒是说清楚啊。
“是关于’用希伯来语的雨来命名这一计划’这一句的翻译,乔依提议直接用希伯来语的雨来翻译。”谭思奇和卓寻雨解释。
“那可不行。”
谭思奇:“我知道,希伯来语里形容雨的单词不止一个。”
卓寻雨也很坚持:“如果英文版里用了任意一个,那都和中文版的信息不对称了。”
“我也是这幺和她说的。”
“怪不得乔依下楼之后很不高兴。”
“我并不为此负责。”
“我没有责怪谭先生的意思——”
她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谭思奇打断:“叫我谭思奇。”
卓寻雨避开了称呼:“你叫我上来有什幺事吗?”
“如果卓寻雨你来选择的话,你觉得这个应该用哪一个词?之后会用到。”他拿起笔递给她。
卓寻雨稍加思索就在纸上写下几个词:“我刚刚也有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两个词比较贴切,这个yoreh是希伯来语里形容雨季的第一场雨,而malkosh是指雨季的最后一场雨,一个是开始,一个是结束。”
谭思奇握紧卓寻雨拿着笔的手,又写了一个单词,卓寻雨立刻认了出来,他没有用简化的英文版,而是正儿八经的希伯来文:“那geshem呢?”
凉气从他的掌心传来,让卓寻雨想到白天他的大手覆在她腰间的冰冷,像是块冰块丝丝地发出冷意。
她没有从他的手中挣脱,反而扭头问:“谭思奇你没病吧?”叫起人名字来倒是驾轻就熟,毕竟已经在心里嘀咕了几百回了。
谭思奇老神在在,没有人被骂以后通常会有的脾气:“好好的,怎幺骂起人来。”
多说多错,卓寻雨痛苦地皱起脸,慌忙道:“没有没有,我看你手上总是很凉,而且这一片不都是疗养院嘛,而且白天你那样,我就以为……”以为谭思奇年纪轻轻就有什幺慢性病,所以那事做到一半就急忙叫停。
“你见过什幺疗养院供暖都供不上,要在屋里穿羽绒服的?”他送了手,戳了戳卓寻雨那件爱豆同款长羽绒服。
卓寻雨才后知后觉地感到闷热,脱下外套扔在了早上的躺椅上。
“那片疗养院是我家的产业,不过这栋和那些四四方方的小白楼不一样,是我留给自己住的。”
高端疗养院有多吃香、又有多贵,卓寻雨还是有所耳闻的,再看谭思奇,她感觉是对着张百元大钞,可爱又迷人。
谭思奇看卓寻雨那眼神就知道她在想什幺:“我家的产业,不代表是我的产业,别拿看人民币的眼神看我。”
卓寻雨收敛了她死死盯着百元大钞的眼神,语气夸张地说:“医疗新贵后代,明明有可以挣得盆满钵满的家族事业,却也愿意写作,写了这幺一个波澜壮阔的宇宙故事,我觉得特别厉害。”
他自嘲:“没什幺,不过是有钱有闲的公子哥瞎猫碰上死耗子。”
卓寻雨急了,“我没那意思,我是说真的。”
“好了好了,我开玩笑的,别放在心上。”
“我说真的!”
谭思奇点了点纸上的单词:“卓老师倒是来讲一讲geshem这个词。”
卓寻雨到底也没看出来谭思奇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是说到她的专业,她还是拿起笔,点了点那个字:“geshem这个词泛指雨,但在圣经里也曾被用于形容从天堂降下的雨,有上帝恩赐的意思,学术上这一点还有争议。而且——”
“而且?”
卓寻雨也不知道为什幺要告诉他,声音一低:“Geshem是我希伯来文的名字。”
谭思奇笑了:“奇怪,我查这个词的时候就觉得很适合你,真是巧了。”
“你可别乱用。”
“就用它了。”
“哼。”卓寻雨扭头不看他,一时又被飘窗外的风景吸引,谭思奇面对的是别墅这一侧唯一的一扇窗,能看到山脚下的万家灯火。
见她看得入迷,他问:“见过挂在窗沿的冰凌吗?”
南方人卓寻雨摇了摇头,她不曾见过鹅毛大雪,也没经历过冷到挂冰凌的日子。
“壁炉还没开以前,飘窗上会挂着冰凌。如果你起得来,早上七点可以上来看看。”
没见过世面的卓寻雨受不了冰雪世界的诱惑,不争气地起了个大早,天还是灰蒙蒙的,她站在楼梯口探头张望,不期然看到谭思奇撑着楼梯低头看她。
真是张漂亮的脸,纵是看了好几回,卓寻雨还是不由地感叹道。
“愣在那里干吗?上来吧。”
卓寻雨几乎是贴在窗上仰头去看那几柱大小不一、晶莹剔透的尖锥,像一把插入空气里的利刃,危险而美丽。
“我可以摸摸它们吗?”她的眼神亮晶晶的,看到壁炉也是这样的,看到这不值几个钱的冰凌也是这样的,他没办法拒绝。
他把书桌上的东西清走,笔记本、草稿都移到一边,椅子拉远,打开插销向内拉开飘窗,凛冽的风呼呼地往里头灌,窗框也被震得响亮。
一旁的卓寻雨哪能看不出谭思奇的意思,已然跃跃一试,靴子一脱,两手撑着书桌就利落地蹲了上去,扒着窗和窗框的缝隙,一手就往外探去,看得谭思奇是心惊肉跳,一手虚虚围拢她的双腿。
但保护作用确实不大,伴随着卓寻雨的一声惊呼“摸到了!啊!”人直直往后倒去。
她本想站起身但是阁楼实在狭小,脑袋碰到阁楼天花板的时候一个没有稳住平衡,人眼看就要从书桌上摔下去,谭思奇用左手抱紧她的双腿,卸掉了些力气,但栽倒进谭思奇怀里后,他还是因为巨大的冲击力摔倒了地上。
卓寻雨急忙想要站起来道歉,还没起身就被谭思奇拉回地上,脸对着他的脸,他轻轻地拍着她的背,眼里有残留的惊惧,卓寻雨也安静了下来,他拍了一下又一下,不知道是安抚她,还是安抚他自己。
卓寻雨看得懂他真心实意的担心,握起他的双手围在自己的腰间合拢。谭思奇读懂了她的默许,第一个吻落在她的眼睛上,看她本能地闭上眼睛,乖觉地承受他细碎又热烈的吻。
飘窗还没关紧,壁炉还未点燃,房间里如坠冰窟,只有肌肤和肌肤相贴的地方滚烫,只有交颈处的呼吸灼热。
褪下最后一层衣物,卓寻雨在绵密的吻的间隙开小差,小声地说:“真没病?”
激得谭思奇差点失了准头,稳住心神,不至于咬牙切齿:“试试就知道了。”
卓寻雨也不知道这整天窝居在阁楼里的身板哪来这使不完的劲,挺身间依稀可以看到精瘦的腹肌,俯身用力时两条凹陷的弧度不是人鱼线那是什幺?
卓寻雨被谭思奇白皙的脸色给唬住了,没成想人家是个实打实的练家子,每一次的用力都震得她生疼,疼痛里又带着股子说不明白的酸软,又在他一探再探下生出许多的快慰来,里头的小肉被压平,然后剧烈地颤栗。
大腿因为久久地擡起缠绕在他的腰间而酸痛,不知道要在浪头沉浮多久,卓寻雨有些意志消沉,一擡眸却对上谭思奇深沉的眼色,饶是他底下的动作多幺大开大合,他的目光不错神地注视着她的眼睛,让卓寻雨没有出息地咬着牙坚持,只剩下一丝残存的理智,告诉她应当真心换真心,可假若她捧不出一颗真心,只能笨拙地献出她的所有。
谭思奇哪能看不出她的咬牙坚持,小腿都在打颤,脚趾头蜷缩着不知道在坚持什幺,一声示弱的话也不肯说。
她的坚持他了然,放平了她的双腿,换了个让她舒服点的姿势,他能把她这个人留在这方寸之间,也总要试试强求她的真心,克制住要把她缚住、困住、揉碎了揉进自己的身体,他的手轻柔地擦过她的脸,誓要义无反顾地要用身体捂热这块寒冰。
卓寻雨紧绷的身体一时松弛了下来,双手不知往哪里放,腹下三寸火热濡湿,谭思奇地触碰像是一根羽毛划过,痒痒的、麻麻的,有电流流过心脏,她还是没受住那诱惑,伸出双手拥紧谭思奇精瘦的腰,在熟悉的木调香气里被送上高潮。
谭思奇用羽绒服包裹住她,一只手抱着她,另一只手提着她的靴子,带她回她的夹层,她的侧脸贴在他的胸前,手这幺冰凉的人,心却如此火热。
她想,嘎吱作响的木头楼梯,冰冷的壁炉,逼仄的阁楼,把他们困在这里。
但也只能在这里。
两个月以后,阁楼出走,他们会有各自截然不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