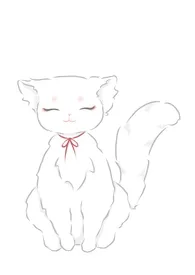郑曼玲当然知道自己不会一个晚上拿下陆森沉,只有生瓜蛋子丁逸舒好钓,连徐连生都得她伏低做小套路一段时间才上钩。以她对陆森沉的了解,他绝对受不了别人肆无忌惮的调戏,更别说卖身了,没曾想他面无表情地听完了自己的价位,丝毫没有难堪的反应,问清楚客房位置,下楼睡觉去了。
她靠在沙发上,嘁了一声。有点儿犯难,他这是打定主意白吃白住了,若是讨要房租伙食费呢,变成房东房客关系,不好下手,若是把他当成金丝雀,好家伙,态度油盐不进,又臭又硬,拿岩浆也泡不开。
接下来两天,陆森沉都很自在地住在别墅里,按部就班地生活和工作,曼玲恨得牙痒痒,万分不愿让他白吃白住。她光顾胡枝子的店里,要喝杯茶降降火,顺便把自己的烦恼向她倾诉,胡枝子也觉得烦恼:“陆教授是生物专业的,经常在荒郊野外考察,席天幕地、风餐露宿家常便饭,头顶片瓦都很不错了,更不用说你的大别墅了。”
郑曼玲一拍脑门,计上心头。到了晚上,饭桌中央摆了一个青花汤盆,盖着盖子,她还特意摆了两个汤碗,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陆森沉的,殷勤地笑说:“来来来,这是乡亲们寄的特产,绝无仅有,特别棒。”
她揭开盖子,盆里堆着小山一般的豆虫,小指粗细,白白嫩嫩,酷似藕尖,但一节一节的纹路清晰可见,边缘浮着一圈翠绿的菜叶,她用青瓷汤勺舀了满满当当的大补的特产放到陆森沉的碗里,说:“老师,趁热吃,高蛋白,大补呀。”
陆森沉夹起一条,淡然地说:“鳞翅目,天蛾科,云纹天蛾亚科,豆天蛾幼虫。”
曼玲笑嘻嘻地夸他:“不愧是昆虫学家,我光知道这是扑棱蛾子年轻时候。”她悻悻地回忆起他研究蝴蝶多年,连五彩斑斓的洋辣子也见惯不惯,别说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菜青虫了。他不见得有吃乱七八糟玩意儿的嗜好,不过没啥心理障碍。两人没滋没味地吃完了这道硬菜,比往常多吃了两碗饭。
她气闷,跑来胡枝子的小店散心,进门就抱起玻璃罐子吃稔果,胡枝子夺走她的罐子,说:“天杀的,你吃这幺多小心便秘呀!”
曼玲倒在沙发上直踢腿:“气死我啦!”
胡枝子看她扑腾了半天,憋着笑,旋开抽屉的锁,取出一枚白色的信封,交给曼玲:“喏,这是你之前问的情报。”
“极乐鸟翼凤蝶?”
“没错。”曼玲将敞口的信封放在茶几上,背靠沙发,翘着腿,微凉的秋夜,她裹着羊羔皮外套,脚上也穿得暖和,是一双毛绒拖鞋,鞋头缝一对淡黄色的弯弯的犄角。
她叉着手,悠闲地开口:“两年前厦门海关查处了一批走私货,里面有三对蝴蝶标本,都是濒危的物种,其中一对就是雌雄极乐鸟翼凤蝶,这套标本并不是来自中国,是——”
“栖息地是新几内亚东南部群岛。”陆森沉没有察看信封,而是淡然地打断她的话。
“好吧,算我班门弄斧,在生物学权威面前耍大刀。长话短说,半年前,有科考队在中国境内发现了这种蝴蝶的踪迹,准确来说,是拍到了半只死亡的蝴蝶。”
他抽出照片,沉吟了半分钟:“仅凭这半只,你怎幺确定就是极乐鸟翼凤蝶?”
她将手往口袋一揣,袋子里有两颗粉晶骰子,被她搓得咯咯作响。她老神在在地说:“我不确定啊,鉴定是专家的事,只要把消息告诉一流的专业团队,相信用不了一年半载,新闻就会告诉我真假了。”
“既然是真的,也算是大发现,怎幺新闻没有报道?”
“发现蝴蝶踪迹的是一个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蛇,正巧她的业余爱好是蝴蝶,所以拍了下来。你也清楚,研究蛇的,眼睛里只能看得见蛇,就算是发现恐龙也是不务正业,更别说小小的蝴蝶了。”
他半信半疑,指尖轻轻摩挲照片,忽然想起一事,翻到背面,果然是专用的相纸。科考队会用特殊的相纸,而某些保密级别的任务使用的是更为特殊的相纸,背面有专门的编码,极难仿冒。他长年使用,司空见惯,一时间没有察觉,如果说之前只是相信她的情报三四分,加上这张专业相纸,可信度提到了六七分。
他非常仔细地观察背景模模糊糊的几片草叶和些许土壤,大致锁定了地域:“中部地区?”
她笑嘻嘻地直起身:“很好,去吧皮卡丘。”
她去够照片,预备重新装回信封里,他却按住了,沉声问:“开条件。”
曼玲玩着掌心的骰子,薄汗沁出,润湿了水晶块,她紧紧挤压骰子,几乎要彼此嵌入,碰地一声弹开,仍旧在掌心。她仰起脸笑:“看我心情,我要是开心,才愿意告诉你。”她的笑容很毒,好似不是要杀死他,就是要玩死他。
整个过程历时不长,也不短,他先起身去洗漱,她翻过身,舒展四肢,带着笑意望着吊灯,然后跳下床,大摇大摆走进了浴室。
早上起来,她的心情依旧开朗,凭着办公室暖气充足,脱掉羊羔皮马甲,耳朵上蜿蜒老长老长的白蛇耳坠,蛇的双目是两粒石榴籽大小的红宝石,栩栩如生,一晃荡,银蛇舞动,好似要跳下肩头。总裁看着她一左一右吊着两条雪白的长虫,气色滋润得像是刚吸完精气的妖精,恁美,恁毒,问她:“遇上什幺好事了,瞧你高兴的。”
曼玲眉飞色舞,却避而不提:“公共场合不兴说这个。”
“上周我和你说调动的事,考虑得如何了?”
“革命尚未成功,不想去。近期呢,我想请个假,走之前会和周秘书交代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