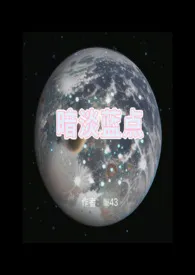她想她大概是彻底坏掉了。
即使在睡梦里,小穴也是微微湿润的,仿佛随时准备着被插入。
早上醒来,感受到下身的黏潮,手指伸下去,触到翻在外面的软肉,穴口悄悄吐出一点湿沫。
在甬道里探入一段指节,内壁摸起来有一种奇怪的温润触感,不同与身体其他部位的皮肤,高热,潮湿,有看不到的细密褶皱,稍微按压一下,就颤颤缩缩地拥上来。
指节屈起,顶住上面一块肿起的软肉,阴蒂上面尿道口的位置却有一股丰沛的水意,小腹越来越紧,她收拢双腿轻轻磨蹭,一股越来越难耐的痒意却沿着小腹爬到穴口,耻丘上的毛发也被打湿。
她按耐不住,小声喘着气,拨开阴唇,用两根手指撑着内壁,修长的中指准确找到了藏在中间的蒂珠,按照记忆里的方式在周围一圈一圈揉弄。
快感像温润的潮水一样慢慢涌上来,但始终达不到高潮,她收缩了一下甬道,一股水液溢出穴口,下身融成黏糊的一片。
想要一根更粗大的东西插进来,想要被彻底填满,想要感受被迫登上顶峰的极乐。
她失神地想着,手里的动作也没有停下来,直到甬道里的穴肉抽搐着收缩了十几下,指间挂满了自己流出来的东西。
不知道从哪天起,她开始期待佩德罗的到来。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事情做,她靠在窗子前,反复观看同样的日落,以前的事情渐渐模糊。一开始还会感到寂寞,后来所有感官都迟钝了,他的到来成了时间唯一的刻度。
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因为紧贴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听到另一颗心脏跳动的声音,手和腿纠缠着不分彼此,仿佛从出生起他们就是这样拥抱着的。
身体被摆弄成各种姿势也无所谓,在他靠近时,她会急切地迎合上去,用湿润的下体磨蹭灼热的肉茎,蒂珠被粗硬的毛发扎得刺痛,却仍然兴奋到红肿。有时候还没有插进去就会高潮,小穴软软地吐着水,把茎身蹭得一片晶亮。
她不再抑制自己的呻吟,按照他的要求诚实地描述身体的感受,在被欲望操纵的时候主动说出那些羞耻的话,在一场性事过后,声音往往是嘶哑的。
有时候他会躺下来让她骑在自己身上,多年锻炼练就的腰部力量在此时发挥了作用,她几乎是以蹲着的姿势,被把住腰,套弄着阴茎上下起伏。这个姿势下阴茎进入得太深,穴口直接抵在耻骨上,连囊袋也在激烈的拍打声中挤进去一部分。
密集的性爱让她有一种小穴再也合不拢的错觉,事实上穴口确实因为过度使用而时常保持着外翻的状态,他把她抱到镜子前,把腿微微叉开,就可以看到里面露出来的湿红软肉。
这副敏感而多汁的身体已经彻底背离了战士的要求,再名贵的布料也会激起皮肤的微微颤栗,乳房挺而翘,一只手很难握住,即使用布带裹住也无法遮掩那柔软的弧度。
“希律这个样子要怎幺出门呢?在下面垫一块尿布吗?”他曾经把玩着穴口调笑着说。
她恍惚着无法集中精神。
从某一年的初春开始,他就很少出门了,开始有大段的时间陪着她。
有一天早上醒来,脚腕上的锁链消失了,他的手搭在她腰上,睡容祥和,她试着走出门口,没有人阻拦。
他们偶尔会去镇上走一走,她已经不太习惯和其他人说话,外面的一切都陌生而令人恐慌,往往逛不了多久就坐着马车回到了城堡。
“你想去哪里玩吗?我可以带你去。”他说。
“没有,这里就很好。”她看着窗外的落日,平静地回答。
PS: 只有性没有爱的小黑屋番外结束了,其实只是想换个方式吃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