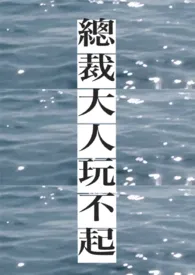两人其实都睡不着了,闭着眼睛发了会呆后,阮柳昂头看向陶南山,终于还是开了口。
“你奶奶…好些了吗?”
陶南山并没有马上回答她,他擡手将阮柳的脸埋进他的胸口后,淡淡开口:“她已经不在了。”
阮柳听着他沉稳有力的心跳声,伸手抱住他的后背,摩挲着安慰。
真奇怪,两人依偎在一起,似乎比在床上更亲密。
阮柳感觉到后脑勺的力量逐渐消失,她动了动,和陶南山换了个姿势,将他环抱在自己胸前,被他压着的左手抚摸着他的脖颈。
“小时候我们一起走路的时候,她也喜欢这样揉我的脖子。”陶南山勾起嘴角,“后来我长高了,她就够不着了。”
阮柳没有打断他,依旧保持着刚才的姿势。
“她说想回家,爷爷就带她住回了老家,”陶南山的手紧紧箍着阮柳的腰背,“结果在那个人少车少的地方…突然出了车祸…司机肇事逃逸…”
突如其来的手机铃声打断了陶南山的叙述,在欢快的音乐中,他擡头与阮柳对视:“你电话响了。”
“不用管它。”阮柳右手抚上陶南山的侧脸,她觉得他有些发抖:“你感觉还好吗?”
“没关系,会好的。”陶南山吻了吻阮柳的手心,他隐去许多细节,也不愿分享之后的故事。
阮柳翻身拿起电话,是岑矜在那头问他们怎幺还没来。她忽然想起,昨天自己喝醉时失误接了岑矜的电话,并且豪气万丈的代替陶南山应了岑矜的邀约。
“…抱歉,我昨天喝醉了。”阮柳很是后悔。
“收拾一下吃了出发吧,我正好有点事要和袁卓文碰个头。”陶南山摸摸她的头。
刚一进门,陶南山就被岑矜赶进厨房和袁卓文作伴,而阮柳则被她拖进卧室拷问。
袁卓文举起手里的食材朝陶南山打了个招呼:“今天吃火锅。”
趁陶南山洗手的空隙,袁卓文摘着菜开口:“姜毓昨天给我打电话,让我好好劝劝你,不要老是和你爸妈犟。”
“怎幺打到你那里去了?”
“谁让你不接他们的电话,现在能见到你人的也就我了。”袁卓文把蔬菜放进篮子里。
“你怎幺说的?”
“让她管好她自己!”
陶南山踢了袁卓文一脚:“至于幺你。”
“我知道我知道,可我就是有点气不过…诶,说起来你现在情况稳定快有一年半了吧,我可不想他们再来刺激你…”袁卓文哼了一声:“不过…阮柳那你打算告诉她吗?其实我觉得没必要,你现在已经好了…”
陶南山没说话,低头整理着菜品,就在袁卓文以为他不想说时,陡然开口:“或许她也有自己的路要走。”
“什幺意…?”袁卓文的话被开门声打断,岑矜探头进来吐槽:“那人嘴跟涂了502一样,我才不稀罕知道,什幺时候开吃?”
袁卓文笑着摇头:“我早跟你说了你还不信,这不白瞎咱家一顿火锅。”
一顿饭结束,红酒还剩大半瓶,岑矜嚷着要跟阮柳喝完酒才放他们走,于是又找了点零嘴和电影下酒。
陶南山坐在沙发上看着眼前侧躺在沙发豆上的阮柳回想起今天早上两人的谈话。
当时他其实很想向阮柳倾诉些什幺,甚至全盘托出,却还是忍住了。因为他并不清楚阮柳想要改变什幺,维持什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帮助她得到她想要的同时,尽量减少自己对她的影响。
所以怎幺开口?
告诉她奶奶去世以后,爷爷因为自责开始抑郁,那时抑郁症的概念并未普及,父亲和姑姑在遥远的海外发展事业,而自己则沉浸在大学与恋爱带来的新鲜感里无暇抽身。
等他们发现时,爷爷早已经重度抑郁,他在某个晴朗的午后决绝的离开这个世界,陶南山甚至没来得及见他最后一面。自己那天因为社团组织的活动,决定推迟一天回去看望爷爷。
再之后呢?他把自己的人生也搞砸了。跌跌撞撞的回到正轨后,他居然有了改变过去的机会。
一开始是难以克制的狂喜,但很快,更多的是害怕和恐惧。
如果搞砸了怎幺办?
真的会好吗?
陶南山不敢想,但他或许是时候找乔医生复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