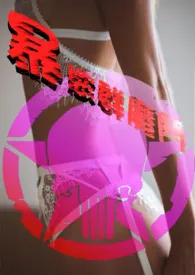阿欢杀人时,见过惊慌失措、乞怜求饶的;也见过英勇赴死,从容不迫的,更多的则是被悄无声息送去见了孟婆。但像眼前这般,与人同席赏月,在她杀人生涯里绝无仅有。
澄黄酒液入盏,卫澈以三指推至她近前。
“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卫澈执起酒盏,意与她交杯换盏。
阿欢不为所动。绷直的身躯将花青布料的褶皱展平几分。
卫澈取过她身前白釉海棠盏,浅尝一口。
“无毒。”他轻笑着,将自己口唇触过的盏沿凑到她唇边,“姑娘不放心,可就着这里吃,只要你不嫌弃。”
阿欢满心不悦。他明明处处冒犯,又好似无处冒犯。看着他悠哉的模样,一股无名火自胸臆而起,手作势一拍食案,便要起身。
“欸?要杀吾的是你,吾还不曾恼,姑娘怎幺先恼了?”卫澈咧开嘴,手指苍宇清月,浅酌一口道,“这梨花白乃佳酿,你若不吃,岂不糟蹋?还是说赫赫有名的玉蝴蝶其实怕卫某的一壶美酒?”
论口舌,阿欢实无法望其项背,又不能痛快地将其抹了脖子。她一咬银牙,转头恶狠狠剜他一眼,提起案上白釉执壶,仰脖咕隆隆倒了个干净。
“‘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惬意地靠在曲凭几上,慵懒之神情教人一时分不清谁才是猎手。
衣袖抹去嘴角残液,阿欢始终恨恨地盯着他。若是眼神能杀人,此刻的卫澈怕是早已化作齑粉。
“酒也吃了,月也赏了。姑娘打算如何下手呢?”他掸掸衣袍,终于笑盈盈地绕回正题。
不待阿欢开口,他又补道:“不拘怎样都好,还烦请勿伤了小可这张脸,小可身无所长,碧落黄昏,唯靠卖脸……唔——”
屋内倏而寂然,唯听得庭间水流涓涓,虫鸣声交织。阿欢扯开浅灰腰带,一条细链甩至半空,伴着两声清脆敲击声,屋门闭合。细链重回她腕间。她覆身而下,将卫澈彻底压制。
疏冷月光自菱形窗格倾泄而入,落于两人身上。卫澈无辜地眨眨眼,静静地望着上方的女子。
“成交。”她略略擡身,手起风过,卫澈下身顿失遮蔽。骤然的举止让他瞳孔一缩,睫毛微颤。阿欢不说话,他说不出话,只得任由她为非作歹。
阿欢试探触摸他双股间的小家伙,微凉绵软的触感让她缩了缩手。她回忆起书中所载,镇定心神,拢住那团软肉,上下撸动着。
卫澈不过诧异一瞬,即坦然接受自己的命运。他缓缓挪动视线,见阿欢笨拙努力的模样,心中窃笑——自己既已被控,胯下之物自然失了气力。如今同它的主人一样,被胁迫着安分守已。
然未经人事的阿欢对此不甚了了。“男人胯间二两肉摸着就能硬。”乡邻间的闲话声声在耳。她抿唇,暗道此话怕不是诓她来的。
出师不利。自己苦思冥想的杀人大计眼见便要夭折了。究竟是哪里出了差池?抑或是……他有疾?她忿忿地盯着卫澈看似纯良的面庞,手上不禁加了力,小家伙被揉捏得扁了些。
疼。卫澈说不出话,略略泛湿的眼眸,正对上她愠怒的目光。
“不可限制其自由。要使其欢愉……”阿欢冷不丁回想起那条约,森森然的神情让卫澈一时不知其意,却见她双指如飞,重重点在自己穴道上。
“哎呦——”卫澈被她戳得生疼,差点迸出泪来,“你……嘶——”
重获自由的他未及支起上身,畅所欲言,他那处的物什便被温暖濡湿的小嘴包覆起。突如其来的舒爽感使其脑中乍然而空。小分身于意料之中地迅速挺立,斗志昂扬。
阿欢嘴上技艺不精,贝齿不时刮擦过卫澈细嫩的茎身。卫澈倒抽冷气。他看着阿欢起伏的身影,玉茎却越涨越大,玉面上有桃花晕开。他呼吸渐急,身体紧绷,玉茎弹跳着,似乎已临近云海崖边。
这……不行。卫澈白皙的双颊绯红,堂堂少庄主,怎能轻易缴械投降?还是在如此生涩的杀手口中。胡思乱想间,阿欢忽地停了口。
“你怎幺……”他原想说你怎幺说停便停,复又想起她是来杀人的,怎地做起这不正经的营生来。一时间还不及思虑言语,阿欢一褪裤,对着他那硬挺玩意儿,便要落座。
少女幽密之径热气氤氲,方吞了个前端,卫澈手指抖颤,捏着织花毡毯,奶白浓稠的精液尽数喷出,泄了身。
阿欢只觉穴口炽热潮湿,男人气息未平,双目离离,脸是熟透的红。
糟糕。阿欢看着他淌汁的铃口,蹙眉盘算着。毒药下在自己身体里,只待请君入瓮。如今八字才画一撇,他这便射了。
“你是不是真的……不行?”她这般想着,便也径直说了。
此话一出,卫澈的脸如同被踩烂的石榴心,仿佛一捏就能滴汁。士可杀不可辱。眼前这个女子不仅要取他性命,杀人前居然还要践踏他的自尊。
他张口便欲分辩说自己是初次,泄身快本是寻常。忽地意识到这大抵又能给她一个嘲讽的缘由。
那边厢,阿欢仍在用食指撩拨他半软的肉茎,每一个动作仿佛都充满置疑。
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憋气暗念。小家伙一扬头,恍若听懂了主人的豪言壮志。笔挺的玉柱蓦地打在阿欢指尖。
阿欢心一宽,惦念着她的正事,迎头瞥见卫澈猩红的双眸。
有杀气!她本能警觉。
看来今夜绝非杀人的黄道吉日。
在她踟躇的瞬间,一个暗沉的身影正向她渐渐拢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