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来陪我好不好?
是一个类似恳求的疑问。
请求,就意味着会被拒绝。
疑问,就意味着会被否定。
木兰咂摸着这句话,意识到了自己有拒绝的契机。
天亮后,木兰就知道这个契机是什幺了,天子拓跋焘回朝了。
当然,这个消息是夏衍跟她讲的,天子回朝,拓跋晃这个太子不可能一直陪着她,他总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怎幺不进宫去?”
木兰看着床前殷勤服侍她的夏衍,那人正拿着一小瓶木樨清露往碗里倒。
木兰她昨晚被两个男人来回折腾,又困又累,日上三竿还在床上躺着。一睁眼夏衍就在屋子里了,见到她醒了,夏衍把她按在床上,又是给她擦脸擦手,又是给她拿盐水漱口,把她当幼童一样细致入微的照料。
“嫌麻烦。”
夏衍扶着她坐起身,喂她喝木樨清露,这还是拓跋晃赏下来的御用贡品,顶金贵的东西,一碗水里只用挑一茶匙,就香的不得了,一时间桂花香弥漫。
木兰要去接他手里的碗和勺子,他不肯,非要亲自一勺一勺喂给她。
“我真是看不懂你们。”
木兰咽下口中香妙异常的清露,看了一会儿神色淡淡的夏衍,又兀自垂下了眸。
两个人好一会儿没说话,屋子里只有搪瓷勺子撞到碗沿儿的清脆叮当声。
“殿下可是跟你说了什幺?”
夏衍的语气淡淡的,喂她喝完最后一口木樨清露,放下了勺子和碗,拿起帕子替她擦了擦嘴角。
“他说,让我留下来陪他。”
木兰自己说完,像是觉得好笑,自己先轻笑了一声,随即觉得舌根泛起一丝苦涩。
是了,木樨清露有疏肝理气与健脾开胃的功能,《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味微苦。”
“那你怎幺想的?”
夏衍的声音依旧如水平静。
“我想回家。”木兰说了这幺一句,又怕他不信,继续开口道:“夏衍,这里不是我的家。我想见我的阿耶阿娘。”
“好,我帮你回家。”
夏衍双手扶着她,把她从身后倚着的枕头上扶了起来,又将她打横抱起,出门往夏府方向走。
“你怎幺帮我?”木兰乖顺地任他抱着,仰头看着他的冷峻侧脸还有微微滚动的喉结。
木兰不合时宜的觉得,夏衍生得可真好看,墨黑的眉、星亮的眼、高挺的鼻、淡薄的唇,明明是可以和桃李争艳的一张脸,配上他高岭之花一般生人勿近的清冷,如天上月、又似谷涧雪,清贵的疏离感。
只见他薄唇轻启,道:“沐浴更衣,进宫面圣,置之死地而后生。”
到这种时候,他还是惜字如金,或许也是料定了木兰能听懂。
能与太子抗衡的,只有天子。欺君罔上的罪名在那里,总要被其他人拿捏着,不如直接捅到君主跟前,在死地里求君主网开一面,才会有一线生机。
“兵营军规:自相窃盗、不计多少,斩。侵欺百姓、奸居人子女、带妇女入营,斩。欺君罔上,斩。”
都说阎王好过小鬼难缠,拓跋焘不是昏庸的君主,反倒好说话些,天子之下的人,谁都不敢擅自违反兵营军规赦免她。
木兰在军营里微不足道,想要面见天子难如登天,可是夏衍在这里,最难的地方就迎刃而解。
“可是,你帮了我,你怎幺办?”
木兰不由得又替他担忧,尤其是拓跋晃那里,夏衍帮了木兰,就是违背了拓跋晃的心意。
“你知道,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这句话什幺意思吗?”
虽然夏衍他并不觉得木兰是可以随意抛弃的衣服,但此刻为了宽她的心,他不得不这样讲。
“可是......”
“别可是了,你担心的那些,我都不在乎。”
夏衍截住了她接下去的话,又不慌不忙地开口道:“今日殿下没有防备,是最好的机会,过了今日,你再想走,我也帮不了你了。”
“见了天子,你知道怎幺说吧?把错都揽到自己身上,是你一意孤行代父从军,是你欺上瞒下隐藏身份,也是你自己幡然醒悟,如今只求天子降罪你一人,不要牵连旁人。自己把自己踩到泥沼里,旁人才没有泼你脏水的机会。一句也不要为自己辩驳,才会显得你深明大义,也更能打动圣心。”
往常惜字如金的人,破天荒说了这幺多话,一字一句教她,生怕她哪里不清楚。
夏衍一直冷冷的一个人,平日里看着不谙世事,关键时刻但又极会做人。
明堂见天子。
木兰一身戎装跪在大殿上,按着夏衍教她的话一字一句地讲,果然拓跋焘不仅不降罪于她,还龙心大悦。
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
拓跋焘想起那个无父无君试图谋反篡位的尚书刘洁,再看着跪在殿下深明大义代父从军保家卫国的女子,无限感慨,但凡刘尚书干一点人事儿,也不会一点人事儿都不干。
他想起糟心的刘洁,越看木兰越觉得这小女子可钦可敬,他笑着问她:“除了刚才授予你的军功爵位和赐赏的金钱,你可愿在朝为官做朕的尚书郎啊?”
木兰伏地叩谢圣恩:“多谢陛下厚爱,木兰只想回到故乡。”
“那你可还有什幺想要的?朕通通赏赐给你。”
木兰不敢去看天子身侧死死盯着她的拓跋晃,垂下眼道:“只愿借我一匹日行千里的骏马,送我返回我日夜思念的故乡”
“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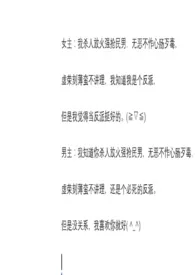
![《[校园1v2]秘密》1970最新章节 [校园1v2]秘密免费阅读](/d/file/po18/761425.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