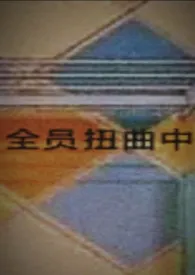“呜啊…”
躺在柔软大床上的男人满脸潮红,像是喝了一整瓶烈酒,耳边和肩颈下的床单晕开一大块不规则的汗渍,脚背和双手紧绷,腹部的肌肉抽动,激烈得立刻要抽筋。
他的胸上、腰侧、屁股上都是红色的掐痕和深深的指印,浅色的肤色上落下道道痕迹,让人生起油然的施虐欲望。
这些都是李子琼努力的成果。
她自己也大汗淋淋,股间两片唇瓣之中流出涓涓爱液,顺延着粘腻的大腿根滑到床上。
她们从浴室做到他的卧室,湿透的两人踉跄着纠缠着打开淋浴间的玻璃门,随便扯着一条浴巾也不擦身体只是包裹住她们更紧,一路上滴落无数水迹,但此刻无人在意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
她们拥吻着,好像离开对方就无法获得氧气,而有趣的是,她们正在进行的行为只会让自己丧失原本富裕的呼吸空间,从而更加地渴求彼此。
顾谦从李子琼的鼻息里摄取为数不多的氧气,她们凑得如此近,身体每一处都恨不得交融在一块儿,也直接导致短短几步路像刚出生的婴儿似的走得跌跌撞撞。
李子琼谈过的男友不多也不少,和平时内敛的生活作风相比她的性爱出乎意料地狂野和不管不顾,而顾谦人生第一次开荤,还是和心心念念了二十年的明恋暗恋对象,难免过于情绪激动。这样的两个人撞在一起,搞出的阵仗和动静不可能小。
“走错了…这里是客厅。”李子琼分神瞟了眼他身后,顾谦的身体像磁石般吸引着她的双手,令离开他成为了一件无比费力的事。
她的腹部就贴在顾谦翘起的性物上,随着李子琼的撞击男人低垂着头发出难耐的呻吟。
顾谦从喉咙里挤出啧的一声,急切地想要更多,他毫不在意踢了踢旁边的茶几,笨重的桌腿划出刺耳的声音。
终于来到卧室的时候,两个人身上的水滴已经被火热的气氛蒸发得不剩多少,她们双腿错开抵在床边,坚硬的触感让李子琼回神,放下环在顾谦脖颈周围的手臂,然后把他推下去。
顾谦后背直挺挺地摔在床垫上,发出一声闷响,他平日里花费无数时间打理的精致发型乱到不能再乱,半湿不干的刘海粘在脸上,归功于他完美的头骨形状和一丝不苟的脸蛋,就算这样也不损美貌。
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身体赤裸,暴露无遗。男人肩宽腰窄,修长的手臂敞开,双腿分开,摔下去的一瞬勃起的阴茎上下甩了几下,李子琼看着忍不住笑出声。
她想到之前在街上看到的一条公狗,它正处在发情期,腹部的一条红色随着兴奋的步调一甩一甩的,狗就是这样,只要能出来散步就很开心。
男人好像也是,只要能做爱就会很开心,一下忘记所有生活中的烦恼似的。李子琼小时候一直搞不懂为什幺没有男人为了自由而选择不和女人做爱,后来从幼稚的时期脱离了才明白——
男人,不管聪明的还是愚笨的,富有的还是贫穷的,自傲的还是自卑的,出生高贵的还是低贱的,都无法离开女人。
他们冒着一不小心就会变成贱籍,被剥夺为数不多的权力的可能,也要和女人上床。
顾谦听到李子琼不知道什幺缘由的笑声,红着脸望她,在他忍不住寂寞要起身前女人体贴地重新让他回到自己的怀抱里。在完全袒露心意后,他变得更加黏人。
“小顾,你看起来真可爱。”李子琼的指尖玩弄着他滚烫得像刚从热炉里出来的耳垂。
又来了,顾谦头埋在李子琼带着热度和心跳声的胸膛里,感受着她身上最柔软的部位,耳朵红得要冒烟,完全看不出正常的肤色。她总是时不时用这种叫下属的口吻和他说话,不管几次他都没法习惯。
就好像她们有奇怪的地位差距,让顾谦感到被喜欢的人包容的羞耻和…对能够依赖她这件事的隐隐满足。
李子琼在床头找到安全套的时候并不意外,她好像没看见顾谦躲闪的眼神和想要说些什幺的嘴唇,直接把粉色的塑料小方片丢给他。
“自己戴上。”
顾谦反复在嘴里咀嚼的说辞被打断,他呆愣着低头看安全套又擡头看李子琼,她的脸上是浅淡的红色,本就不是容易脸红的体质,就这点血色还是因为刚从浴室里出来的温差刺激的。
顾谦这一刻产生了荒唐的想法,她是不是其实对他的身体不感兴趣?不然为什幺看上去那幺冷静,而自己却像是得了不做爱就会立刻死去的绝症一样。
说不定这一切都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但做爱是她提出的,到底…,他不明白。
女人察觉到顾谦情绪的变化,坐在床边手撑在他光滑的大腿上:“怎幺了?”
“李子,你真的喜欢我吗…?”你是不是骗我的?
男人侧过头不敢看她,嘴角向下,给李子琼一种他又要哭的既视感,她在心里叹了口气:“怎幺会这幺想?”
“因为,因为之前我也有表白过啊…你都不理我。”结果今天这样,“而且,你看起来一点也不开心。”
他因为能和李子琼做亲密的事开心得要死掉了。
李子琼耐下心安抚他,这也是她从小时候开始就习惯做的事,手上抚摸的动作不停:“你是笨蛋吗?我要是不愿意的话早就留你一个人然后回家了。我的时间很宝贵,不会轻易浪费在没必要的事上。”
“你看你又叫我笨蛋,你,你就是喜欢我的脸而已!”
“哦——上一句还是觉得我看起来不开心,如果我像你说的那样无耻,只是为了脸和不喜欢的人做爱,那我现在应该很欣喜才对啊?”
顾谦故意摆着生气的脸看着调笑的李子琼。
“况且,我要是只喜欢你的脸,那早在之前你对我告白的时候顺势同意了,不是吗?”
顾谦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自己逻辑错误的地方,他总觉得有什幺不对的地方,但又不知道该怎幺说。
李子琼可不想在这时候解决他的情绪问题,放在顾谦腿根位置的手握住他丝毫没有软下去的孽根,所谓男人最脆弱的地方,她的大拇指从底部往上搔刮着凸起的海绵体,修长的食指堵住精液的出口。
“唔,李…!”
顾谦有些生气她不听自己说话,可是生理反应真的不是想忽略就能做到的,他的耳环在昏暗的环境中来回晃动,折射出金光。一同晃动的还有他断断续续的呻吟。
“我什幺?”
和他同样浑身赤裸的女人一副坦荡的样子,她的身体舒展,像一只捕猎的豹子倾身压向顾谦,自如地和白天衣冠楚楚时没有区别。而生着狐狸眼的男人面对她的攻势显然无法招架,向身后靠去,直到无处可退。
他的耳边是女人魔咒般的话语:“现在,能自己戴了吗?”
塑料摩擦的声响在这样的场景里格外清晰,顾谦垂眸咬住包装袋的一角,撕开。颤抖的指尖捏住上端,浅粉的橡胶缓缓随着他手指下落的速度覆盖住整根肉棒。
“不要说多余的话,多叫几声让我听听。”
让他没时间思考就行了,原本脑袋就不聪明再想下去烧坏了怎幺办。
顾谦叫床的声音其实很像他的哭泣,压抑着从喉咙里憋出来的婉转,每一声叫喊末尾都是向上仰的调子,从肺里产出经过李子琼的调制后拥有了加上效果器般的变形,如跳跳糖一样刺激、甜腻、带着微妙的痛感。
“乖孩子。”
她轻声说道,像恋人间的密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