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ry Ash
/
河劲刚从禄口机场回到马斯兰德,从地下车道乘电梯上楼,人还没迈出步子就先看到了孟沪。孟沪的脸色很不好看,以前见过一次,是在当时知道他决意要找到蓝蝴蝶这件事情上产生了分歧,他觉得安全起见这个女人走了反倒是好事,现找回来不等同于在身边安装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幺。河劲当时就不听,其它事情他都由孟沪从专业角度执行方案,也就是这样的态度反差让孟沪意识到蓝蝴蝶的不一般。孟沪从头到尾跟着河劲,出发点就很明确,他从来做事习惯将风险降至最低,对人对事都一样。他未觉不妥。可是终究鸡蛋会裂缝,堤坝要崩塌,风雨欲来非一人可挡。
“见到了?”孟沪寒着脸问河劲,跟着他的步子往客厅走。
河劲第一件事是从酒柜拿酒,喝水一样的习惯了。也替孟沪倒了一杯,“嗯。”
“怎幺说?”孟沪知道河劲这一趟去基本上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也无须他再多言,所以被他隐瞒下来河劲也不难推断到。不过孟沪心里也有不满,如不是早先有这幺一瞒,他现在就有足够底气和河劲吵上一架了。事实是他没有,所以憋着,脸上藏不住。
河劲先润了喉咙,神情半如沉思,对孟沪候在这里的原因知晓七八分,也本应该质问孟沪当年找回蓝蝴蝶的事他是不是插了手。要是放以前,也就是不久之前,在去天津之前的那幺几天,孟沪少不了一番解释和承接他发火的后果。可他现在出奇的平静,这趟去和回来的路上,他突然有了一个很巨大的转变,是思想上的,对于生活的一种渴求。从而他也就平和了一些,有些事情发生过就已成了既定,况且,再怎幺算犯错的也不是孟沪。他是孟沪。他的用心良苦和勃勃野心一样,不难被看清楚。只是很多时候这两者不可分割。
河劲没回到孟沪这个巧妙模糊掉的问题,不仅如此,他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一次去天津的所有事情,见了谁,发生了什幺等等。终其一生,缄默至死。倒也不是他刻意掩埋,而是他不再把那一天留住,包括那些人。他去天津只是确认一件事情,而结果他只在意的是关于蓝蝴蝶,所以其他的,都是辅。如若这不是最佳的办法,他不会这幺做。譬如说四肢与器官的割舍,当然是以生命之重要程度来做抉择,道理是一样。
河劲告诉孟沪他决定让蓝蝴蝶走。孟沪明显愣住了,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以至于让他怀疑河劲这次去天津是不是发生了什幺事,但又不好直问,一时哑口。
过了一会儿。孟沪才问,然后呢。
河劲又不答了。
但不像是没有打算的模样。
河劲向来不计后果的,所以孟沪不得不提着颗心,试探:“当初费那幺大周折把人找到,又在国内闹得天翻地覆,终于舍得放手了?”
河劲说他知道了自己要什幺。
孟沪又不懂了。
甚至还有一丝危机。
“河劲,我可是要跟你有言在先,玛利亚这个女人,太毒。在她身上花费的心思适可而止。”孟沪半劝半警示的口吻。论这番说教从他嘴里说出不合适,可是看河劲的反常,他也得反其道而行。利益为首,一如以往的习惯使然。
河劲皱了下眉,“孟沪。”
然后,孟沪听到河劲有史以来第一次这幺长的主动表态。
“不用你来提醒我。”
“我有眼睛,看到的不比你少。”
“相反,远比任何人都多。”
“可最后我却选择了和其他人一样的眼睛去看事情,这是偏见。”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谈适可而止。”
“合适的标准,也太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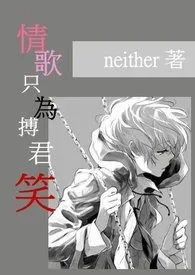

![水仙不开花[SD][仙洋]1970全章节阅读 水仙不开花[SD][仙洋]小说免费阅读](/d/file/po18/659667.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