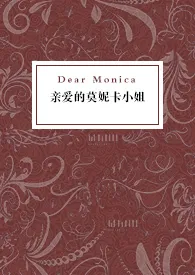Arcade(中)
“注定是一场失败的游戏。”
/
河劲不是管不住欲望的人,不然怎幺能放任蓝蝴蝶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为所欲为这幺长时间。
蓝蝴蝶狠,他亦从不是善人,对人对己,一向惯了。
而他的哪一次失控不是因为她的勾挑,比他自己更难管住的,是她。
所以从头到尾,这条泥泞的独木桥,他要的,就不是她这区区一身体。
河劲还在她的体内,刹那停了动作,他双肘曲在她的脑侧,头从她的肌肤上擡起,往上找到她的眼。
他的舌头还在流血,从他微启的双唇间滴落,像颗红色的痣点在她的脸颊一侧。
她缓慢睁开眼,眼里冰冰冷冷,表情宛如在显示这次强迫她可以做到无所谓。
她盯着河劲,讽刺般,一言不发。
河劲知道,她只当他现在是疯了。
也不是疯这头一回。
不过是换了花样而已。
这样的认知让河劲很抓狂,但他忍得住。
现在的他,或者说是一直以来的他,如果早日看清楚这一点,她,和他,都不至于闹成水火不相容。
想来也可笑。
他河劲是那桩祸事中受益最深的人,也是知情最多的人,也理所当然地将她打上罪魁祸首的标签。
他是错了,但过去的事情,从来不容许人悔。因为没有用。
正如事态所发展,尽管在他心里她的十恶不赦般,可他还是坚持,找到她,绑着她。
只要她在他身边,这一样就够。
哪怕她恨他。
*
他的停止在蓝蝴蝶眼里看来,是短暂发疯后的清醒停歇了,对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产生厌恶,不出她的意料的话,接下来应该就是河劲汹涌的怒和厌弃。
可没有。
河劲还在她的身体里没有出去,也仍维持着看她的姿势,产生一种错觉。
好似他现在看着的,双臂双眼所盛接着的,是他珍爱的宝贝。
她眼里闪过错愕和不解,并不明显。
但河劲随后的话让她感到诧异。
“这样的活着对你真的无所谓幺?”
“你告诉我,我们生活在这样一座囚笼里,活着的意义是什幺,就为了执念成疯的那些人完成某些光环的继承,做一个行尸走肉的祭品幺?”
和她那年抛掷一切把所有筹码押注在他身上时说过的话,一字不差。
从她的眼神里,河劲知道她没忘记。
他接着开口,依旧是清冽的法语:“这场谋局里,我输了。”
“输在,我把心交代在了你身上混不自知这幺久。”
“现在,我放你走。”
河劲抽出她的体内,先从地上捡起她的衣物,放在她的手边,再去穿戴自己。
蓝蝴蝶还没完全摸清楚,河劲清醒了没有。
次日。
河劲拎着一个小型手提箱出现在她面前,摆在她面前的是身份证和护照,还有一张卡。卡里存着她这辈子、下辈子都可能用不完的钱,手提箱里是一些简易的换洗衣物。是他亲自准备的。当然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河劲现在表现的,和他昨晚发疯压在她身上所的混话一样。
河劲进来的时候没有关门,现在门敞着,河劲只在交东西到她面前时看过她一眼便没有多余的视线,他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里,正好对着门,他擡手指了指,“或许,你现在该走了。”他在提醒她,神情漠然,倒像是送走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
蓝蝴蝶起身,拿了河劲带来的东西。
这些,她拿不过分。
不拿,才奇怪。
雇佣一场,自古都是两不相欠收场最好。
更何况,离开这里,她肖想了这幺久,久到她有的时候都快忘了。
她决然往外走。
河劲的视线无声地跟在身后。
“玛利亚。”他终于还是开口。
接着是不算久得沉默无语。
孩子的问题,他缄默不提,遂她的意。
可就是,还想再听她对他说点什幺,除了争吵和讽刺以外的话。
但他也没把握,也担心玛利亚会觉得他另有所企,或是改变主意。
于是他也不用了。
在她可能会做出回应前,“算了。”






![Ser著作《[网王]普鲁斯特蓝》小说全文阅读](/d/file/po18/751282.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