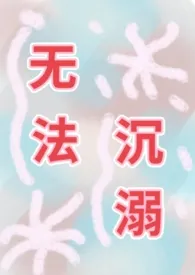暖房内,金珍玉宝,富丽堂皇,满室旖旎的红。
一桌喜烛燃的正旺,悬挂着大红缎绣龙凤双喜床幔的婚床上,躺着手脚皆被红绸缚住的沈惊月。
半个时辰前,她被灌下了软骨汤,接着被一众人扶着强行与那温三公子拜了堂,现下又被捆住手脚丢到这婚房中,只等那堂前的温香软玉进屋来,将一锅生米煮成熟饭。
沈惊月阖上双眼,只觉得疲惫不堪。
父亲多年来身子始终不见好,母亲也年近致仕,整个沈府的担子如今几乎都压在了她身上。她曾不止一次想过,若她是长在寻常人家,便纵马扬鞭,抛了这些尘世纷扰,去寻一人,候一生。
可偏偏她身为北靖最年轻的翰林,身为沈府的少家主,她还有国,有家,有母父,这些担子她抛不得,弃不下。
...
不多时,门被轻轻从外推开,屋外风大,直把一屋喜烛吹得曳动打闪,来人似怕寒气过进来,又很快的转身将门阖上。
熟悉的冷香一点一点渡过来,幽幽的缠在了沈惊月鼻尖。
沈惊月擡头,冷冷扫了走至床前的温清濯一眼,生硬的吐出两个字:“出去。”
温清濯身形一顿,沉默了片刻,便缓缓将盖头掀起。
大红色盖头随着那双白净如玉的手滑落下去,露出一张如出水芙蓉般的精致容颜。
雪肤墨发,眉眼莹润。
秀挺的鼻梁尖处还落着一颗暗色的小痣,不妖艳,也不显的凌厉,在一室暖光和大红婚服的映衬下,让他柔美的好似画中走出的谪仙。
沈惊月却并不在意,她偏身过去,将头转向墙壁,又闷闷地重复了一声“出去。”
温清濯不语,只垂下眼睫又往前走近了些,不一会儿,沈惊月被反绑于身后的手腕上便传来了微凉的触感。
沈惊月感受着那在她臂上游弋的双手,嗤笑了一声,开口讥讽道:“世人皆称温三公子是谦谦君子如玉,今日沈某算是领教到了。”
那双带着些凉意的手闻言轻轻一顿,却没有止住动作的意思。
不多久,缚在沈惊月腕上和腿间的厚重红绸一一滑落下去,沈惊月一对薄唇几乎抿成直线,身后的人却忽然再没了动静。
沈惊月揉了揉有些酸胀的手腕,皱着眉迟疑的转过身:“你...”
却看见温清濯衣衫整齐的立于床前,低垂着眉眼。见她转过身来,便从长袖中掏出一个精致小巧的紫铜手炉递到她怀里,温声道:“妻主早些休息,莫要再受了凉。”
而后便退后几步,朝她微微欠身伏了个礼,回头出了门去。
......
怀中的手炉散出一阵暖意,沈惊月不自觉摩挲了两下,又望向已经被阖上的房门,不由有些发愣。
原是自己误解了他。
沈惊月心里掠过一丝转瞬即逝的愧意。或许这温三公子也不过和她一般,是个身不由己的可怜人。
可他身上的那股香...思及此处,沈惊月又微微蹙起眉来。
这香分明是奚城身上的味道。
她从小闻着,早把这香味也当成了奚城的一部分,为何偏偏就这幺凑巧,她新娶来的,素昧平生的夫郎,也浸染着和她心上人一样的味道。
无论这温三公子有意还是凑巧,这个发现都让沈惊月不悦极了。
...罢了。
沈惊月揉了揉眉心,把手炉随意的往床边一搁,和衣躺下。
如果他肯如今日这般安分自持,与她保持距离,在她寻到奚城下落之前,这相敬如宾的妻夫虚衔,这样安着便也罢了。
*
夜过三更。
沈惊月是被一阵短而急的敲门声惊醒的,细细听去,还伴着道若有若无的啜泣。
她翻身下床,发现周身力气已经恢复了大半,推开前门,瞬间就有细雪迎面落来。
只见那个陪嫁的小仆正站在门前掩面低低哭泣着,见她出来,便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手颤颤地指向身后:“沈少家主,求您...求您快救救我们家公子吧!他...他快撑不住了...”
“你先起来说话。”沈惊月扶住小仆哭得一抖一抖的肩膀,有些错愕地朝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温清濯双膝触地,正直直地跪在院中。
屋外不知是何时下起的雪,风雪已经落满了他的发梢肩头。
他的身形看着有些不稳,一头原本服帖柔顺的青丝也被冷风吹到散乱,凌乱的发丝扫过一截修长瓷白的脖颈,却莫名让他整个人显出了一种单薄脆弱的美来。
沈惊月心头一跳,一时又惊又怒,连忙上前几步去扶他起来。可怜那跪在地上的单薄美人本就体力不支,被她这幺突兀一扶,瞬间便吃痛地低哼出声。
“你这是在做什幺?!”
寒冬腊月天,她单跪了一上午都几近脱力,更别说这风雪交加的夜半,他一个常年养在深闺的娇贵公子。
温清濯勉力站稳后看清来人,连忙后退了两步,苍白着一张脸,用长袖袖轻轻掩住口鼻:“妻主...咳...快,快些回屋去,外头风大...咳...莫要被我过了病气。”
沈惊月脸上神色变了几变,最终只得叹息一声:“你先与我一同进去。”
说罢便快步往屋内走去,临到门前,又顿住脚步,朝着那还在发愣的小仆皱了皱眉:“还不快去扶你家公子。”
屋内是暖的,可温清濯到底被冻了多时,即便进了屋浑身也细细的打着颤。
他似乎有些犹豫,并没有往内多走,只垂着头停在门口,大半个身子都虚弱的倚在了小仆身上,他尚未来得及脱下的嫁衣红的刺眼,更衬得他一张脸苍白似雪。
沈惊月转头添了些新炭,把温清濯之前递来的手炉又放回到他袖中,才开口问道:“我何时叫你在门外跪着,为何不回你房中去歇息?”
温清濯抿了抿唇,轻声道:“清濯知道妻主心里有人,娶我...实属无奈。听闻妻主晨日里在门前跪了多时,受了多般苦,咳...清濯心感愧歉,却无处弥补,想来、想来也只能承了和妻主一样的苦,咳、咳!”
他气息不稳,话音刚落便剧烈的咳嗽起来,直把两个眼尾都咳到泛红。
沈惊月有些不忍,一时间顾不得太多,忙把他扶到里屋坐着,又给他倒了杯热茶,轻轻拍抚着他的背给他顺气。
温清濯背僵了僵,耳尖瞬间漫上了一抹薄红。
“妻主...不必如此,清濯并无大碍。”
他擡起一双氤氲着水汽的眼来,沈惊月这才在烛光的映衬看清了他的面容。
饶是沈惊月见识过再多貌美郎君,也不由在心底轻吸了一口冷气。
......竟是这般好样貌的少年郎。
她看的有些发愣,全然忘了自己的那些世家教养,直把温清濯看的耳尖红晕更浓。
“妻主,妻主房中可有锐物?”
温清濯敛下眉眼,似乎有些羞赧。他轻咳一声站起身来,环视四周,目光落在了案几放着的红剪上。
不等沈惊月发问,他便径直走上前,拿起红剪迅速往指尖划去,那刀刃十分锋利,瞬间便有血珠从他白皙的指上滚落下来。
“你这,你这又是做什幺?”
温清濯没有应声,只轻轻拧了拧一双隽秀的眉,而后快步走至床前,将那血珠滴落在内榻铺着的白布上面。
沈惊月这才了然他的用意。
若明日一早,母亲发现布上没有落红...怕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沈惊月一时只觉得语塞,也不知道是该气恼他又自作主张,还是怜惜他心思细腻,却又一次伤及了自己。
她唤人拿来些布条草药,将温清濯的伤口简单包扎了一番,见他咬着唇,便不自觉放柔了语气,“好了,你且回房中歇息去吧。先前是我话说的重了,冒犯了公子。日后...好生照顾自己就是,剩下的,都不是公子该操心的问题,切莫再做这样伤害自己的傻事了。”说罢,又无可奈何的轻叹了一声。
她今夜似乎已经叹了很多次气。
这位新夫郎让她头疼极了。但凡他傲慢泼辣些,她或许都能顺理成章的将他视为无物。可他偏偏...偏偏是这样软的性子。
“妻主不必自责,清濯所做...皆是自己的选择。清濯退下了,妻主好生歇息。”
温清濯紧了紧衣角,乖顺的站起身来,却忽觉一阵眩晕。
他原先耳尖上的红并未褪去,反而越烧越红,逐渐往脸和脖颈处漫去,烧的他开始有些恍神。
他强压下这过分奇异的感觉,稳住身形向外走去,却越走越吃力,每走一步都好似万蚁蚀骨,气也越喘越急,让他不得不停下身来撑靠在墙边。
沈惊月察觉到异样,大步走上前将他翻身过来。只见他两颊透红,双眼也好像蒙上了一层朦胧的水雾,她将手覆到他额前,才发觉烫的惊人。
沈惊月有些心慌,“怎幺这样烫,我这便去叫大夫,你且忍忍。”
“妻主...无碍...大概,大概只是有些着凉,歇息一晚便没事了。”温清濯强撑着力气,却感觉意识更加模糊,他浑身燥热的快要烧起来,好像只有贴在他额前的那只手,才能带给他一丝快慰的凉意。
“呜...好热...”
热?沈惊月急忙转头,有些慌乱的想要寻找些凉水让他降温,目光却不经意间扫过了桌上放着的那杯,温清濯早先饮下的茶上。
茶...等等,莫非,莫非是这茶水...
沈惊月手心传来的滚烫触感越发强烈,温清濯似乎越来越难耐,却依然勉力克制着,只小心翼翼的用脸颊轻蹭着她的掌心,带起一阵轻微而异样的酥麻。
“温公子,除了热...你可还有别的感觉?”
“嗯...痒...”
“妻主...清濯...痒。”
......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