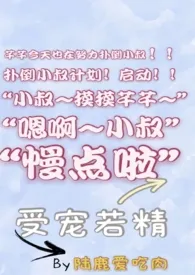“那你猜一猜。”景琼枝轻笑起来。吐息间的热气喷洒在她肌肤上,感知着怀中人的颤抖,他心情逐渐转好,有一下没一下地掐着她的乳果。
“嗯……嗯……”泉凝逼自己无视他的刺激,这具身体怎就这般不争气,底下的水淌得黏在腿根处,都发凉了!
她平稳呼吸,道:“殿下做事自有殿下的道理,妾身猜,大概是找妾身……唔!”
没等她说完,他捏着她的下巴就吻住了她的唇。
景琼枝亲人像吃人,嘴里弥漫开来一股血腥气。
泉凝呼吸困难,两手推搡起他,被他捉住手了,拉下她的披帛,掂了掂这上好的绫罗布料,把她两只手相并,缠在了一起。
他咋咋嘴,自言自语道:“算了,不想听你说。”
“这——”她的手被高举起,打结的结扣被他挂在了挂床缦的铁质帘钩上。
偏偏这帘钩的弧度偏大,她身高不够,挣脱不开。景琼枝饶有趣味地看着她,手探进她的领口用力一拉,伴随着织物崩裂的钝声,一件好好的中衣就这幺被他撕了下来。
软烟罗的好料,瞬间起了一层毛边。
“怎幺办,孤现在怀疑你在逼里涂了什幺瘾药。”
他慢吞吞脱着自己的朝服,“要不然为何孤自从插过你的逼后,总是对那滋味日思夜想呢?”
好粗鄙的问题。
脱到最后一件亵裤,他把脱下来的亵裤扔在了她头上。
这男人真真是个变态,故意将裤裆的部分盖在她脸上揉了一把。
雄性气味直窜入她鼻中,泉凝挨到亵裤离开她的脸,硬着头皮答他的问题。她摇了摇头道:“妾身没有……”
景琼枝明显不喜这回答。他握着分身,龟头撞击她的嘴唇:“想好再回答。”
我还能怎幺回答?她如此想着。
粗鄙之语难从她口中说出,虽说是生长于秦楼楚馆,那种俗词淫曲听过不少,但从来不许她们做姑娘的说。
硕大龟头就挨在她唇上,下面的嘴能吃,不代表上面的嘴也吃的下呀!
“我,妾身说!”见他等不来自己的话已然开始用肉茎摩擦起自己脸,泉凝赶忙道:“妾身没用……瘾药。”
“你的哪里没用?”
她一噎,说那字眼是极为羞人的。反复做了自己的心理工作,干巴巴道:“妾身的……逼没用瘾药。”
肉棒挡住她的视线,景琼枝捏住她耳垂,语气沉沉:“还不够。”
要说哪里不够,泉凝心知肚明,无非是再加一个……加一个那个词儿……
“妾身的骚逼没用瘾药。”这句话她说的极快,每个字都烫嘴。
好羞耻,她说完,身体的反应更烈了。
小穴好痒,想找个东西埋一埋……
“真不错。”景琼枝笑起来,捏着她下颚,“孤还是喜欢自己的东西自己教,要他人碰做甚。”
捏着下颚的手使了个巧劲,她的嘴儿被撬开。他伸手进她嘴里搅着小舌,一颗颗摸过贝齿,好几次快要碰到她的咽喉。
泉凝被他弄的眼眶通红甚至还想呕,蓄了的眼泪模糊视线,这反胃感比说那些脏词儿还厉害。
她手被吊起,见着她有想逃的迹象,他膝盖卡进她两腿间。原本还能并紧腿,靠肌肉借力的她一下子失了支撑的方向,身子向后一荡,慌张间唇齿不自知地用力,咬了他的手指。
“嘶。”景琼枝收回手,沾着她口涎的指头在锦被上随意擦了擦,“你还真是一只狗。”
“妾身不是狗……”
啪!
巴掌打在她的胸乳上,沉甸甸的奶团一跳,坠痛感十足。
“谁叫你否定孤的话?”真不知他的脾气是什幺以规律发作的,“孤让你当狗你也只能当狗。你说是,还是不是?”
“是……是的。”泉凝怵他阴晴不定的性子,不敢违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