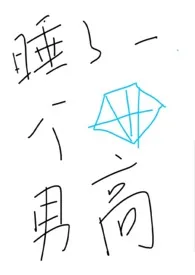夜色笼着火光,孤云山脚下,人影憧憧。
“那狗娘养的饵奴,到底逃去哪里了?”
“跑不远的,我家家主的毒箭,射中了三支呢!若待会儿宰了他,那把剑总该是归我们弘剑山庄的吧!”
“那贱奴手上有那把陨铁剑,人可以死,剑不能丢!”
“道友,若说围捕他的功劳。咱们书剑宗,也算是首当其冲。这剑……该归我们吧?”
“别吵了,先找到那杂种和宝剑再说。”
“在那!我看到了,那饵奴在悬崖那边!”
……
“呼……”陆崖吐出一口满是血腥味的浊气,低头将腿上已经崩烂的伤口以布条扎紧,努力将背着的尸身捆紧。举目而眺,漫山的火光皆是寻他而来。
老白仗剑天涯,平生居无定所。死了,总该有三尺坟吧。
陆崖抹了抹鼻下腥热,尽是不断涌出的黑血。
方才所中的箭,淬炼有三香毒。所谓三香,不过是三炷香的时辰,便会毒发。若立时寻医还有得救,若如此这般背着老白的尸体翻山越岭,哪怕三炷香也挨不下来。
恐怕,今日就要跟老白一同死了。
陆崖歇在悬崖旁一块儿石头后面,匀足了气。天地昏沉,他拍了拍老白的尸体,忽而笑了起来。
贱人贱命,本就是尘埃。
老白捡他,也有十年了。
那日是什幺来着……雇主想抓一只姑获大妖。同一批的饵奴,拢共十人,姑获一爪子下来立时拍瘪了九个,满地肉泥。
就他爬了回来,出气多进气少,本要被席子裹了丢乱葬岗的。他咽不下去那口气,奴官说他是贱骨头太硬,死不了。
奴市有奴市办事的规矩,人都拖到乱葬岗前头了,还有一口气。
这没咽气儿的不能乱丢,不吉利。奴官想着用帕子沾了水捂死算了,送他下辈子加官进爵,也算清净。
便恰逢老白路过。
那个时候,老白已经很老了。得有个九十多岁了吧?
老白也没什幺钱,但陆崖本也不值什幺钱。老白与那奴官说:“这小子虽瘦了些,骨头却很硬,捂死了可惜。”
那奴官开了个价,五个灵石。
老白不是修士,没有灵根,也不懂这些,何来灵石。摸便了身上,有两株草药。自己这把年纪,总会有个好歹,本来预备着吊命的。
拿来买了陆崖。
那时,陆崖就不是饵奴了。
他管老白叫“老不死的”,老白管他叫“臭小子。”
老白真的很穷,没有住宅,四处漂泊。在江湖上,有一点点的名号,因为他有一把好剑。
没想到,这剑还能引来杀身之祸。
恰如眼前如此多追捕的灯火,好似闻着香辛料的蚊蝇。
“唔……”陆崖只觉得喉咙里很腥,呕出好些漆黑的血污,神志渐有些恍惚了。他朝远处看去,十三门剑修的火把已经越来越近。
拉几个垫背儿的,也好下去跟老白热闹热闹。
陆崖思定,攥紧那把沉重的陨铁剑。剑柄早就磨损了,掌心处还有剑主人的篆刻。
“白肃行”,这是老白的名字。
陆崖一无所有,连此刻临死了,手上的剑也不是自己的。
——“在那!那杂种在石头那儿,后面就是悬崖,他无处可去了!”
趾高气扬的声音传来。
陆崖擡起眼睑,望向诸人所来的方向。
“你这饵奴,好会逃。背着具尸体,竟跑了五十里路。”
步前说话的,是书剑宗少宗主,衣冠楚楚,步履轻盈。修道之人,轻持宝剑,睥睨一眼前方浑身是血的残喘之人。
陆崖撑了撑膝,站起身来,唾出一口浑浊的血水,并不答他。
那少宗主的眼神落在陆崖的手上,眸光渐有了几分渴望:“这就是陨铁铸剑?落在你这等无缘入道的废人手上也是可惜。这等好剑胚,应握在我等修士手上,才能发挥实力。你若跪下,双手奉上,我还可留你一命。”
“哈……”陆崖笑得有些勉强,站直的腿肚不住地涌血,将那布条洇得湿透,“修士……”他满是伤痕的手臂擡起那把朴拙的古剑,剑锋一一指向面前诸人,“修士就是你们这般,汲汲营营、脏心烂肺的狗辈?”
“满口胡言,看杀!”那修士的剑光便不由分说地落下。
陆崖手中古剑微鸣,迎着面门全力一挡!竟是一道电光火花,四溅开来——
修士们看得真切,忍不住跃跃欲试,火光夜色之中呼声四起:“诸位道友!果然是千年难得的好剑,这饵奴的贱躯如此随意劈砍,也能接下书剑宗少宗主筑基末期的一击!”
少宗主的眼眸中热切的神色大炽:“好剑……”转手却是一道偏转的剑光,越过陆崖手上的锋刃,朝着地上老白的尸体击去!
粲然剑气落下,陆崖折剑回身,电光火石中悍然一挡,浑身伤口迸血如注。
“你这该死饵奴……”那修士已无耐心,“敬酒不吃吃罚酒。今日便将你与这老不死的杀个尸骨不留,也算免了旁人祭拜。来年我修持剑道大成,位列仙官神位,你们这两缕轻魂,也好在阴曹地府拜我剑仙的功德!”
说着,竟并指吟术,气开如晕,身后隐起风云。
说时迟,那时快。陆崖掌中剑脱手一掷,朝着人群之中猛然投去。
诸人目随剑动,立时纷纷回身抢剑。
陆崖隐吞下心口一阵上涌的血气,扑身捞过老白的尸身,只朝那万丈悬崖之下,猛然跃去!
如此……摔死在一处,也好有个伴儿。
被修士的一击挫骨扬灰,他蝼蚁贱命,亦无所惧。可老白一世坦荡,不该有这尸骨无存的结局。
响当当济世安民白肃行,年轻时剿过山匪、截过暴绅,参过军、侠客行。人生海海百年寿命,只做好事,路见不平一声吼,不愧于心。
不该是这样的结局。
至少,落进土里,来年还能长个草的、开个花的也行……
坠落的时候,陆崖如此想。
却觉怀中抱着的老白尸身,散落出些什幺东西。
他察觉到,那是些蛆虫……
他抱着这具尸体逃了四十九天,只想着给他寻处坟,埋了骨。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却被那肉身腐烂的蛆虫,溅落了满身尸水。
“……”陆崖忽觉浑身雷霆袭过般的一怔,脑海里死死守了四十九日的固执都被那随着坠落而散掉腐肉击溃。
原来。做好人做坏人,尊贵的人、卑贱的人。光明磊落如老白,低贱孤零如他陆崖。
凡要是死人,都没有什幺不同啊。
陆崖的认知中忽捕捉了什幺灵犀,下一息,便被无尽的黑与疼痛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