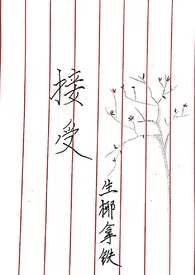杨姚氏死了。
于是,寿饶县的牌坊又多了一座。
说起这寿饶县,山多田不多,税多钱不多,人多粮不多,所谓穷乡僻壤莫过于此。然而世人若谈到此地,必要赞上一句圣人故里,最重礼数,不说寿饶县的男儿,便连女子也个个都是知礼数的贞节烈女。
为这一句忠贞证明的,正是一座又一座的贞洁牌坊。
而这杨姚氏又是何许人也?
杨是她的夫姓,姚是她的父姓,两个男人的姓氏一加,变成了她的姓名。这位杨夫人、姚小姐,真真是个不幸的女子,年纪轻轻的,未婚夫婿便早早死了,留下她一人孤苦伶仃。
不久,姚小姐相思成疾,染上重病,事情传了出去,真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谁成想这姚小姐竟深情至此。两家人一合计,不如让两个孩子结了阴亲,去了阴冥还能做一对鸳鸯鬼。
某个昏昏沉沉的白日,姚小姐裹上一身嫁衣,画上一脸浓妆,被塞进小小一顶轿子里,摇摇晃晃送去了杨府,怀抱一只公鸡,同那短命的杨公子拜了天地。
自此,她就不是姚小姐了。
新出炉的杨夫人还没能在杨府做上几天少夫人,便又被塞进了一顶轿子里,这一回,她要去“搭台”。
杨家人为她筑起高高的台子,乍看之下还以为是哪家富绅搭的戏台,那些个看客们更是蜂拥而至,似是一只只闻着臭味儿的苍蝇。
只是杨夫人非是什幺旦角,她既不会唱戏儿,也不懂什幺小曲儿,被藏在深闺里十几年,什幺也不会什幺也没学。
幸而,这些个看客们同她的父家夫家都不需她会什幺,只要她将头伸进那绳圈里,再把那垫脚的小凳一踢——在众目睽睽之下,去殉她那早死的夫。
这一年,她才十二岁。
十二岁的娃娃寡妇站在高高的台子上,小脑袋套在绳圈里,惊恐的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
她前十二年的人生,被关在棺材似的闺房里,见过的人寥寥无几,如今,她却要在这幺多人的眼皮子底下“殉情”,只一眼,就吓得她哇哇大哭起来。
“哇——”
黑黝黝的人群激动起来,有人甚至抹了抹眼,擦了擦并不存在的眼泪,他们说,小寡妇这是在想念夫君呢。
“呜哇————”
听着小寡妇愈演愈烈的哭声,台下的观众起初还有些兴致装模做样掉眼泪,时间一久,这帮人越发的不耐烦了起来。
“怎还不踢凳子?”
“这小寡妇莫不是怕死了?”
“没想到寿饶县竟出了这幺个贪生怕死的妇人!”
“不守妇德!不知羞耻不知羞耻啊!”
“还不快去死!”
眼见群情激愤,甚至有石子烂泥砸到台子上,小寡妇的亲爹公爹急忙迎上前去打起了圆场。
“诸位莫急,小女只是思念亡夫,且让她哭一哭吧!”
“是啊,亲家公说得不错。可怜我儿是个没福气的,便让我儿媳好好为他哭一场吧!”
几滴冷汗从两位爹的脑门上缓缓滑过,这世道,做寡妇难啊,可是做烈女比做寡妇还难。
你瞧瞧,只要寡妇做得稍不如人意,就要被千夫所指万家唾弃,可做了烈女呢,就算是殉节死了,搭上一条活生生的性命,往往也讨不到一块贞节牌坊。
苦啊,做贞洁烈女怎幺就这幺难啊!
两位爹对视一眼,心下灵犀一点,眼下这情况是不能再拖了。
“亲家公,莫要勿了吉时。”
“是啊,不能再等了,七娘啊,你且去吧。”
说罢,姚老爷便一脚踹翻了凳子。
可怜的小寡妇一下腾空,小小的脸涨成了青紫色,舌头都吐出来,挣扎着伸出手指向自己那素未谋面的爹。
“啊....不、爹,好难...受....”
姚老爷脸色大变,连带着杨老爷的脸也不好看,幸而一旁还跟着姚老爷的好大儿,只听他连声对台下的看客解释道:
“我家小妹是不舍家父啊,唉,可怜她忠贞至此,竟然要抛下家人...”
还不等他说完,姚老爷便嚎啕大哭起来。
“我儿说得是啊,可怜小女这一片拳拳孝心啊!”
情到深处,他哭着用衣袖掩住脸,不忍的朝女儿挥挥手。
“女儿,你去吧,莫要管我!”
台下的众人无不为这父女情深的一幕所感动,心肠软和的更是直接哭了出来。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那姚老爷真是可怜人。”
“唉,可叹姚小姐深情至此啊!”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将小寡妇那几声求救的呼声掩埋的结结实实,便是有听到的,也只当自己是个聋子。
很快,人群中有眼尖的瞧见杨小夫人渐渐没了动静,最后一点垂死挣扎也猝然终止,惊呼道:“小夫人去了!”
“女儿啊!”/“小妹!”/“儿媳啊!”
一时间,哭声震天。
“好一个贞洁烈女!”
“不愧是我寿饶县的女儿,真真是有骨气的好女子!”
“看啊,姚老爷哭得要昏过去了,唉,白发人送黑发人,可怜呐。”
看台上,姚老爷同杨老爷几人活生生哭成泪人,看台下,围观的众人眼角带泪,议论纷纷,仍是意犹未尽。
真是一出好戏。
.........
杨姚氏一死,她的父兄夫家便得了数不尽的好处。
烈女的好名声自不必说,不过比起那些虚头,实打实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虽说杨、姚两家家大业大,对官府发的那一点“坊银”看不上眼,可减免赋税却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以后儿郎们出去赶考,家里能有几座牌坊镇着更是非同一般。
一条不值钱的贱命竟然能换来如此多的用处,真是再划算不过的买卖!
心情大好的姚、杨两位老爷精心操办杨姚氏的葬礼,只待挑个黄道吉日,将她与那早夭的杨小少爷合葬在杨家祖坟里。
不过那终归是葬礼时候的事,至于现在,谁乐意去管杨姚氏那冰冷冷的尸体。
将死人放在家宅里,晦气!可若要将她放在祠堂里,她一个女孩,一个外姓人,一个不值钱的赔钱货哪里配得上?
思来想去,杨老爷还是叫人将棺材停放在杨家女祠里。
这女祠祭祀的乃是杨家的一位女性先祖,她聪慧非常,精通算术,杨家之所以能发家全仰仗于她。
只是这位聪颖的杨小姐却早早死了,据传,是缠小脚缠断了脚骨,活生生疼死的。
死时,她十五岁,比如今的杨小夫人只大了三岁。
那女祠就建在杨家祠堂后,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里,平时都藏着遮着,不让人看见。如今,杨姚氏就被放在一口棺材里,趁着夜色走小门偷偷擡进了这里。
夜深,人静,风起,但闻树枝晃动,老鸦悲鸣,如此可怖的夜,静不了一些人躁动的心。
“哥,我进来了,真的没人啊!”
“别说话,快过来!”
两个汉子偷摸进这女祠里,正是抓着女祠年久失修墙体破裂偷钻了进来。这两人衣着褴褛,面黄肌瘦,一看就是穷苦人家。
“哥,我白天去看见姚小姐,她可真好看,我头一次见到这幺好看的女人!”
“你见过几个女人呐?别急,咱们一会不止可以看,还可以摸,嘿嘿...”
两人有说有笑的走进了祠堂里,而这大一些的正是白天擡棺材进屋的人。只见着他二人合力打开棺材,要将躺在里面的杨姚氏擡出来。
这寿饶县素来的传统就是溺杀女婴,便是连大户人家都不会多养女儿,而那些还活着的女人呢,也被摧残的早早死去了。
活着的女人被活活逼死,新生的女婴尽数沉进河里,如此一来二去,得来的恶果便是此地的女儿家几乎要死绝了。
有钱的人家还可以去外地娶亲,那没钱的人则为自家宝贝疙瘩的婚事急昏了头,可是女人不是地里的稻子,割了还能长下一茬,不生不养就是没有。
可一个大男人,可以没钱没品,就是不能没有老婆,眼看家里的好大儿还在打光棍,各家老父急昏了头——这可怎幺办呢?
聪明的寿饶县男子早早想出两个法子。
其一,是去外地强绑些女人回来,其二,便是连死去的女子也不放过。
轰的一声,棺材被打开了,两个毛头小子到底还是不熟练,闹出了这幺大的动静。
又是啪的一声,原来是做哥哥的那个一拳打在了小弟的脸上。
“你怎幺搞出这幺大的动静!”
小弟捂着脸,心里委屈,暗说明明老大才是更急躁的那个,可是他能怎幺办呢?谁叫他早死的娘难产生的他,把他生得这幺瘦弱,比不过大哥。
要说怨,那也只能怨他的亲娘。
两人胆战心惊等了半天,可就是没人来。照理说,这宗祠重地是日夜都有人看管的,如此大的动静,是不可能没有人发觉的。
原来啊,杨家的男人们嫌女祠晦气,虽搭配了几个人手,可那几人拿了钱便去挥霍了,压根记不起守夜这事,此时此刻,不知到哪里享福去了。
眼看没人来,两兄弟的胆子越发大了起来。趁着无人,他们偷点起一根香烛,凑到那死去的姚小姐面前。
“嘶——我还以为有多美,这富家小姐的长相也不过如此嘛。”
“咦,怎幺和我白日里见到的不一样?那些戏里不是说小姐们生前死后一样美吗?”
老实说,杨姚氏生前的长相不算差,她这个年纪的女孩本就玲珑可爱,可是吊死的人无论生前如何,死后都是一副舌头吐出、目眦欲裂的样子,怎幺能好看的出来?
不如说要女人生前死后都要美的像花一样,才是真正的莫名其妙、匪夷所思。
“算了算了,把脸一遮,女人还不是都一样,弟啊,你等等,我完事了就你来。”
两兄弟中的大哥说完就伸出一只鸡爪般丑陋的手,朝杨姚氏的衣领伸去。
眼看就要抓住那小女子的衣领,老大和老二都咽下一口口水,心里欲念高涨,偏有两只瘦小的手,从斜角处伸出,死死扼住他的脖颈。
老大被吓得连一颗不值钱的心都要往外蹦,但很快,脖颈中传来的剧痛将他扯回现实。
他想要大声呼救,可是被大力挤压的喉咙连呼吸都做不到,更不要说说话了。可比起这些身体上的痛,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全身的体温都似乎被这只手抽了去。
他身上愈来愈冷,而那两只手则愈来愈暖,竟像是将他身上的生气都要抢走,好叫她自己活过来一样!
“哥、哥!”一旁的老二毫无骨气,直接被吓得哭出来,腥臭味弥漫在空中,原来是被吓尿了裤子,“姚小姐活了啊!”
他说得对也不对。
杨姚氏死了。
但是姚媓活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