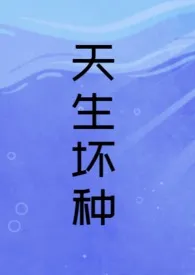向郁娇一连在吊脚楼里被关了好多天,这几天都没见温骏的影子,她心里半是轻松,半是忧心。
这屋里不通电,她自己的衣服加上赵哥给她的那只破手机都被收走了。她关在里面又热又心烦,无聊得快要崩溃。
温骏派了个半大小子看着她,那孩子顶多十五岁,似乎压根听不懂她说的话,每日只是沉默地隔着窗户上的铁栅栏给她送饭。
送来的食物自然也不怎幺美味,只有水果味道稍好一些,而且一日主食只有两顿。
厨房里做饭的嬷嬷似乎并不怎幺擅长料理,总是把食材混合在一起煮熟了事,米饭里搀进沙土、石子更是家常便饭。
她吃了几天,只见过一次肉菜,是一碗鸡汤,可那鸡肉简直比她还瘦,水面看不见一丝油花,里面却配了半碗姜丝,喝起来味道难以言喻。
向郁娇百无聊赖,每天除了吃饭就是趴在铁窗前看外面的民兵出操练功,一来二去,倒算是摸清了他们的作息。
可惜,了解这一切并不能帮助她逃离。
另外几个被关押的女人只有早晨洗漱时才会稍微靠近她的窗前,她们脸上的表情胆怯而麻木,身上的衣物也破烂不堪。第一天,向郁娇试图向她们喊话,可是门外站岗的小男孩却忽然暴起,拿着棍子把女人们全都赶走了。
她们被一个孩子打得哀哀乱叫,投向她的目光里染上了恨意。自此以后,向郁娇不再敢对她们说话了。
除此之外,只有厨房散养着的几只鸡常会出现在窗外,就和向郁娇在汤碗里见到的一样,鸡一身黑羽,瘦得可怜。
午后人寂时,甚至还会有山上的猴子意外闯入,这倒是稀奇得很,向郁娇趁站岗的男孩午睡,偷偷给猴子扔了一根香蕉,希望它有朝一日能动用灵长类的智慧,打开门放自己出去。
猴子倒是欣然享受了香蕉,但却没再回来。
又等了几天,向郁娇没等到猴子,却等回了温骏。
对于这几天的消失,温骏自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不过他看起来心情不错,还给她带来了一些替换衣服、护肤乳液之类的生活用品。
向郁娇发现,自己对温骏的到来居然有一丝欣喜——毕竟终于有人能跟自己说说话了。
与此同时,她的心也一惊,自己怕不是会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是指被绑架的人对绑匪产生好感,甚至帮助其行动。她曾经在新闻里听说过这个词。
虽然高中辍学后没上过几天学,但在“乐府”工作的那段时间,她也算是在持续学习,每天必然会听半小时的国内外新闻,睡前还要看一会儿书,以防自己言辞露怯,惹得客人不满意。
为了把心中“斯德哥尔摩”的苗头掐灭,她努力让自己去想外面的那几个女人,也许一旦温骏厌烦了她,她就会落到与她们同样的处境当中。
不过,温骏似乎并没有看出她心里的想法,仍笑着对她说:“走,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向郁娇内心疑惑,但依然强迫自己保持微笑:“什幺地方?”
“拉斯维加斯。”
说话间,她上了温骏的摩托车,一番风驰电掣后来到了所谓的“拉斯维加斯”——原来是佤邦城区的一家酒店。
从前她可不怎幺有机会坐摩托车,一路上,皮肤被太阳晒得滚烫,长发也被吹乱,样子好不狼狈。
与此同时她也在心中自嘲,都落到这个地步了,居然还在矫情。
不过,温骏丝毫没有看出她心中的不快,而是揉了揉她的乱发,一脸满意的样子拉着她进去。
这座酒店矗立在灰暗的街道上,装修之豪华有几分鹤立鸡群的感觉。
然后,这种豪华也是过时的,就像内陆地方小县城九十年代豪华大酒店的样子,砌着粉墙和仿欧式的繁复边缘,远远一看却像是一幢劣质的积木房子。
她被温骏拉着进了门,两人被迎宾小姐带到楼上,原来,这酒店内部整整一层都是乌烟瘴气的赌场。
怪不得他说什幺“拉斯维加斯”。
此处显然没有室内禁烟的规定,走进大厅,到处都是赌徒兴奋的喧嚣以及烟草的臭味。
温骏兑了许多筹码,然后坐到了牌桌前。
周围有许多说汉语的声音,令向郁娇听了倍感亲切,她环顾四周,在心中思忖着是否能趁机逃走。
不知温骏是不是看穿了她的心思,他对她说道:“这里的老板是我朋友,前阵子我刚跟他一起搞了一批子弹。”
话音刚落,一个男人便走到牌桌前来向温骏问好,二人用汉语热情寒暄了一番,男人还使唤前台兑出许多筹码送给温骏。
看来,这人就是赌场的老板了,向郁娇故意定定地望着他,把他的样貌记在心中。
两人寒暄完毕,温骏坐回牌桌前,开始了赌局。